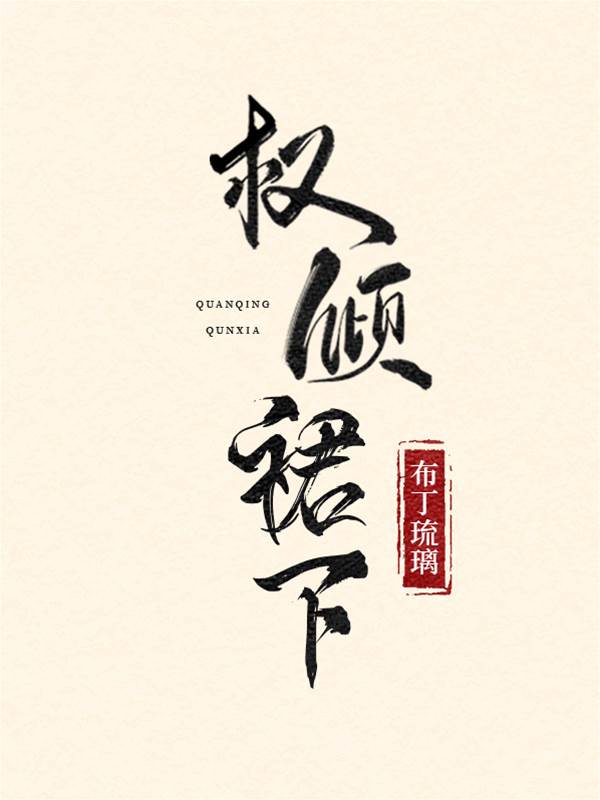《丹陽縣主》 第70章
如果他真的只是陳慎,就好了。
而朱槙夜探的營帳這事過去后不久,就發生了一件大事,推了整個戰局的進行。
朱槙的軍隊夜襲駐扎營北角,燒毀了數十間帳篷,火勢順風而行,又燒毀了半個慶都縣城,攻破了防線救出了陳副將。幸而慶都縣百姓多已被暗中撤離,人員傷亡并不大。
蕭風迅速反應,帶領軍隊撤出駐扎區,得以保全全軍。又抓了朱槙幾個殘余斷后的手下,并與趕來的京衛援軍會和。此時蕭風軍隊八萬人,而朱槙軍隊卻只有五萬,并且于下游地帶,易攻難守。
對于朱槙為了救自己手下,不惜燒毀縣城,不顧百姓安危一事,蕭風十分憤怒,與元瑾合計,如今兵力盛于朱槙,又占了士氣,趁著朱槙的軍隊糧草不足之際,正是攻擊的大好時候。
元瑾則覺得這件事有些不尋常。
朱槙的確用兵極巧,但為何,駐扎在慶都的軍隊只有區區五萬人,知道保定難攻,何必用這些人來送死!
難道他還有什麼后招,等著上鉤?
但也不是啊,他背后已無援軍,且無論從什麼方面看,他這場戰役都是要敗的。究竟是因為什麼呢?
元瑾想讓蕭風再等等看,但蕭風卻告訴:“阿瑾,你也知道,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此時不戰,才是不好。”
對于行軍作戰,五叔自然是比自己懂的。當年父親曾夸過他‘用兵凝練,直覺堪比三十歲老將’,他既然覺得應該攻打,就沒有錯。
元瑾與他站在高,看著一無盡秋,看著朱槙軍營的方向。
說:“那便進攻吧。”
蕭風就開始著手準備起來,力圖一擊必勝,不要再給朱槙氣的機會。
Advertisement
大清河河水滾滾而去,天沉,線不明。
日暮時分,戰鼓突然響徹天際。
蕭風領軍隊自西顯口而下,將自己麾下最銳的部隊組織四千敢死隊,以虛打實,看似從虎口過江,實則通過架橋,出其不意地渡過大清河,向朱槙的大本營發起猛烈的沖擊。
一時間喊殺之聲震天地。
朱槙的副將立即傳令出兵。先派出一萬人應戰。而更多的蕭風部隊自西顯口而下,加戰局應戰。
朱槙的營帳中,穿鎧甲,當他以這裝束出現的時候。他的氣質便截然不同,有種凌厲和肅冷之。朱槙這十年來,可以說有一半的時間都是在打仗中度過,戰爭于他來已經是的一部分。
當初帶領他的老師,朵三衛的統領,曾經告訴過他,一旦當什麼東西為你天分的一部分,你就是不可戰勝的。普通人會怕戰爭,怕傷,怕死亡。但是他不會,他的神經已經千錘百煉,已經無比的適應。這才能讓他對戰局做出迅速和最佳的反應。而現在他要做的反應,不同于尋常。
他慣用的兵,一柄玄鐵所鑄長刀立于營側。
“殿下。”屬下將長刀捧來,朱槙一把拿過,在手里掂了掂,出了沉沉的笑容。
朱槙上戰馬迎戰,戰鼓雷雷,他一聲長喝,浩瀚的回應聲便從四面八方傳來。挾裹著他洶涌向前,是這樣的氣勢,就足以嚇退普通軍隊。
此時顧珩與清虛站在朱槙后,顧珩看著他的背影遠去,他盡量控制著自己的眼神平靜,不要出毫的仇恨,讓人察覺到什麼異樣。
與薛元瑾相認后,他就回到了朱槙邊,如今已有小半個月了。這小半個月里,他幫著朱槙守衛營地,到現在,終于到了兩軍正式開戰的時候。并且都氣勢洶洶,一副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架勢。
Advertisement
他心中擔憂,便不能放下心來,一直站在外面看。
“得嘞。”清虛卻了個懶腰,跟顧珩說,“侯爺,咱們進營帳吧,這外頭怪冷的。”
顧珩留下來后方,保護包括清虛在的一批手無縛之力的幕僚。
“我放心不下殿下。”顧珩就說,“再者也得準備是否要接應,殿下雖然驍勇善戰,對方卻畢竟是人數居多,且蕭風也實力不俗。”
清虛抓了抓胡子,覺得他很無聊:說起話來老氣橫秋,覺比他的年齡還大。
但是營帳也沒有別人可以說話了,清虛只能鉆進營帳中,把他的燒燒酒端出來,坐在地上一邊吃,一邊跟顧珩一起看戰局。顧珩轉頭看向他,看著清虛一副滿不在意的樣子。角微,覺得他比自己更像一個臥底。
清虛發現顧珩正看著他,就笑瞇瞇地舉起了燒:“侯爺也來點?”
“不必了。”顧珩問,“道長,您就不擔心殿下?”
清虛灌了自己一口酒,笑道:“侯爺,你看你這說的是什麼話,他可是靖王。自然是……”他眼睛一瞇,“一切在他的掌握中了,旁人替他什麼心。”
顧珩突然間有種不想跟他說話的沖,他轉過頭看自己的。
過了會兒清虛無聊了,鉆進營帳準備睡一會兒。戰局隔得有些遠,其實看不太清楚了,顧珩準備進營帳中看看。
他剛走進營帳,就看到清虛四平八穩地睡在他的床上,吃了燒的油手,就蹭在他的被褥。
顧珩:“……”
朱槙究竟是從哪里把這號奇人挖出來的!
他正要上前去醒清虛,突然間營帳被打開了,有人沖了進來,跪在地上:“侯爺,大人,對方搬來神機營炮統,我軍不敵。殿下傳話,準備撤退!”
Advertisement
顧珩很是震驚,幾乎不相信自己聽到的話。朱槙敗了,這怎麼可能!同時清虛一個鯉魚打從床上起來,沖到報信人面前:“你說什麼,敗了?”
顧珩心道你剛才才說什麼一切都在靖王掌握中,現在可被打臉了吧。
那人應是,清虛就讓他先退下,他自己跑到了自己的床下,翻了一會兒,拾出一個包裹。笑著對顧珩說:“幸好我早已做好撤退準備,侯爺,您快些打包吧,我看恐怕不到一炷香就要全部撤退了。到時候你沒打包好,我可不會等你。”
顧珩:“……”
不是說好了,對靖王殿下非常放心嗎?為什麼會提前打包。
清虛卻先拎著他的包裹出去了,說:“我在外面等你!”
顧珩角再次微扯,但是在迅速收拾的時候,他卻突然意識到了什麼不對。
一涼意過他的。
不對!
這件事,似乎有什麼地方不對。但是他被清虛擾了心神,卻好像沒有發現這種不對。
但究竟是哪里不對呢?
顧珩在腦海中迅速回想,將這幾天都過度了一遍,突然抓住了什麼細節。那就是朱槙出征的時候,未曾吩咐他做好接戰準備。這是不合理的,朱槙沒有預料過戰況會如何,怎麼又知道,不需要他接戰呢?而朱槙作戰多年,這樣的代,他是絕對不會忘的。還有清虛……這個人同李凌一樣,是朱槙絕對的心腹。就算他再怎麼玩世不恭,也不會對戰局如此的不關心。
除非……朱槙這一仗,本來就沒有想贏!清虛是知道結果,所以漠不關心。
但是朱槙為何要敗呢?
顧珩又想起山西詭異的調兵。
朱槙讓裴子清將兵調至懷慶,而不是前往保定支援……
Advertisement
不對,朱槙恐怕,就不是想攻打保定。這只是個障眼法,他假意攻打保定,吸引朝廷的注意力。同時暗中將兵力用在懷慶。只要將懷慶阻斷了。京城上鄰宣府,左鄰山西,幾乎等同于被靖王的勢力包裹在,那可只有死路一條了!
想通這一點,顧珩眉心重重一。他還說要幫助阿沅戰勝靖王,沒想到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發生這樣的事,他都沒有察覺。
希現在還沒有太晚!
顧珩將顧七進來,低聲叮囑了他一番,道:“你快些去,晚了就來不及了。”
顧七領命而去,隨后不久朱槙也帶兵回來了。所有人都已經準備好了撤退,一直退至山西孟縣都有追兵,但是追至山西就不再有了,山西是朱槙的老巢,蕭風是不會貿然追過去的,太冒險了。
而蕭風營帳中,打了勝仗,大家自然都無比高興。
其實保定本來就易守,打勝仗并不是因為攻克難關。其實這場勝仗的意義,是在于給大家以鼓舞。靖王不是不可以戰勝的,在此之前,知道要跟靖王打仗,很多將士一聽到就了,更遑論迎戰了。
蕭風將手臂上的一道淺傷包扎好,神采奕奕地同元瑾道:“阿瑾,你便是太過疑神疑鬼。你看,并未發生什麼別的事。說不定明日,我們都可以打道回京了。”
元瑾也笑了笑,只是笑容有些勉強。心中總還是沉沉的,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對,可是又一時半會兒說不上來。
朱槙的大軍撤退回山西,保定得以保全。慶都的老百姓得知消息,近些的都已經趕回來了,而這夜軍隊中是徹夜狂歡,酒都隨意吃,犒賞經過了廝殺的將士。
元瑾吸取教訓,只吃了些羊就走出了營帳。
這夜天空深藍明澈,星河深邃。在這遠離人煙之,能看到巨大浩瀚的星河從頭頂鋪開,人立于星河之下,只覺得自己渺小。元瑾靜靜地立著,立在星辰之下,覺得自己披星戴月,竟有種超塵世之。可惜這種覺并不長久,寶結了一聲,打斷了的思緒:“二小姐,有人求見您。您快些來看看吧!”
元瑾同寶結到了營帳,只見一個人等在營帳外,似乎有些焦躁,不停地在踱步。
待走近了,元瑾才發現,這是慣跟在顧珩邊的下屬,也曾見到過幾次。他一見元瑾立刻抱拳,道:“二小姐,可算見著您了,我有急事要稟!一定要快!您上蕭風一起聽吧!”
元瑾覺得有些奇怪。
顧珩不是說過麼,他傳消息會通過京城的一個酒樓,怎麼會直接派人過來,而且還是他最親近的屬下。
那勢必真的是十萬火急的事。否則顧珩才會不顧自己被發現的風險,直接給傳消息。
元瑾心中的不安愈來愈強烈,都顧不上讓顧七直接跟說話,直接帶著他立刻前去主帥營帳。
營帳正熱鬧,元瑾卻都他們退下,并讓寶結清了場。
蕭風就覺得有些莫名其妙,元瑾這是這麼了?大家這不是才打了勝仗麼。
帳只剩他們三人,元瑾也不多說了,徑直對顧七說:“行了,你快講吧,你家主人究竟代了你什麼急事。”
顧七就將顧珩代自己的話復述了一遍:“……侯爺說,朱槙早有計劃,這次保定之役不過是假敗。其實早已調兵懷慶,準備從懷慶攻破。他說讓你們早日做好準備,不要到時候被他牽制住了,那便回天乏了。”
元瑾和蕭風的臉很快黑起來。們的確完全被保定牽制住了,本沒有注意到朱槙的作。朱槙這才是個徹底的聲東擊西的做法,倘若他真的將懷慶占領,那他們豈不是被甕中捉鱉!
朱槙,果然不可小覷!
元瑾讓寶結先帶顧七下去安頓后,蕭風才問元瑾:“這人……可靠的住?”
“五叔放心,靠不住的,我絕不會帶到你面前來。”元瑾道,“再者這次的事的確有些蹊蹺,朱槙敗得有些……輕易,不像他的作風,肯定有后招。我們之前以為他是要反殺,如今想想本不是,他是就對保定不興趣,因為保定的確難攻,他不會這麼做。他真正的目標其實是懷慶。所以我們現在要立刻調兵懷慶,不可耽擱。”
如此說來一切就都合理了,朱槙的目標本就不是保定,才能解釋他之前的一系列行為。而元瑾之前一直預的不安也得到了證實。
蕭風也不再托大,立刻上書朝廷,直接從臨近的開封等地先調兵過去。
而他與元瑾,也都來不及回京城。準備直接便從保定趕往懷慶,同時蕭風沉思了一會兒之后,跟元瑾商議說:“阿瑾,我一直在思索一件事。朱槙的厲害,其實有半是在于他邊的那個人。”
元瑾看向他,朱槙邊有這麼多人,他說的哪個?
“清虛。”蕭風說,“你在靖王府應該看到過他,此人高深莫測,不是旁人能及。靖王有他相助,就是如虎添翼。”
元瑾自然也知道清虛的厲害,只是此人忠心于靖王,他們能有什麼辦法。問道:“……難道五叔有什麼辦法除去他?”
這不太可能吧,清虛現在隨跟著靖王,殺他不比殺靖王容易。
“倒也不是。”蕭風沉后說,“我可能……有個別的辦法可以對付他。就是吧……”他嘖了一聲,似乎有些不好說的覺,含糊地說:“總之,你到時候就知道了。”
他這說得越來越玄乎了,這讓元瑾有些不著頭腦。
五叔究竟要干什麼?什麼到時候就知道了,他不會整出什麼幺蛾子來吧?
不過事態急,他要是能出奇制勝,用什麼法子倒是真的不在意。
“對了,今日朱槙似乎也傷了。”蕭風突然說,“傷的比我重些,似乎在腰部,我看都溢了。”
他說著,一邊注意元瑾的表。
燭火幽微,帳中沉寂了片刻。
元瑾只是眼神略微有些波,卻并沒有什麼表的變化。
朱槙的傷并不是新傷,恐怕是他的舊傷口又裂開了。
“戰場上刀劍無眼,傷不是常有的麼。”元瑾道,隨之說,“我先回去歇息了,明日還要趕路,五叔也趕快休息吧。”
說完之后就退了出去,離開了他的營帳。
蕭風一直看著離開的背影,直到徹底消失在他的視線里。
朔風之夜已過,朱槙的軍隊自保定撤退后,一直向南行進,在第三日才停下來駐扎,此時已經到了山西寧山衛。
軍隊駐扎后稍作整頓。畢竟才經過了一場大戰,也不能總是馬不停蹄。山西是朱槙的地盤,很安全。
而且朱槙新裂開的傷口,也需要理一下。
清虛習得一些醫,正在幫朱槙看傷口。
“你這傷口有些不尋常。”清虛看了看他的傷口,正好在腰側,傷口雖淺,卻有些紅腫,仍然有一浸出來。
清虛說,“怎的老是好不,這裂了三次,恐已傷及本。你得好生修養幾日才行。”他說著出手,示意下屬將金瘡藥遞給他,他來包扎。
“無礙。”朱槙卻說,“本來一開始遇刺就沒有好,后來不久宮變時再度裂開。索傷口淺,倒也無事。”他將掩蓋,讓清虛等人退了下去,他自己想好生休息。
但是他閉上眼睛,紛人事卻又饒不了他。
這傷口是怎麼形的,實在是不想再提,皆是他親近之人一一加重的。唯一一個治愈過他的,遠隔千里,對他宛如陌生人。
殺父之仇……
那日之后,朱槙就總是呢喃這四個字。
他是個極其善于聯系何解決問題的人,很多問題其實靠聯系彼此都能融會貫通的解決。唯有元瑾的問題,他怎麼也想不,只是隔了一層關鍵,但是這層關鍵卻是打不通的道,堵塞了所有的思緒。
如果他能解決這個問題,那是不是,便不會有這麼多的……針鋒相對了。
朱槙靜靜地睜開眼,看著自己放在紅木架上的長刀。
他戎馬一生了,作戰不會有人勝得過他,他心里很清楚。薛元瑾若跟他作對……永遠都不會贏。
猜你喜歡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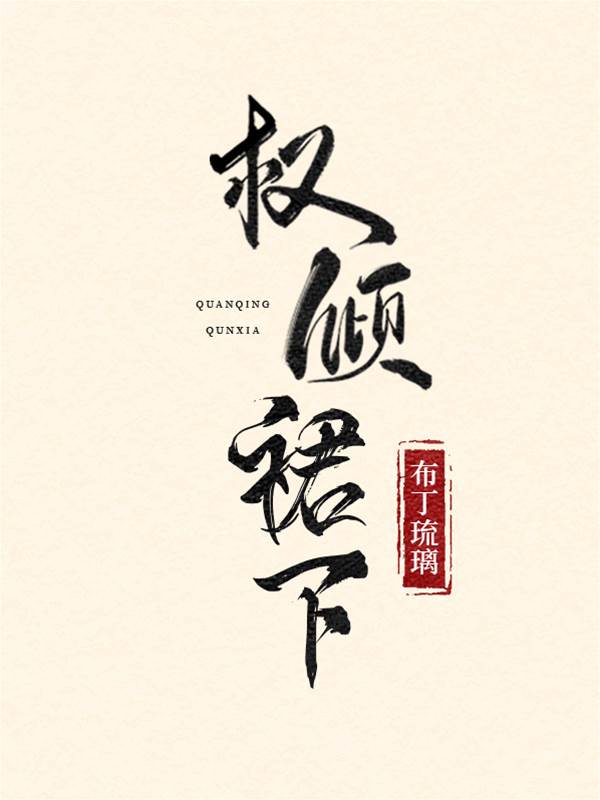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512 -
完結967 章
神醫王妃她拽翻天了
秦語穿越成炮灰女配,一來就遇極品神秘美男。 秦語道,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因為相遇是妹妹陷害,大好婚約,也不過是她的催命符。 秦語輕笑:渣渣們,顫抖吧! 誰知那令人聞風喪膽的燕王,卻整天黏在她身邊.
170.1萬字8 23384 -
完結161 章

太子妃實在美麗
尚書府的六姑娘姜荔雪實在貌美,白雪面孔,粉肌玉質,賞花宴上的驚鴻一現,不久之後便得皇后賜婚入了東宮。 只是聽說太子殿下不好女色,弱冠之年,東宮裏連個侍妾都沒養,貴女們一邊羨慕姜荔雪,一邊等着看她的笑話。 * 洞房花燭夜,太子謝珣擰着眉頭挑開了新娘的蓋頭,對上一張過分美麗的臉,紅脣微張,眼神清澈而迷茫。 謝珣:平平無奇的美人罷了,不喜歡。 謝珣與她分房而睡的第三個晚上,她換上一身薄如蟬翼的輕紗,紅着臉磨磨蹭蹭來到他的面前,笨手笨腳地撩撥他。 謝珣沉眸看着她胡鬧,而後拂袖離開。 謝珣與她分房而睡的第三個月,她遲遲沒來, 謝珣闔目裝睡,等得有些不耐煩:她怎麼還不來撩孤? * 偏殿耳房中,姜荔雪正埋頭製作通草花,貼身宮女又一次提醒她:主子,太子殿下已經到寢殿好一會兒了。 滿桌的紛亂中擡起一張玉琢似的小臉,姜荔雪鼓了鼓雪腮,不情願道:好吧,我去把他噁心走了再回來… 窗外偷聽的謝珣:……
25.7萬字8 76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