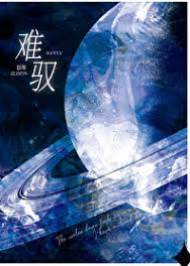《危情泰蘭德》 第1卷 第237章 你到現在,還在關心歐紹文?
黛羚渾無力,掙扎漸漸變得徒勞,直至完全放棄。
昂威抱,固執地不讓從懷中落,仿佛只要稍一松手,便會化作一縷青煙,在他的世界里徹底消散。
“你是不是……從一開始,就已經知道了一切?”
的聲音破碎,融化在淚水里,帶著絕的哀傷。
"一直以來,我在你眼里,是不是就像一只可笑的螞蟻?"
止不住的淚水順著蒼白的臉頰滾落,滴落在他前,灼燒著他的心。
的控訴帶著撕裂般的痛楚。
“如果我是個騙子,那你也一樣,你也是個騙子,徹頭徹尾的騙子,我恨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昂威一下一下著的頭,在頭頂深吻。
“你只要知道,我不怪你殺了阮妮拉,也不怪你利用我對付拉蓬,我心甘愿。”
“我只是......太蠢了。”
“黛羚。”
他的指腹拭去眼角的淚痕,溫又克制。
“明明你要什麼,我都會給,但我卻忽略了你的痛苦,你的掙扎。”
行走在刀尖上的男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對一個人心意味著什麼。
從未想過要墜深淵的起點,卻在與的每一次鋒里,一次次沉淪,直至無法自拔。
當他終于意識到自己已無可救藥地上時,已然無法回頭。
既然無法回頭,那就只有大膽向前走。
黛羚的哭泣漸漸變無聲的噎,昂威收臂彎,單手捧起淚的臉。
月過窗欞,在臉上投下斑駁的影,他看得那樣專注。
Advertisement
“你知道嗎?沒有你的每一天,我都很難過。”
他的聲音在耳畔哽咽,卻極盡克制。
“我真的不了你離開我,就算只有一天。”
“黛羚,我該拿你怎麼辦?我的世界一直下雨......我理不好,從今往后,不要再離開我好不好?”
“你說的話我不信,一個字也不信,你明明我,為什麼不說?我們之間從來不存在仇恨,你可以我。”
黛羚閉雙眼,淚水仍不斷從睫間滲出,搖著頭,發黏在的臉頰上。
“我們不能在一起,除了阮妮拉,還有丹帕,你父親手上沾著我姐姐的...這是一道永遠不過,永遠逾越不過的鴻。”
間溢出一聲哽咽。
“我們在一起,會遭天譴……我已經罪孽深重,不能讓你也萬劫不復……”
“你以為我在乎什麼狗屎天譴?”
他盯著,眼底藏著忍的怒意。
“Leo......”
的呼喚打斷他,緩緩睜開淚眼,在黑暗中描摹他鋒利的廓,冰涼的手指攥住他的袖,仿佛那是在深淵邊緣最后的依靠。
“我只求你,別再傷害無辜了好嗎,以前發生過的我不在乎,但我要寶莉活著。”
的指甲幾乎掐進他的皮,"求求你,讓活著,除此之外我別無所求。"
昂威的發梢還在滴水,冷意順著他的襟滲,但那雙眼睛依舊清明如炬。
他抱著發僵的,輕輕撥開頸間的發,方才的卑微褪去,聲音里帶著不容置疑的決絕和認真。
Advertisement
“黛羚,什麼都可以,但你聽好,寶莉不可以。”
他目幽深,帶著冰冷的理智和講理,“也許對你來說是朋友,但是于我,因為,我損失了上億的貨和幾條人命,我和的這筆賬與你無關,這次,我只是順水推舟,借馬力雍原配的手送上路,沒有親手殺,已經夠仁慈,但你不能開口讓我救。”
“下一個,就是歐紹文。”
他注視著,凝視著所有細小的反應。
“你知道,我和他是死敵,更何況......因為你的關系,所以他也必須死。”
“這是我的原則,誰也無法改變。”
他的語調沒有起伏,像是在陳述一個無可更改的事實。
“你記住,歐紹文和我之間,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你希我死嗎?”
黛羚搖頭,像是終于被現實擊垮,突然掩面哭出聲來,撕心裂肺的哭泣在寂靜的房間里回。
昂威沒有猶豫,將摟進懷里,任由的淚水浸他的襟。
他抬眸向窗外,神凝重,仿佛陷深思。
“以后你會明白,很多事沒有絕對的是非對錯,有些事很復雜,我不下狠手,就無法解決。”
他緩緩收懷抱,聲音微微發啞帶苦。
“我要保護你,黛羚……只有我變得更強大,才能讓你不再走我母親的路。”
昂威的眸微暗,良久,他低聲道。
“你知道嗎?所有人對我的背叛,我都不會原諒,唯獨你,我做不到。”
“我的心,難道你看不明白嗎?”
他出手,想的臉頰,卻被猛然避開。
Advertisement
努力掙,拼盡力氣推開他,眼中是藏不住的糾結和痛楚。
黛羚踉蹌后退,后背撞上桌角,形一晃,險些跌倒。
昂威眸一沉,立刻上前,想要扶住。
卻揚起手,制止了他。
“Leo,你知不知道,”
的聲音帶著固執的堅定。
“就像你說的,你有你的原則,我也有我的原則。”
“我的世界里,本就不是屬于我的選擇,我也沒有資格。”
抬眼,目直視著他,眼底泛著淚,卻無比清醒。
“但我必須保護我的朋友,所有幫助過我為我犧牲過的人,我不可能袖手旁觀,坐視不管。”
房間里陷死一般的沉默,只有清晰的嗚咽。
兩個人僵持著,誰都沒有退讓。
他眉宇微皺,問,“包括歐紹文嗎?”
的抖,沉默良久,終于還是問出了那個最不愿面對的問題。
“Leo……”
“歐紹文在香港的那兩個朋友,是不是你殺的?哈爾濱的周庭禮,是不是你殺的?”
的眼神里有害怕,有試探,還有一自己都未曾察覺的絕。
當然不想聽見答案,甚至不敢去想,但必須問。
昂威的微微一僵,緩緩抬眸,沉默片刻后,他終于直起子,像是從思緒里離出來。
他看著,忽然笑了。
那笑容落寞,又帶著幾分苦,抿了抿。
“你到現在,還在關心歐紹文?”
仿佛早已習慣的立場,卻仍然忍不住心痛。
“如果我說,都不是。”
他收了笑,著,目深沉而痛苦,“你會信嗎?”
Advertisement
“黛羚,在你眼里,我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存在,我真的……好想開你的心,看看里面到底裝的是什麼。”
黛羚沒有說話。
信嗎?
不知道。
可如果不是他,還能是誰呢?
就在這時,門外傳來汽車引擎熄火的聲音,接著是急促的腳步聲,門鈴響起,聲音在沉悶的空氣里格外刺耳。
兩個人對視著,誰也沒有作,仿佛連呼吸都停滯在了這個空間里。
然后,坤達急促的息聲過門口的語音裝置傳來——
“爺,抱歉打擾!你沒接電話,我只能直接過來。有急事,非常急!我在門口等你!”
昂威的睫微微了,視線終于有了些許波。
他緩緩垂下目,掠過桌上的戒指與那束仍帶著水的花,神淡漠地移向別。
沉默片刻,他終于了,緩緩轉,手搭在門把手上,臨走前,只是微微側臉,留下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黛羚,你所謂的朋友,是會殺死我的敵人。”
“你必須做出選擇。”
“當然……如果你不我,那就試著再一次拋棄我。”
話音落下,他推開門,毫不猶豫地離開,步伐堅定,沒有回頭。
猜你喜歡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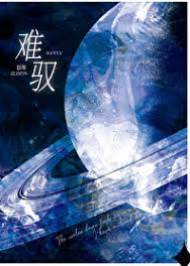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18 11698 -
完結83 章

他似火
一场联姻将两个陌生的男女捆绑在一起,本就签好了协议,两年期满便离婚各奔东西,可是真要离婚了,温言却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平日里宠她上天的男人
15.3萬字8.18 1495 -
完結201 章

噓!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唔唔……”“疼……”“求求你放了我吧……”“沈佑寧你做夢,你這輩子死都是我孟宴辭的鬼。”寂靜的夜里一片漆黑,房間里光線昏暗。一個嬌美的女人被禁錮在床榻,她衣服有些凌亂,臉色慘白,手被皮帶綁著高舉過頭頂。而,男人則是一臉泰然自若地看著女人掙扎。看著她因為掙扎過度,被磨紅的雙手,臉上的情緒愈發冷然,鏡片下的鳳眼里只有滿滿的冰冷。“寧寧你又不乖了。”“是不是想讓我把你的腿給折斷……”“這樣就不會跑了… ...
32.7萬字8 4213 -
完結102 章

迷糊軟妹甜糯糯,醫生老公不經撩
【非女強+閃婚+短篇小甜文】【先婚后愛+甜寵雙潔+溫馨救贖】 本文又名《迷糊蛋和可愛鬼婚后相戀的日常》 理理最近甜食吃多了,牙疼,去醫院掛了個號。 給她看牙的醫生露在口罩外面的眉宇凌厲,如墨染的眼睛實在好看,她忍不住盯著看了好久。 不管對方說什麼,她都乖乖點頭。 等到醫生摘下口罩,理理一愣,哎?這不是自己上個月剛領證的老公嗎? …… 姜淮言平日清冷自持,無欲無求,與人相處不冷不熱,鮮有喜好之事。 直到娶了理理,最愛早晨將她圈進懷里,聽她用將醒未醒的溫軟朦朧嗓音喚他——老公。
19.3萬字8 17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