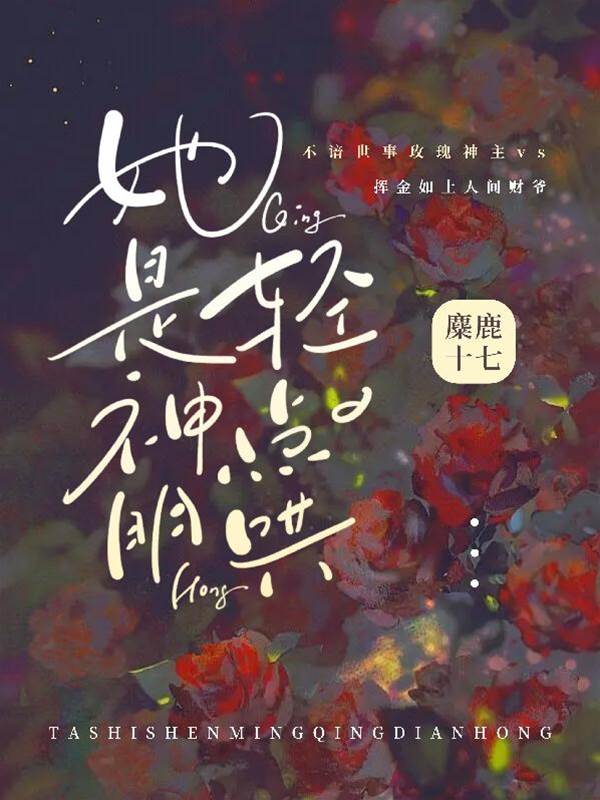《危情泰蘭德》 第1卷 第231章 我要見你
倒一口氣,心的猜想如墜萬米高空,轟然落地,平靜,卻也不平靜。
再次聽到他的聲音,幾乎全僵,寒意瞬間蔓延至四肢,握著電話的手微微抖,卻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他知道還活著,也知道的下落,仿佛一切盡在掌控,從未逃過他的眼睛。
黛羚沒有回應,也沒有掛斷電話,等待心里那口氣緩緩散去。
睜開眼,抖著蜷在墻邊,手從至口,攥著自己的襟,像要窒息,如同溺水之人拼命抓住最后的浮木。
兩顆冰冷的心折磨著彼此,在死寂的沉默中靜待對方先開口。
五秒后,昂威的聲音再次響起,在耳畔無比清晰地回響,就像此刻他就在后。
“……我們結束了嗎?”
“我要你認真回答我。”
剛才,在心里想了一萬遍他會說什麼,會質問什麼,但聽到這句話的那一刻,的心還是不由地痛了一下。
他只問,他們真的結束了嗎……
那麼平靜。
或許是無奈,或許是千言萬語已無從開口,他的嗓音始終寂寥,卻撥的心弦。
此番再次對話,他們已經徹底對立,了仇敵,這一手都是由策劃開始,又親手結束,的確是始作俑者。
可無法心,發生的一切讓恐懼,害怕這一切真的如所猜測,分毫不差。
愣了幾秒,黛羚還是決定面對,話說出口的時候,語氣冰冷,得像一把鋒利的刀。
“你想怎麼樣?”
沒有任何稱謂,生疏又決絕。
那頭傳來一聲輕笑,帶著短促的息。
Advertisement
“我想怎麼樣?”
他緩緩反問,語氣玩味。
“你覺得,我想怎麼樣,是由我說了算嗎?”
“你給了我這麼大的‘驚喜’,然后就這樣一走了之,輕而易舉地背叛了我。”
頓了頓,他低聲喚的名字,像是在咬牙,卻又極度平靜。
“黛羚。”
“……想過背叛我的后果嗎?”
昂威絕口不提阮妮拉的事,字字句句都圍繞他們之間的,仿佛比起那條人命,他更在乎和歐紹文的“茍且”。
他的心如刀割,的驚慌失措,在這一刻,相隔萬里,卻無聲對峙,僵持不下,毫不留地撕扯著彼此的心。
“我從接近你開始就是有目的的,我利用你殺掉拉蓬,我還親手殺掉了阮妮拉,但這些,都是我一個人做的,你別牽連任何人,一人做事一人當。”
黛羚沒有直接問他關于這些天發生的事,不知為何,心懷僥幸,心底仍希不要是他。
他鼻息一哼,冷冷打斷。
再開口,語氣比剛才更加冰冷決絕,不容置喙。
“我要見你。”
這是第一次,從這個男人里聽到如此冷的威脅,對。
“就這麼走了?不管那個在暗地里幫你的人了嗎?你不是說,一人做事一人當?既然這麼有骨氣,那就立刻回曼谷,用你自己來換。”
“如果我見不到你,我會立刻殺了。”
“黛羚,是你我走到這一步的,你怪不了我。”
此話一出,黛羚猛然一。
幫的人?
“Leo……”
口而出。
可電話那頭,卻已然掛斷。毫無遲疑,仿佛厭惡與討價還價。
Advertisement
時間,只留給做出選擇。
黛羚渾一,靠著冰冷的墻壁坐下來,等待意識清醒。
他知道了……有人在幫。
N……
他一定抓了N。
不管是真是假,這一刻,沒法再坐視不管,眼睜睜看著邊的人,一個接一個因而遭牽連。
曼谷,海湖莊園二樓沒開燈的臥室床邊,男人沒在漆黑里的仿佛疲勞至極,好像累得再也沒有什麼力氣。
時隔大半個月,終于聽到了的聲音,莫名的安心,但同時,被背叛的怒意也始終無法平息。
他靠在床沿坐在地毯上耷拉著頭,襯衫的扣子隨意解開,領帶被胡扯落在地,旁邊是一整瓶威士忌,已經空了一半。
握著手機的手無力地從耳邊落,屏幕從通話頁面熄滅,恢復一張照片,黑暗中,格外刺眼。
雪地里,兩道影相擁。埋在那個男人的口,上落滿了雪。那一刻,唯得讓人心碎。
那一刻,還真是唯,如何不人。
整個夜晚,他就盯著這張照片發呆,看得月漸深,暮蒼茫,心里千瘡百孔,百轉千回,剜心挫骨。
不過和幾分鐘的對話,他卻像死了一百回。
他不希死,但這樣好端端的活著,卻是在歐紹文的邊,那種痛,比死更讓人難以忍。
睨向手機屏幕一眼,眉目冷徹骨,下一秒,再也抑制不住,猛地將手機擲向墻壁,七零八落了碎片,跟他的心一樣。
他起,猛地抬踹墻,仿佛嘗不到痛,又仿已經若痛到麻木。
原來,只是不喜歡澳大利亞的雪,喜歡的是哈爾濱的雪。
Advertisement
就像喜歡的,始終是香港,從來不是曼谷。
這個夜晚對他何其殘忍。
在他們曾經恩過的房間里,再沒有繾綣纏綿的話,也沒有難舍難分的糾纏,他來回反復踱步,出火機和煙又扔掉。
好像除了喝酒,他找不到任何辦法熬過這個漫長又令人心碎的夜晚。
他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但他快要瘋掉,瘋到什麼都顧不得。
他只想見,無論付出什麼代價。
——
當天,歐紹文一整天都沒有回太平山的別墅,黛羚知道,他遇到了棘手的難題。
摯友死于非命,因他而起,或許這輩子都無法安心。
更何況,還有一個未出世的孩子……
明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宿命,有些事,終究只能獨自去面對,也無法逃避。
離開之前,把房間里所有關于自己的東西都丟進了垃圾桶,就像從沒來過這里一樣纖塵不染。
離開之前,也沒有再回頭看一眼,仿佛一場短暫而安穩的夢。
抵達曼谷時,夜如墨。
剛出機場,一輛悉的勞斯萊斯已經靜靜等候,阿努站在車旁,和無數次一樣,在夜幕下等待。
他們四目相對,他的眼神卻沒怎麼變,起始與終結,這個忠心的手下又究竟知道多呢?
“黛羚小姐,爺在等你。”
輕輕點頭,坐進車,過車窗向曼谷的夜空。
一彎冷月,與香港的夜相似,又不相似。
終究還是回來了。
但這一次,除了這輛車,一切都已悄然改變。
曾經,是被保護的對象。
而現在,是被押解的囚犯。
Advertisement
去赴一場等待已久,為特意準備的凌遲。
車子沒有駛向海湖莊園,而是拐向海邊,駛一僻靜的港口。
一個小時后,車穩穩停下。
抬眼去,夜下的港口,幾盞昏黃的路燈孤零零地亮著,投下微弱的暈,在的空氣里晃不定。
不遠,深夜的木板碼頭盡頭,一輛黑跑車靜靜橫陳而立,孤獨地映在海面上,映襯出沉沉夜。
男人高大的軀立在車旁,背對著來的方向,雙手落袋,迎著大海的浪,一如既往灑的姿,剪影沉默不語。
一人一車,就那樣一不地站著,即便氣場如他一般強大,此刻,那份彌漫在空氣中的落寞仍然悄無聲息地將他半個子吞沒。
黑皮夾克勾勒出他英的姿,比記憶中更顯鋒利,也更遙不可及。
仿佛又回到了初見的那一刻的陌生。
猜你喜歡
-
完結1434 章

倒貼前妻:總裁逼婚99次
顧念喜歡了池遇很多年。只是兩個人從結婚到離婚,池遇都從來沒明白過她。好在她從來不是為難自己的人。她有錢有顏,怎麼還找不到個眼睛不瞎的,能把她放在心上。所以,她不堅持了。只是她身邊開始鶯鶯燕燕的時候,這從前瀟瀟灑灑的前夫哥,怎麼就突然回頭了。怎麼就突然說她也不錯了。怎麼就突然說後悔了……...
263.1萬字8.18 308249 -
完結180 章
八零之改嫁隔壁老王
冬麥男人炕上不行,但她不懂,一直以為就這樣,日子挺好。隔壁那個復員軍人沈烈娶媳婦,喜宴還沒結束,新媳婦鬧著要離婚。她去幫著勸,新媳婦說“他又兇又狠又不愛說話,還窮得要命!”冬麥推心置腹“沈烈部隊立過功,見識廣,以后改革了,好好經營,日子肯定能過好。”誰知道人家一口懟過來“那你怎麼不嫁?要嫁你嫁,別勸我!”她哪里知道,人家新媳婦剛從一年后重生過來的,人家知道沈烈馬上要栽坑里,人家悔悟了不要愛情要鈔票了。冬麥勸說無果,鄰居離了,冬麥生不出孩子被婆家嫌棄,也離了。后來,她嫁給了那個被嫌棄窮的鄰居沈烈...
86.1萬字8 9086 -
完結1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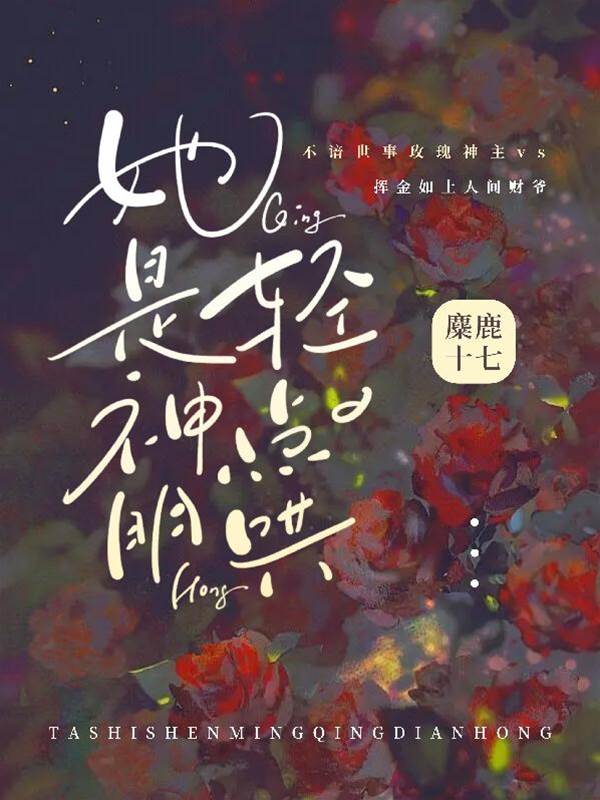
她是神明輕點哄
[不諳世事玫瑰神主VS揮金如土人間財爺][先婚後愛 雙潔+情有獨鍾+高甜]“她牽掛萬物,而我隻牽掛她。”——柏聿“愛眾生,卻隻鍾情一人。”——雲窈雲窈有個好的生辰八字,擋災的本事一流。不僅讓她被靈蕪城的豪門喬家收留,還被遠在異國,家財萬貫的柏老爺給選中做了柏家大少爺柏聿的未婚妻。—雲窈喜歡亮晶晶的寶石和鑽戒,豪門貴胄笑話她沒見過世麵,柏總頓時大手一揮,寶石鑽戒一車一車地往家裏送。—雲窈有了寶石,想找個合適的房子專門存放,不靠譜的房產中介找上門,柏太太當機立斷,出天價買下了一棟爛尾樓。助理:“柏總,太太花了十幾億買了一棟爛尾樓。”男人麵不改色,“嗯,也該讓她買個教訓了。”過了一段時間後,新項目投資,就在那片爛尾樓。柏聿:“……”—柏聿的失眠癥是在雲窈來了之後才慢慢好轉的,女人身上有與生俱來的玫瑰香,他習慣懷裏有她的味道。雲窈卻不樂意了,生長在雪峰上的玫瑰神主嫌棄男人的懷抱太熱。某天清晨,柏太太忍無可忍,變成玫瑰花瓣飄到了花盆裏,瞬間長成了一朵顏色嬌豔的紅玫瑰。殊不知,在她離開他懷抱的那一瞬就已經醒過來的男人將這一切盡收眼底…他的玫瑰,真的成精了。
23.9萬字8 7712 -
完結729 章

大佬絕嗣!我一夜懷上他兩個崽
“你體力不行,體驗感不好,我要換人!” “你想換誰?” “換個體力好的!” 男人沉着臉,身體力行讓許初願感受,他體力有多驚人! 結婚三年,許初願遲遲懷不上孩子,只能以這種方式,刺激丈夫! 一夜荒唐,誰知,還沒來得及懷上孩子,就被一紙離婚書,砸了滿臉。 男人說,“我孩子的母親,是誰都行。” 六年後,她攜龍鳳胎迴歸,逆天醫術、專業考古學者、珠寶鑑定師……還是首富家的千金,多重馬甲身份,驚爆人眼球。 而薄大總裁,被爆絕嗣。 後來,在許初願帶娃即將嫁給別人時,他將她抵在房間角落,眼眶泛紅,“初寶,我孩子的母親,只能是你!”
141.8萬字8.18 88532 -
完結151 章

這個校草有點野
安中運動會看臺上人聲鼎沸,個個都在賭今年男子三千米冠軍花落誰家。許微喬終于偷了空子躲在裁判員那迎接某人沖破終點線,不想某陸姓選手一個沒剎住,栽在了許微喬懷里還就地滾了一圈,許微喬被攬進了一個熱烈的懷抱里,混子摔了外面那層玩世不恭的殼,朝她笑。 “完了,栽你身上了。” 純又野的千里轉校生×孤高的偏執清冷爺
28.1萬字8 12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