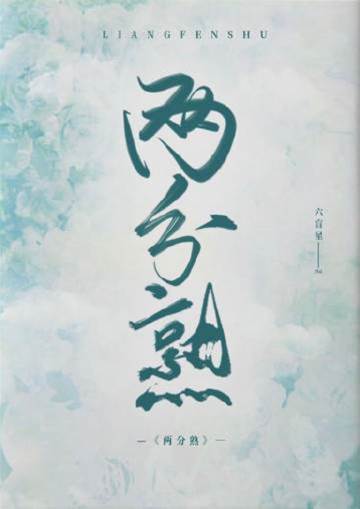《誘她臣歡》 第1卷 Ch.146.“認定了就是我兒子”二更合一
盛矜北在深海里大腦長時間缺氧,醒來已經是五天后。
.......
元城。
細碎的從枝椏的隙中進來。
盛矜北在一片混沌中醒來,耳邊約傳來一陣溫的哼唱聲,像極了小時候父親給唱的搖籃曲。
線刺眼。
下意識地瞇起了眼,視線一片模糊。
男人側對著,一藍白條紋的病號服,懷中小心翼翼地抱著一個小小的襁褓。
姿勢很標準。
他低頭看向懷中的寶寶,角止不住地上揚。
“小家伙,爸爸。”
寶寶的小手在空中抓來抓去,吐著小舌頭,像是在回應他。
盛矜北的嚨像是被火燒過一樣干,呼吸間帶著一淡淡的消毒水味道,輕聲喚,“書禮...”
提到這名字。
接著。
大腦突然像是被撕裂一般,跳海前的記憶似開機代碼般一下子涌。
每一幀都刻骨。
親眼見證了傅書禮極端地自殺式死亡。
一下從床上驚坐起,“書禮——!”
傅司臣微微一僵,迅速將寶寶輕輕放在一旁的嬰兒床上。
寶寶小一癟,發出幾聲不滿的哼唧,但很快又安靜下來,繼續抓著空氣玩。
傅司臣快步走到床邊,俯抱住,大掌的頭。
“都結束了,別怕。”
盛矜北口急劇起伏,泛紅的眼眶蓄滿了淚水,“書禮...書禮...”
“他真的死了嗎?
傅司臣不停地上下著的背,“真的,都已經過去了,別想那麼多。”
盛矜北心一,也跟著抖得厲害,大滴大滴滾燙的眼淚落下來砸在他的手臂上。
而后。
一把推開他,雙手攥住床單。
傅司臣眉頭鎖,想說什麼,卻覺腔似乎被一塊巨石狠狠制,說不出話來。
Advertisement
盛矜北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現在的是多麼失態。
雙手捂臉,痛哭。
不輕輕地問了問自己,他永遠不會回來了嗎?對嗎?
那麼年輕鮮活的一條生命。
在年的影下,最終還是走上了不歸路。
良久,緩緩啟,“他的尸在哪,我想去看看他。”
傅司臣繃了角,“海浪太大,救生員在海上找了兩天都沒有找到他的尸。”
盛矜北睫羽輕,“所以是死無全尸,對嗎?”
傅司臣沒吭聲。
他下腔中翻涌的緒,把連人帶被子抱進懷里,摟得死死。
聲音酸。
“別哭了,好不好,老婆。”
盛矜北猛地抬起頭,紅著眼睛死死瞪他,“誰是你老婆?我跟書禮結婚了,書禮才是我老公。”
傅司臣子一。
悶,氣短,心口疼,傷口疼。
克制著,似乎是忍了又忍。
“好,很好,非常好。”
盛矜北子不由地往后瑟了一下,以為他又要發瘋了。
然而。
他卻沒有,一點點拭掉咸的眼淚,“不管怎麼樣,我的老婆就只有你一個。”
盛矜北,“我給誰當老婆都不給你當。”
傅司臣憋悶,“沒關系,我心里認定了你。”
盛矜北深吸氣,“你去找你的關小姐,才是你明正娶的未婚妻。”
傅司臣委屈,“老婆,我以前那是裝的....”
“叩叩——”
門外傳來輕輕的敲門聲,打斷了兩人的說話聲。
醫生推門而,手里拿著病歷本。
“傅先生。”醫生清了清嗓子,“您該回病房做檢查了,您的傷口需要定期觀察,不能耽誤。”
傅司臣頭也不抬,“不去。”
醫生早知會是這種結果,也沒太驚訝。
畢竟這幾天,他也沒真正在自己病房待過。
Advertisement
憑借醫生的職業素養。
他還是認真勸誡,“傅先生,您的狀況不容樂觀,必須按時檢查,如果您不配合,可能會影響恢復。”
傅司臣冷聲回應,“我說了,不去。”
醫生周皺起了眉頭。
僵持不下。
盛矜北這才端詳起他。
他上病號服的領口微微敞開,約能看到繃帶的邊緣,臉蒼白,眼底淡淡的青黑,下滋生出濃的胡茬...
盛矜北語氣冷,“傅司臣,你回去吧,我現在不想看到你。”
傅司臣眼神黯了黯,啞聲說,“我們分開已經很久了,從你離開定京的那天起,到今天是第208天,我沒有一天不在想你。”
“我現在只是想留下來看著你,守著你,也不可以嗎?”
“不可以,你這樣只會讓我更厭惡你。”
盛矜北別過頭,不去看他。
傅司臣定定看著,黑眸里點稀疏破碎。
他晃了晃,腰桿也彎了下去,腳步虛浮地朝門外走去。
頹唐,落寞,孤寂。
就在他即將踏出房間之際——
孩子‘哇’地一聲哭了。
盛矜北聞聲顧不上自己正在輸,掀開被子就要下床。
可有人比快一步。
有什麼東西在眼前‘嗖’一下就過去了。
傅司臣抱起襁褓中的小嬰兒,邊拍邊哄,“寶寶乖,爸爸在這里,不哭不哭。”
“.......”盛矜北致的眉眼染上些許怒氣,“傅司臣,孩子不是你的。”
傅司臣輕哄,“不管是不是我的,我都認定了,他就是我兒子,而且,你現在還很虛弱,應該好好養,這幾天我替你帶他。”
盛矜北沉聲,“我可以找育嬰師,不需要你。”
傅司臣輕輕晃了晃手臂,“育嬰師哪有親爹照顧得好。”
小嬰兒似乎真的被他安住了,咂著小,眼睛一眨一眨地看著他。
Advertisement
他欣喜,“北北,你看,他好喜歡我,他出生我都沒怎麼抱過他,讓我留下來帶他幾天,等你恢復好了,我就走。”
盛矜北氣得口起伏,后背開始冒虛汗。
攥了拳頭,猩紅著眼睛看他。
“傅司臣,你到底知不知道,什麼尊重?你沒看出我不愿意嗎?我不愿意看見你,不愿意你再次進我的生活。”
傅司臣微微一僵,心臟升起麻麻的疼痛。
“對不起,是我的錯,是我太著急了。”
他眼神黯了黯,低頭看著懷里的小嬰兒,孩子的眼睛一眨一眨地看著他,小手抓著他的手指。
似是在無聲挽留。
他沉默了很久,終于低聲說道,“好,我走。”
說完,傅司臣輕輕將孩子放回嬰兒床,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寶寶乖,爸爸...先走了。”
盛矜北別過頭,不去看他。
傅司臣最后深深看了一眼,轉離開了房間。
“砰——”
一聲悶響。
伴隨著醫生的驚呼,“傅先生!快來人!病人暈倒了!”
盛矜北聽到靜,下意識朝門口張。
莫名心煩。
隨即一下掀開被子,將自己整個人蒙了進去。
不聽不看不念。
可是,門外的嘈雜聲不止,分外清晰。
“傅先生!傅先生!能聽到我說話嗎?”
“快!準備氧氣!他的況很不穩定!”
........
大約過了兩分鐘,外面聲音突然停止了。
不知為何盛矜北心跳的特別厲害。
攥了被子,心里掙扎。
最后狠了狠心,歸于平靜。
一連兩天,病房只有傅司臣安排過來的護工和育嬰師。
而傅司臣再也沒有出現過。
像人間蒸發了一樣。
盛矜北右眼皮一直跳,消極緒不管不顧在腦海中炸開。
他不會死了吧?兩天火化都來得及了。
Advertisement
不知為何,現在變得特別悲觀。
夜深人靜。
盛矜北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著。
終于,掀開被子,輕手輕腳地下了床。
看了一眼嬰兒床里睡的寶寶,了他的小臉,然后披上一件外套,悄悄走出了病房。
過門上的玻璃窗。
看到傅司臣躺在床上,呼吸罩覆蓋了他大半張臉。
沒死。
沒死就好。
轉離開,像不曾來過。
盛矜北是第四天出院的。
林兮聽說回了元城,親自來接,兩人好久沒見了,一見面什麼都不說,只是激地抱著一味地流眼淚。
即使一句話不說。
林兮也知道吃了多苦,盛矜北也知道跟著了多心。
林兮幫收拾東西,“醫院這種地方,能待就待,出院手續辦完了,我們回家慢慢說。”
育嬰師從盒子中拿出一雙嶄新的鞋,底,包著腳后跟的,“盛小姐,外面風大,您還在月子,把這個換上。”
盛矜北瞧著鞋可,便接了過來,碼數正好。
隨口夸了句,“你也太會買了,這麼合適。”
育嬰師解釋,“不是我買的,是傅先生托人送過來的,還有帽子。”
盛矜北繃了角,沒吭聲。
林兮跟樓宴生對視一眼,不著痕跡說,“宴生,你不是說傅司臣那天暈倒,直接被送進了重癥監護室,好像是因為傷口染,加上過度勞累,況嚴重的,他現在怎麼樣了?”
盛矜北正在收拾嬰兒用品,面上沒有多余的表。
樓宴生輕咳一聲,“我也不清楚,還沒去看他,應該死不了。”
盛矜北抱起孩子,“走吧,收拾好了。”
“.......”林兮張了張,把剩下的話咽了下去。
找個機會再說吧。
離開元城之前,盛矜北曾買過一套小面積的兩居室,也算有個自己的小家。
之前在陳屹那投資二手車行的錢,不賺了,而且翻了十幾倍。
辭掉了傅司臣安排的育嬰師,自己花錢請了一位經驗富的月嫂,幫照顧孩子。
不想再和傅司臣有任何瓜葛。
哪怕是他安排的人,也不想再接。
心里清楚,自己必須徹底獨立,才能真正開始新的生活。
算著日子,母親還有半個月就刑滿釋放。
再也不用制于人,看人臉。
搬進新家的第二天。
盛矜北正抱著孩子在臺上曬太,門鈴突然響了。
月嫂王姐去開門,神有些猶豫,“盛小姐,外面有位士...說是您的母親。”
盛矜北愣了一下,心里猛地一。
快步走到門口,果然看到了那張悉的臉,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
“媽——”
把孩子給王姐,撲進母親的懷里抱住,激地說不出話。
“您怎麼...怎麼提前出來了?不是還有半個月嗎?”
周淑清鼻尖泛酸,輕輕著的頭發,“乖兒,表現良好減刑了,那麼久沒見,我都不敢想,我的兒都當媽媽了。”
盛矜北拉著走進屋,歡喜的不得了。
“減刑?怎麼這麼突然?”
要知道之前可是從未有過一次減刑的況。
周淑清輕輕拍了拍的手,頓了頓,“北北,其實...這次減刑,是傅司臣幫的忙。”
盛矜北笑容僵在臉上,攥了手指。
一言不發。
周淑清說,“北北,出獄后我和他聊過一次,聊了很久,他讓我別告訴你,怕你心里有負擔,可我覺得...你有知權,畢竟傅家是傅家,傅司臣是傅司臣,他們不一樣。”
盛矜北心里輕輕咯噔了一下。
“可他們是一家人,傅家害死了我的爸爸。”
周淑清一驚,“你怎麼知道?”
盛矜北說,“其實我一直不信我的爸爸是個癮君子,有次在傅宅聽見了傅廷梟夫婦的對話。”
說到這,周淑清漆黑的眸子涌著別樣的緒。
盛矜北捕捉到,眼睛異常明亮,“媽,你早就知道是不是?”
周淑清沉默。
沉默等于默認。
盛矜北反握住的手,“媽,我現在手里有傅家的犯罪證據,這次回來,我不想等了。”
周淑清,“你想怎麼做?”
盛矜北眼眸微瞇,“我要實名舉報傅家,我一定要讓他們得到法律的制裁。”
周淑清攥住的手,“如果有證據,媽媽支持你,但傅家心狠手辣,一定要做足準備才行。”
盛矜北一愣,原來被家人無條件支持是這種覺。
從此再也不是孤一人。
夜風微涼,盛矜北走到臺,隨手將晾曬的小服收下來,目不經意間掃過樓下。
昏暗的路燈下,一輛黑轎車靜靜地停在那里。
幾乎要融于黑暗。
約約看見一抹猩紅在夜中忽明忽暗。
沒當回事。
午夜時分,盛矜北再次醒來,喂完去上廁所。
路過窗邊時,又看了一眼樓下。
那輛車居然還停在那里,閃爍著猩紅。
不知道了多支煙。
的心猛地一沉。
莫非是…
傅司臣?
猜你喜歡
-
完結59 章

和冷漠老公互換后的豪門生活
本書章節內容有問題,請大家在站內搜索《和冷漠老公互換后的豪門生活》觀看完整的正文與番外~ 別名:和陰鷙大佬互穿后我躺贏了,和陰郁大佬互穿后我躺贏了 豪門文里,陰鷙強大的商業帝王意外成了植物人,沒人知道他的意識清醒地困在身體里。寧懿從苦逼末世穿來成了他的炮灰妻子,因為替嫁姐姐而心態扭曲,正要虐待殘廢老公。然后,他們倆互換了身體。看著寧懿代替自己躺尸,男人滿是惡意:“這滋味,如何?”…
26萬字8 7046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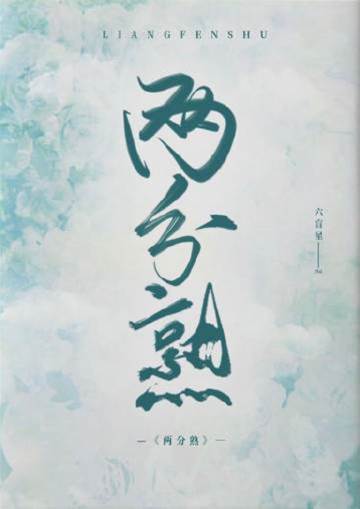
兩分熟
大學時,阮云喬一直覺得她和李硯只有兩分熟。學校里他是女粉萬千、拿獎無數的優秀學生,而她是風評奇差、天天跑劇組的浪蕩學渣。天差地別,毫無交集。那僅剩的兩分熟只在于——門一關、窗簾一拉,好學生像只惡犬要吞人的時候。…
25.3萬字8 6408 -
連載272 章

二婚撩惹
我從不相信謝志清出軌,直到接了一通陌生的電話。“我老婆出軌了,出軌對象是你老公。” 短短幾個字,擊碎我婚姻幸福的假象。 親眼目睹老公和情人進了酒店,我與情人的丈夫達成復仇的盟友。 只是情難自抑,離婚后我倆又該何去何從......
53.4萬字8 365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