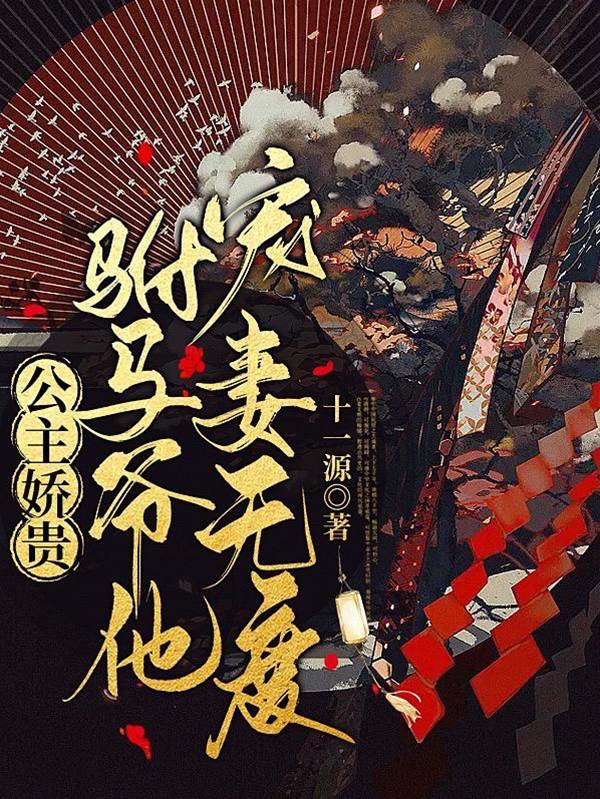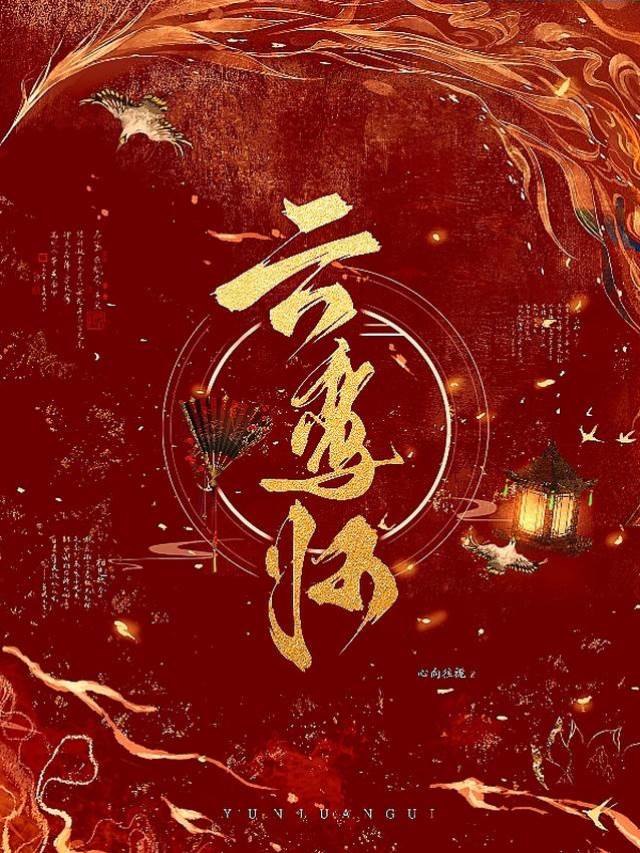《戲夢入君心》 第1卷 第41章 玉佩
段君彥坐在裴夢桉邊,手里把玩著那塊玉佩。
床頭的燈調的很暗,月灑進來混跡其中。
段君彥想著大夫剛才說的話。
裴夢桉有心理問題。
但平日里本就看不出來。
得帶他去看一看。
又想到許意剛剛說的。
裴夢桉很喜歡自己嗎?
段君彥想著,不自覺的勾了。
大概是的吧,不然怎麼會張口閉口喜歡十爺,一舉一勾引十爺呢。
是很早就喜歡了嗎?
不然怎麼會收著他的玉佩呢。
并沒有因為自己的玉佩莫名出現在了別人那里而到有一一毫的不適。
反而覺得心不錯。
段君彥把裴夢桉的手小心翼翼的握進掌心給他暖著。
若是旁人拿了十爺的玉佩,恐怕早就被剁了手了。
哪里還能在十爺面前躺著讓十爺給暖手?!
裴夢桉醒來的時候,差不多是后半夜了。
手上的針已經在一個小時之前被拔掉。
這期間,段君彥聽了大夫的話,一直在用溫熱的巾輕輕給裴夢桉敷著手背。
他太瘦了,扎了這麼一會兒針,手背就有些腫。
段君彥看著心疼。
他將裴夢桉的手放在自己的膝蓋上,給他捂著,暖著,就這樣不知過了多久,突然覺到了自己手心中的輕。
段君彥一回頭,正對上裴夢桉瑟迷茫的雙眸。
“醒了,難嗎?”
段君彥抬手了裴夢桉的額頭。
Advertisement
“不難了。”
裴夢桉開口回答,聲音很小。
一睜眼看到的是段君彥,而不是漆黑的深淵,這讓裴夢桉心很好,原本倉皇的眸底帶出了些笑意。
“謝謝您,來找我。”
這一句話狠狠的刺到了段君彥心里,一下子讓他難的有些不過氣。
“裴夢桉,是我把你害這樣的。”
你該怪我,罵我,指責我,唯獨不該謝謝我……
裴夢桉笑著搖頭,輕輕撓了撓段君彥的掌心。
“十爺,親親我~”
裴夢桉剛醒過來,還很虛弱,本不該這樣勾人。
但他實在是被剛剛的形搞怕了,這時候段君彥帶給他的暖意更能讓他覺到真實。
段君彥被他的心,但也不敢太過于放肆,只是俯在那的瓣上蜻蜓點水的上一。
就算這樣,裴夢桉也已經很滿足了。
他往里面挪了挪,眼神示意的看向了自己邊的空位。
段君彥便起了,了外套上了床榻,把裴夢桉摟進懷里。
“裴夢桉……為什麼你會有我的玉佩?”
問題太多了,段君彥一時間不知道如何開口,思來想去決定先從最簡單的開始問。
但他卻如何也沒想到,這個他以為是最簡單的問題,卻是最復雜的。
裴夢桉也沒想到,段君彥會看到了這枚玉佩。
雖然他確實沒刻意去藏,但他也不覺得十爺是會去翻人東西的人。
Advertisement
所以一直放著,也沒有特別的去管。
他哪里知道,在段十爺的心里,裴夢桉就是他的,裴夢桉的一切自然也該是他的,有何看不得?
裴夢桉看著面前的玉佩沉默了好一會兒。
就在段君彥以為他不會回答了的時候,裴夢桉終于開了口。
“您不記得了嗎?”
段君彥拿著玉佩的手一頓,腦中莫名閃過了風雪加的畫面。
他只記得,這玉佩已經失了很久,至于什麼時候失的又是失在哪里,卻是記憶已經模糊了。
裴夢桉抬頭,看到了段君彥眸底的迷茫,微微有些失落,但也是意料之中。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兒了,您不記得也是很正常的。”
裴夢桉手,從段君彥手中過了那塊玉佩握在自己手里。
他的手上還有一點無力,但依舊沒有放手。
眸底是懷念,作是珍重。
“那天,下了很大的雪,是小寒……”
那會兒,裴夢桉還不裴夢桉,他還只是個沒有名字的流浪兒。
寒風刺骨。
流浪的孩子在墻之中,盡可能的躲避著冷意。
太冷了,他真的快要被凍死了,已經兩天沒有吃東西了,了就抓雪吃,垃圾桶里都翻不出什麼殘渣。
肚子里沉甸甸的,冷的發。
他環抱著自己,卻如何也汲取不了一一毫的暖意。
禍不單行,年節前幾個富家子兒結伴出來找樂子,找到樂子之前,先在墻之中找到了蜷一小團的孩子。
Advertisement
“呦,快瞧瞧,有只小病貓呢。”
“哪呢,哪呢?我看看來!”
他被凍得意識都有些迷茫,耳朵里霧蒙蒙的聽不太真切東西,還沒反應過來什麼呢,就被人拽著胳膊抓了出去。
富家子弟的跟班們總是很有眼力見兒。
他被重重的甩在了雪地之中,本就單薄的人更是脆弱,他一時之間甚至都爬不起來。
周圍的人笑一團,惡意來的毫無理由。
像他這種螻蟻,為富家子弟消遣的玩都是榮幸至極。
誰會在意螻蟻的命呢。
幾個年對著地上的孩拳打腳踢,嬉笑辱罵著,仿佛這就是他們今夜的樂子。
“別……嗚嗚,別打了……”
他努力的把自己蜷一團,護著自己的頭,小小的子不斷的發著抖,因為疼痛,也因為寒冷。
小小年紀的孩子,就已經承盡了人間苦難。
他不明白自己做錯了什麼,為什麼要遭這樣的折磨。
可他更不知道的是,自己的求饒聲,更是那些蛇蝎心腸之人的調味劑。
孩小聲的嗚咽著,幾乎喪失所有力氣。
其中一人停了作,另外幾人也跟著停了下來。
“怎麼了,哈哈哈哈好玩的啊,這不比那些歌舞廳的有意思?”
率先停下來的那人皺了皺眉。
“這樣多沒意思啊,顯得我們欺負人似的。”
孩聽不真切,但他下意識的認為這些人停手是放過他了,于是他努力的向外爬去,想要逃離這里。
Advertisement
整個人在雪地里趴了太久,已經凍得僵,手腳都沒了知覺,卻依舊在努力向前。
厚重的雪層下面是尖銳的石塊兒。
他一手摁上去,被刮出了跡,殷紅的落在潔白的雪上格外顯眼。
只聽那人殘忍至極聲音響起,“不如我們來比比看,誰先把他打到出不了聲,怎麼樣?”
猜你喜歡
-
完結1020 章

我閃婚了個億萬富翁
被催婚催到連家都不敢回的慕晴,為了能過上清靜的日子,租了大哥的同學夜君博假扮自己的丈夫,滿以為對方是個普通一族,誰知道人家是第一豪門的當家人。……慕晴協議作廢夜君博老婆,別鬧,乖,跟老公回家。
176.1萬字8.18 319119 -
完結12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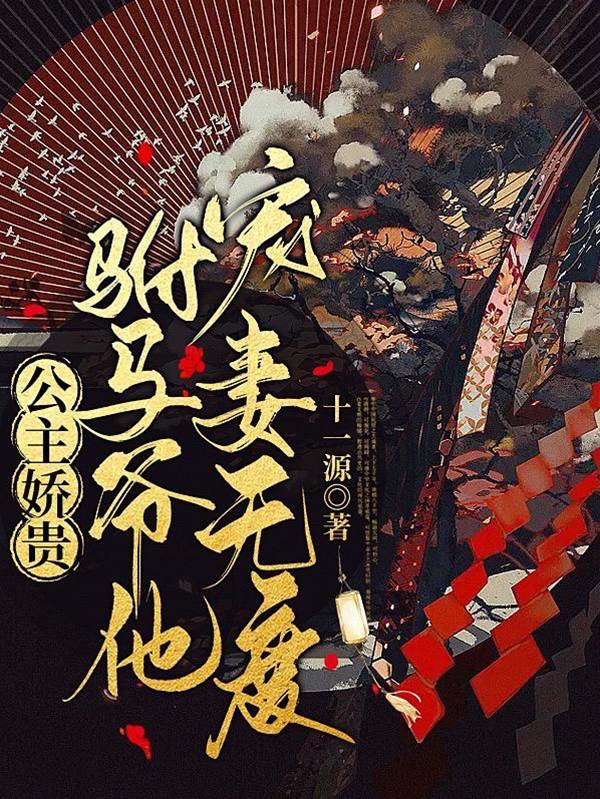
公主嬌貴,駙馬爺他寵妻無度
【1v1 、甜寵、雙潔、寵妻】她是眾星捧月的小公主,他是被父拋棄的世子爺。幼時的他,寡言少語,活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中,是小公主一點一點將他拉出了那個萬丈深淵!日子一天天過,他成了溫文儒雅的翩翩公子,成了眾貴女眼中可望不可及的鎮北王世子。可是無人知曉,他所有的改變隻是為了心中的那個小祖宗!一開始,他隻是單純的想要好好保護那個小太陽,再後來,他無意知曉小公主心中有了心儀之人,他再也裝不下去了!把人緊緊擁在懷裏,克製又討好道:南南,不要喜歡別人好不好?小公主震驚!原來他也心悅自己!小公主心想:還等什麼?不能讓自己的駙馬跑了,趕緊請父皇下旨賜婚!……話說,小公主從小就有一個煩惱:要怎麼讓湛哥哥喜歡自己?(甜寵文,很寵很寵,宮鬥宅鬥少,女主嬌貴可愛,非女強!全文走輕鬆甜寵路線!)
21.6萬字8 12884 -
完結78 章

她與白玫瑰
名門紈絝少爺X頹廢暴躁少女眾所周知,京城有所大名鼎鼎的天花板貴族高中,同時也是官二代和富二代的聚居之地——京城二中。京城首富江家的獨子江延灼,為人桀驁張揚,暴戾紈絝,又野又狂。偏偏這位不可一世的校霸一穿上校服,不光眉眼幹幹淨淨,還會規規矩矩地戴個騷裏騷氣的金邊眼鏡。冷菁宜頂著冷兮芮的名字,轉進京城二中的高二零班之前,已經見過這位桀驁不馴的校霸,次次都是大型場麵。那個操著一口濃重京腔,右耳戴著金紅色耳鑽,站在濃豔血腥氣裏的少年,從此深深地刻在了她的腦海裏。——他既是神壇上神聖不可侵犯的神明,高傲自尊,得萬千寵愛。他又是無法無天窮兇極惡的撒旦,暴戾偏執,強勢紈絝,不可一世。——她來時,她是他捧在心尖上的祖宗。她走後,他成了孤獨又璀璨的神明。——In My Barren Land,You Are My Only White Rose.在這萬物荒蕪的陣痛世界,你是我心尖上一塵不染的白玫瑰。——“祖宗,我不怕死,我隻怕你疼。”“來做我的江太太。”——在這路遙馬急的喧囂人間,顛倒黑白的真假世界,原來真的會有人跟你八年不聯係,還一直深愛你。
24.3萬字8 1665 -
完結168 章

閃婚而已[先孕後愛]
江織大四畢業第一次去酒吧,第一次喝醉酒,第一次撲進男人懷裏,第一次一夜風流。 時隔一個月,就“驚喜”的發現自己懷孕了。 她不是那種自怨自艾的人,思考了不過幾分鐘,就從角落裏翻出那夜收到的名片。 江織沒想到男人更乾脆。 隔了一天,新鮮的紅本本就領到手了。 *小劇場/// 從前在商業新聞才能看到的巨佬此刻就在躺在身邊,這種感覺實在有些不真實。 江織沒忍住輕輕踹了他一腳。 男人立刻翻身起來,動作熟練的握住她的小腿,低聲,“又抽筋了?” 江織認真的打量他,“你有沒有那種特別漂亮的女祕書?” 畢竟言情小說都是這麼寫的。 男人皺了一下眉,仔細想了一下最近似乎沒有哪裏惹到這個小祖宗。 他低聲下氣的哄着,“寶寶,我真沒有,不信你明天來集團檢查,今晚能不能不讓我睡書房。”
25.2萬字8 13285 -
完結2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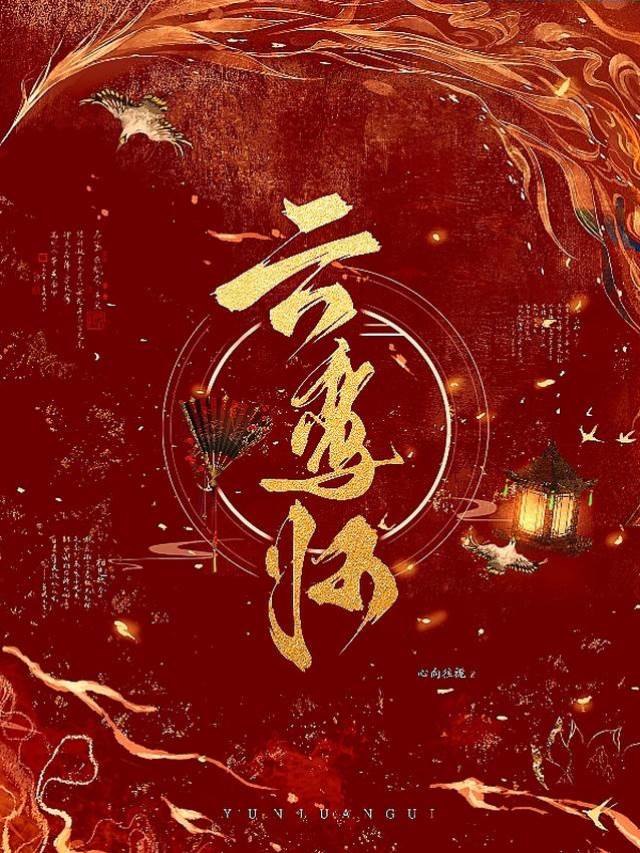
雲鸞歸
【黑蓮花美人郡主&陰鷙狠厲攝政王】[雙強+甜撩+雙潔+虐渣]知弦是南詔國三皇子身邊最鋒利的刀刃,為他除盡奪嫡路上的絆腳石,卻在他被立太子的那日,命喪黃泉。“知弦,要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了。”軒轅珩擦了擦匕首上的鮮血,漫不經心地冷笑著。——天公作美,她竟重生為北堯國清儀郡主薑雲曦,身份尊貴,才貌雙絕,更有父母兄長無微不至的關愛。隻是,她雖武功還在,但是外人看來卻隻是一個病弱美人,要想複仇,必須找一個位高權重的幫手。中秋盛宴,薑雲曦美眸輕抬,那位手段狠厲的攝政王殿下手握虎符,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倒是不錯的人選。不近女色,陰鷙暴戾又如何?美人計一用,他照樣上鉤了。——某夜,傳言中清心寡欲的攝政王殿下悄然闖入薑雲曦閨閣,扣著她的腰肢將人抵在床間,溫熱的呼吸鋪灑開來。“你很怕我?”“是殿下太兇了。”薑雲曦醞釀好淚水,聲音嬌得緊。“哪兒兇了,嗯?”蕭瑾熠咬牙切齒地開口。他明明對她溫柔得要死!
42.5萬字8 21820 -
連載390 章

離婚后,姜小姐光芒萬丈
【男主重生追妻火葬場+女主馬甲+爽寵文+復仇】一場大火,讓姜稚看清了婆家人真實嘴臉。 這一切皆因一個人的出現。 第一次見面,他說:“你老公出軌了。” 第二次見面,他說:“一周之內趕緊離婚。” 第三次見面,他說:“你那麼善良,怎麼跟壞人斗,不如嫁給我,多個人多份力量。” 小女人這回卻堅定地搖頭:“算了,咱們還是各憑本事,斗成老幾算老幾吧,再見!” 她瀟灑離去,殊不知身后斯文的男人緩緩摘下眼鏡,目光逐漸顯露出野獸般的掠奪。 再見面,她被前夫惡意灌下不明藥物,男人慢條斯理的解開領帶,語氣危險又低醇:“你看,被我猜中了吧。”
62.1萬字8 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