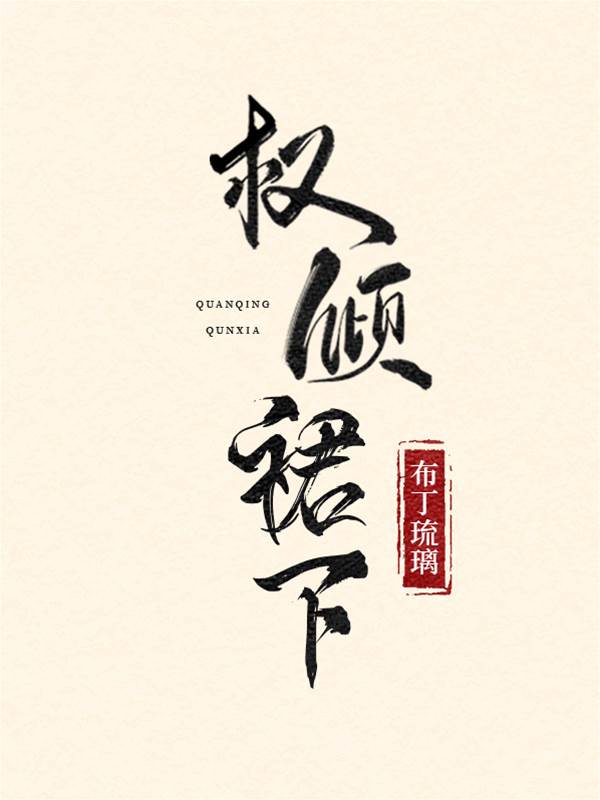《侯府在逃小妾》 失寵
失寵
自那日後, 衛辭似是有意避開趙楨奚,連晚膳都命人送至房中。
宋既已從李公公手中拿到藏匿于樹上的家當,也不必往前湊,懶洋洋地泡在浴桶中驅散疲乏。
隔著裊裊白霧, 男子僅著中的頎長軀裹上一層朦朧, 側致, 如夢似畫。
輕咬下, 憶起怪事一樁——
近來衛辭從未過自己。
多數時間,兩人像對和睦的老夫妻,他擁著, 有一搭沒一搭地談天。通常是宋提問, 衛辭耐著子回答,實在嫌煩了, 便箍住不盈一握的後腰,再于昏暗中索到喋喋不休的小, 輕含住,逗弄般地舐。
卻也僅此而已。
宋能察覺到他有意制的,每每這時,衛辭反而電般的松開,平躺著向銀閃爍的紗簾,調整呼吸。
他在忍耐什麽?又是為何忍耐?
宋垂眸打量一眼水下玲瓏有致的曲線, 分明更甚從前, 衛辭怎麽就膩了呢。
若是早一些也罷, 可如今方費心做好京的心理準備,在這個節骨眼兒失了寵, 人生地不,事業連雛形都不見, 豈非腹背敵?
“在想什麽。”
愣神之際,衛辭走了進來,小臂上搭著慣用的長帕,作生疏地包裹住一頭烏發。
宋不答,只順著力道仰頭看他,水汪汪的杏眼映照著燭,有子不諳世事的爛漫。然而態,瑩潤如暖玉,配合著周水汽,活像是話本裏人心神的魅。
結不控制地滾一番,衛辭錯開眼,卻迎著錯愕的目悠然擡頭,甚至隔空彈跳兩下。
“嘩啦——”
倏然起,雙臂錯,掌心撐著桶沿。
晶瑩水珠閃著金點,流淌過山巒湖泊,令人呼吸停滯,視線不知該安放于何。
Advertisement
宋眨眨眼:“許是泡得時間太久,現下有些乏力,你幫我,好不好?”
衛辭鬼使神差地點了頭,撈過屏風上懸掛的浴巾,一整個將人裹住,抱坐于上。再取來窄小一些的巾,淨臉上的水珠,而後是鎖骨……
終于,連細白雙足都恢複幹燥,仍是依地攀扶著他,撒著:“幫我絞發。”
他分明繃了一張弓,甚至有熱汗悄然滴落在宋口,卻一聲不吭,學著平日裏見過的那般,輕輕攏去發間的水珠。
這麽能忍。
宋決意下一劑猛藥,故意微揚起小臉,任呼吸噴灑在他間凸起,一邊若無其事地攀談:“明日便能京了,公子可高興?”
衛辭并不木訥,紅著眼:“你故意的。”
順勢出舌尖了,理直氣壯道:“不可以嗎?”
他倒吸一口氣,臉紅,懲戒地咬上的。見宋吃痛回,方喑啞地開口:“再等等,等明日,不,後日。”
“為什麽。”不滿地撅起。
“你說為什麽。”衛辭咬牙切齒道,“先是落水發了高熱,近來又日日趕路,我若再折騰,你能清醒著京?”
“啊……”
實是不曾預想過的答案。
見滿目訝然,衛辭愈發生氣,兩指不輕不重地住下,迫使擡頭:“原來,在你心裏,我竟是只在乎那檔子事的人?”
宋不由得屈,原本就是以侍人,難道,還應該幻想一些神聖的不……
衛辭已被熱火燒得頭昏腦脹,略帶暴地t將扔進床榻,扔來一件鴛鴦肚兜。
自己則靠坐在床尾,單曲起,恰好掩住探究的視線。小臂上的青筋,因抓握作暴起令人口幹舌燥的弧度。
明明還不到盛暑,明明紗帳極輕薄,宋卻仿佛蒸籠,忍不住輕吐舌尖以紓解熱意。
Advertisement
衛辭側目看,下頜微揚,結快速聳,薄無意識地張啓,瀉出重呼吸。像是沙漠中水的人,忍耐著不面前綠洲,不知是出于不舍,還是擔憂一切不過只是幻覺。
大顆晶瑩汗珠暈了中,純白化為明,黏在上,勾勒出男子蘊含了力量的理。
宋不爭氣地鼻尖,憂心會流淌出熱燙。
的作令衛辭恍然大悟,手中頓了頓,俯靠近,噙著壞笑:“是我疏忽了。”
“?”
衛辭在嫵的眉眼間落下一吻,問道:“想要了,是不是?”
宋瞠目:“不是……”
他卻只當口是心非,熱的吻緩緩移至上,吐息織,嗓音低沉聽:“想要便說出來,總歸只有我一個在,累不著你。”
宋眼神一陣躲閃,怯怯落于他形狀漂亮的,也憶起藏在裏頭的舌尖有多麽靈活,又有多麽溫暖。
但時辰不早了,義正嚴辭地拒絕:“你若不刻意勾引我,我便不會想。”
衛辭怔愣一瞬,旋即失笑,心想到底是誰勾引誰?
譬如床榻大分明至可容三四人并躺,卻偏往他懷中,且素來只著一件薄薄的,人連手都不知放于何。
又譬如,分明面紅潤,卻裝作手腳乏力,擺出人姿態哄他拭水珠。
嘖嘖……
宋只想他速戰速決,跪坐起,以吻助興,催促道:“你快些弄完去洗手,我要睡了。”
/
終于了京,周遭人聲鼎沸。
宋過車簾隙往外瞧,見長街寬闊,馬車如此行在正中,兩旁還有錦衛開道,卻仍舊留有極大富餘,不影響錯落有致的小攤,人群亦是暢通無阻。
十六皇子行在前頭,衛辭道是再拐一道彎便能分道揚鑣,可車夫忽而勒馬,回稟道:“昭縣主的馬車攔住了十六殿下。”
Advertisement
堂姐回京了?
衛辭憶起下月是祖母壽誕,見宋好奇地過來,簡單解釋:“是我四堂姐,應是認出了侯府的馬車,待向十六皇子問過禮,會來打聲招呼。”
誰知,昭縣主卻非獨自一人過來,側跟著青衫竹紋的趙楨奚。
“在車等我。”
衛辭待一句,掀簾子出去。
昭見了他,掩笑笑:“個頭瞧著比去年躥高了些,你與十六殿下是如何上的?”
“就這麽上的。”衛辭嗓音冷淡,挑眉問趙楨奚,“殿下何故不早些回宮複命。”
“有你這般說話的麽。”
昭為自家堂弟打起圓場,和和氣氣道,“殿下若不急著回宮,不如一同去用午膳?前頭新開了一間食樓,請了蜀中名廚,熱火得很呢。”
趙楨奚瞥過虛掩的車簾,應聲:“也好。”
衛辭眸泛冷,卻終究沒有發作,轉向簾遞出一手,示意宋下來。
“這……”
昭後知後覺地反應過來,堂弟馬車中還坐有一人,且他親力親為地上前攙扶,怕是應了先前夏家小姐的猜測。
果然,一截蔥白纖手探出,而後是被幃帽遮掩的綽約姿。
納妾傳聞竟是真的。
不待宋行禮,衛辭拉著往前一步:“快些走罷,莫要橫在路中間讓人觀猴戲了。”
直至了二樓雅間,昭方從震驚中醒神,卻見堂弟親手摘了子的幃帽,出其下花容月貌的臉。
毫不輸以貌聞名于京中的夏方晴。
昭問:“這便是你府上的小夫人?”
聞言,衛辭眉宇間的疏離稍稍散去,似是冰雪初融,罕見地團著溫和。他“嗯”一聲,客氣道:“堂姐若得閑,定要來喝杯喜酒。”
“那是自然。”
宋為話題中心,卻曉得自己不必參與,由他們閑談,只埋頭用膳。
Advertisement
幾人曾在學堂做過同窗,而昭與趙楨奚經年不見,難免提及兒時趣事。衛辭偶爾應聲,目不自覺地追隨宋,夾去喜歡的菜,再不聲地轉過頭來。
姿態稔,顯然是長久相之下的習慣。
昭不知,略有所思地瞇了瞇眼。趙楨奚也不去想,宋似乎唯有在衛辭面前展隨一面,旁的時候,溫婉知禮、恪守距離。
既如此,為何要逃?
意識到自己興趣過濃,趙楨奚端起酒杯一飲而盡,在衛辭瞥來之前,恰到好地掩去眸中探究。
忽而,昭停筷,狀似不經意地問:“你既已要納妾,何時正式議親?便是瞧不上夏姑娘,那裴姑娘呢?”
衛辭一貫對誰都答不理,今日因著趙楨奚在場,有意保全自家人的面子。此刻聽昭拿喬,名為關切,實則是想刁難宋,當即發作:“縣主的手何時進本侯府中了?”
他自稱“本侯”,明顯了怒。
宋亦是在聽見“裴姑娘”時茫然擡頭,眸中緒晦不明,被一桌之隔的趙楨奚看在眼裏,未做思量,主解圍道:“姑娘的棋盤可否送我一份?”
發覺趙楨奚竟自稱為“我”,昭訝然側目,再看向宋時,了幾分蔑視。
“可以。”宋裝作遲鈍,不管席間的暗流湧,笑著答說,“但金骰子怕是要殿下自行差人去做。”
昭順著臺階而下,同宋搭話:“什麽棋盤?我與幾位閨中好友也玩這些,不知可有幸瞧上一眼。”
至此,方是兩位子初次正式對談。宋不卑不地解釋一遍,稱昭若是興趣,回頭繪份新的送去府上。
話題既已轉移,氣氛也有所緩和。
衛辭終是更仇視趙楨奚,收斂了慍,親自斟一杯茶,堵住宋的,皮笑不笑地說:“我們先行回府了。”
“棋盤——”
他眼也不擡,涼聲道:“差蒼送一趟便是。”
猜你喜歡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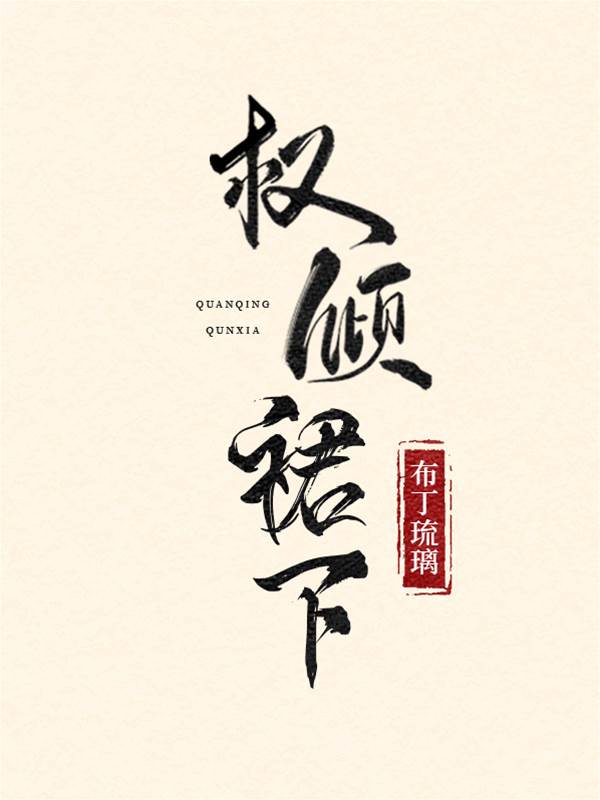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512 -
完結967 章
神醫王妃她拽翻天了
秦語穿越成炮灰女配,一來就遇極品神秘美男。 秦語道,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因為相遇是妹妹陷害,大好婚約,也不過是她的催命符。 秦語輕笑:渣渣們,顫抖吧! 誰知那令人聞風喪膽的燕王,卻整天黏在她身邊.
170.1萬字8 23384 -
完結161 章

太子妃實在美麗
尚書府的六姑娘姜荔雪實在貌美,白雪面孔,粉肌玉質,賞花宴上的驚鴻一現,不久之後便得皇后賜婚入了東宮。 只是聽說太子殿下不好女色,弱冠之年,東宮裏連個侍妾都沒養,貴女們一邊羨慕姜荔雪,一邊等着看她的笑話。 * 洞房花燭夜,太子謝珣擰着眉頭挑開了新娘的蓋頭,對上一張過分美麗的臉,紅脣微張,眼神清澈而迷茫。 謝珣:平平無奇的美人罷了,不喜歡。 謝珣與她分房而睡的第三個晚上,她換上一身薄如蟬翼的輕紗,紅着臉磨磨蹭蹭來到他的面前,笨手笨腳地撩撥他。 謝珣沉眸看着她胡鬧,而後拂袖離開。 謝珣與她分房而睡的第三個月,她遲遲沒來, 謝珣闔目裝睡,等得有些不耐煩:她怎麼還不來撩孤? * 偏殿耳房中,姜荔雪正埋頭製作通草花,貼身宮女又一次提醒她:主子,太子殿下已經到寢殿好一會兒了。 滿桌的紛亂中擡起一張玉琢似的小臉,姜荔雪鼓了鼓雪腮,不情願道:好吧,我去把他噁心走了再回來… 窗外偷聽的謝珣:……
25.7萬字8 76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