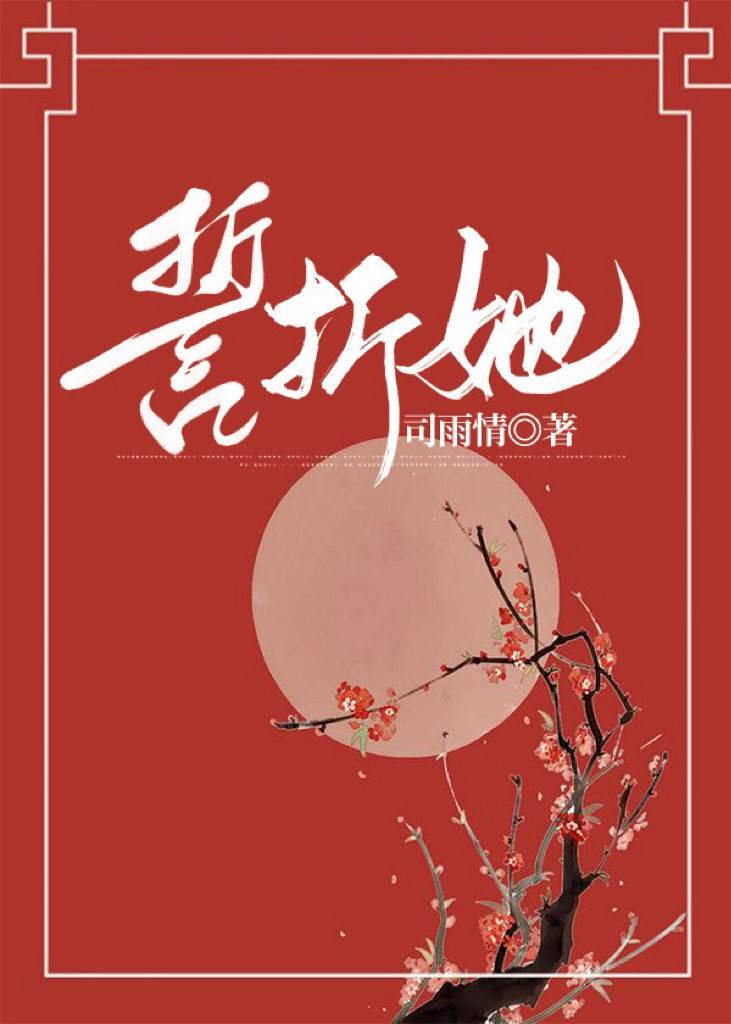《暴君獨寵小宮女》 第四十四章 出氣
朵蘭的橫躺人群中央, 脖頸還在不斷的湧出殷紅,滴答的粘稠汩汩彙聚為泊,死狀相當慘烈。
驚呼過後, 是死一般的沉寂。人人都知魏傾暴, 平生唯一的樂趣便是砍人腦袋,但聽說歸聽說, 大部分人還是頭一回見。
比如太後, 宮鬥十多年手上的人命雖多到數不清,也從沒直面過如此腥的場景。目的殷紅讓人不適, 讓人做嘔, 太後面發白後退幾步,由侍攙扶著才能堪堪穩住子。
徐清婉也好不到哪裏去。第二次了, 上一回皇上當著的面斬下雙臂, 這回砍下人頭, 徐清婉不知道下一次在自己面前飛出去的是哪部位。巨大的恐懼籠罩著, 徐清婉癱坐在地上, 渾珠寶氣都掩飾不住面的蒼白。
所有人都以為到此為止了。皇上沖冠一怒為紅, 砍個下人為寵妃出出氣也說得過去,誰讓朵蘭不知死活地招惹呢!可終究是他們想的太簡單,也低估了霜落在魏傾心中的地位。
劍刃上鮮還未凝固, 魏傾又問:“今日誰過?”
這就是要繼續出氣的意思了。衆人心裏皆是一驚,過霜落的人……蒼天可鑒, 太後和徐清婉皆是言語攻擊, 可還沒來得及對人手滅口呢, 再加上有青竹,芍藥等人護著,今日過霜落的人確實沒有幾個。
沒人承認, 魏傾心底湧出一不耐。幹脆把人都砍了得了,他這樣想。
霜落被他抱著,腦袋瓜藏在狐裘下什麽也看不見。但能聽見魏傾的說話聲,霜落決定裝死到底,因為現在本不知道怎麽面對魏傾,更不知怎麽接找了皇帝當對食這件荒唐事。
Advertisement
霜落胳膊了,一魏傾就自然而然地注意到手腕的紅痕。他剛才及霜落手背的時候就看見了,白皙如雪的上紅著一片,像被人□□過一樣。
魏傾更暴躁了,他不耐煩地又厲聲問一遍:“朕問,今日誰過?別告訴朕手腕上的紅痕是自己掐的!”
還是青竹明白魏傾的意思,回話道:“回稟陛下,方才醫翠紗為小娘娘診脈,當時雙方確實有肢沖突,小娘娘手腕上的紅痕興許是那時候留下的。”
翠紗要冤死了。方才診脈發現霜落懷有孕時太激,著霜落手腕惡狠狠的打算拽人出去邀功,不想霜落掙紮青竹阻攔,混中自己都不確定到底把人怎麽了。
誰知道那小姑娘皮這麽,不經磨,輕輕一也能留下紅印子。明明是個低賤的宮出生,卻渾上下比誰都,不是天生的狐子是什麽?
翠紗一聽皇上的怒火燒到自己上來,趕忙跪著手腳并用爬到魏傾側來,“皇上明鑒!奴婢只是奉命行事,絕無傷小娘娘之心,還請陛下寬恕哪——”
寬恕?魏傾一曬:“朕送你到閻王爺跟前,你問問他能否寬恕?”
翠紗自知死罪難逃,又爬到太後跟前求饒:“太後娘娘,您替奴婢說句話哪——奴婢跟了您十幾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翠紗也是病急投醫,說罷又去求徐清婉:“承妃娘娘,求您開口幫幫奴婢吧……”
太後默不作聲,魏傾砍人不眨眼的惡名在外,可不想在這種時候黴頭,興許這瘋子殺紅眼了能拿劍指著的脖子。
徐清婉更不用說,一聽陛下還有繼續殺人的意思嚇的神志不清瑟瑟發抖,似乎要暈過去了。
滿院子的人都跟拔了舌頭一樣,沒人敢發出一點聲音。莊嚴肅穆的氛圍猶如行刑前的寧靜,所有人屏息等待那恐怖的流時刻的降臨。
Advertisement
魏傾的耐心也到了盡頭,他正提劍,卻聽耳側傳來一聲嚶嚀,委屈的,嗔道:“困了,要去睡覺。”
霜落腦袋從狐裘中出一點點,水汪汪的眼睛向魏傾。好像一只剛破殼鑽出的小崽崽,脆弱的,憨的,誰看一眼都會沉淪下去給一生寵。
魏傾滿腔怒氣莫名消散,心也變的了。他說:“知道了,我抱你去睡。”但他勢必要替霜落出這口氣,吩咐下人道:“將人押到正令司。”
然後,衆人便瞧見上一秒還怒氣沖沖,恨不得提劍殺盡天下人的年輕帝王咣當一聲扔下刀劍,雙手抱著一個小姑娘大步流星上了樓。
等到了二層小樓,帝王還不忘立在勾闌前怒喝:“還愣著幹什麽,等著朕送你們出去嗎?滾——再讓朕在月居瞧見你們,一個個拖到深山喂野狼。”
二層的臥房花團錦簇,溫暖如春,隔絕外頭凜冽肅殺的寒氣,魏傾將人放在床榻上坐好,解下狐裘,再掉鞋。
等霜落躺好,魏傾幫忙蓋好被子,他問青竹:“太醫怎麽還不到?速度像烏一樣,留著他那雙有何用?”
青竹連忙派人去催。等臥房裏只剩下兩個人了,霜落著魏傾,魏傾凝視著霜落,相顧無言間,雙方都不知道該說什麽。
還是魏傾率先打破沉默,他霜落額前的碎發,說:“抱歉,這是最後一次讓你委屈,以後不會了。”
霜落心思不在此,悶聲問:“我不是在做夢吧?”
怎麽還是一如既往的傻。
魏傾笑,一雙桃花眼勾起,像一池波粼粼的春水。“沒有做夢,若不信,你咬我一口試試?”說罷當真掀開袖子胳膊湊上來。
霜落把頭別開:“你當真是我的對食阿吉吉,也是當今獨一無二的皇帝?”
Advertisement
魏傾手進被子裏握住霜落的,說:“是貨真價實的皇帝,也是你獨一無二的阿吉吉。明白了嗎,小呆瓜!”
魏傾食指在腦門上輕輕敲一下以作懲罰。
以前不是沒有料想過份暴的時候,剛開始他怕霜落知道,後來覺得知道也無妨,再後來又怨蠢笨不知道。明明都說的那樣明白了,小丫頭還是猜不著,天在他跟前傻樂,圍著自己一聲聲阿吉吉得歡快。
魏傾覺得自己真的栽了!栽在這個蠢蛋手裏。
初見那日霜落他一聲呆瓜,他記仇,如今一聲呆瓜還回去,算是報了小丫頭愚笨遲鈍天變著法子氣他的仇。
霜落還是沒有反應過來。不適應,不知道怎麽應對雙方份,地位的巨大轉變,怎麽改變兩人的相方式。以前都是欺負魏傾來著,占便宜一言不合就咬人……以後怕是不能這樣了吧。
霜落想不通就暫時不想了。抓著魏傾的手放在小肚子上,那裏還很平坦,卻會神奇的一個月一個月漸漸大起來,新的生命到來,那個小東西上流淌著他們共同的。
想到這裏,兩人都有些虔誠。
霜落撇,責備似的:“都怪你!你往我肚子裏塞了個小娃娃。”
魏傾爽快認下:“嗯,怪我。”魏傾的小肚子,“讓你苦了,難不難?”
霜落立馬點頭:“頭暈,沒有力氣,我又困了。”
“那就睡吧。”
霜落實在困,眼睛都睜不開。沉沉睡去沒一會太醫就來了,李太醫拎著醫藥小箱子,彎腰小碎步邁的極快。一路上已經有人告知他今日月居驚心魄的事,李太醫自覺來晚了,進屋後先來一個跪拜。
他高聲道:“皇上恕罪,老臣來遲——”
Advertisement
@泡@沫
他正拜的來勁,不想魏傾淩厲的視線掃過來,食指豎在邊:“噓——別吵,你過來好好瞧瞧。”
李太醫用袖子拭額上的汗,作麻利地搭上脈枕,閉眼索又觀察霜落臉,還找來芍藥等人問霜落的飲食,一陣忙活後才道:
“回稟陛下,小娘娘初次有孕,嗜睡,乏力,沒食等都是正常的反應。孩子還小,但脈象潤,如珠走盤想必不會有問題。好生調養,老臣定期會診便是。”
魏傾將霜落的手輕輕放回被子中,又問:“有什麽注意事項?”
李太醫悉數道來:“忌勞累,忌生冷,忌劇烈運,忌……同房。”李太醫說到此頓了頓,小心觀察魏傾的臉,解釋說:“也是為小娘娘著想,懷孕初期確實不能同房。”
魏傾瞪他一眼,那意思就像在詢問:朕是這麽如似的人嗎?
李太醫被魏傾蹬的噤聲,魏傾說:“朕知道了,何時可以同房?”
“三個月後可以,不過作要輕一些,也不易頻繁同房……”
李太醫滔滔不絕地講述注意事項,魏傾聽的認真,他記憶力好聽一遍就能記住。
魏傾正聽的神,床榻上忽然響起霜落的聲音:“夠了!可以了……”
小姑娘極為害,到被窩裏害怕見人。魏傾笑,等送走了李太醫將人從被子裏撈出來,順勢臥在床榻上攬住霜落的腰肢:“臉這麽紅,害了?”
霜落才不承認:“被窩裏憋的。”
“好好好,你說什麽就是什麽。不睡了嗎?”
霜落本來睡著了,但李太醫和魏傾一直在床頭嘀嘀咕咕,不醒才怪。許是因為見到魏傾的緣故,霜落覺得上不難了,渾的力又回來了。
但還是氣鼓鼓的鼓著腮幫子,佯裝生氣從魏傾懷裏掙出來要拉上被子睡覺。魏傾許久沒抱,極其想念小姑娘的味道。
于是霜落掙紮他不允,固執地抱的了又。像一塊的玉,細膩令人不釋手,又像一塊甜甜的糖,讓人忍不住想一口吃進肚子裏。
二人在床榻上你來我往,你追我跑,鬧的厲害無意間霜落小手及魏傾間。魏傾呼吸微滯,大掌立馬按住的。
空氣中飄散著甘松的味道,一名為尷尬的氛圍在兩人中間擴散。分別一個多月,魏傾本就有些不能自已,更別說眼下這樣的狀況。
興許是鬧的太厲害,小姑娘臉上酌紅一片,像抹了胭脂。裳也松散開了,自肩頸開出優的鎖骨和大片白皙的皮。氣的厲害,隆起的曲線也跟著一起一伏,魏傾霎時嚨有些幹。
他按著霜落的手,霜落想開他不讓,兩個人就這麽僵持不下。半晌,魏傾低頭在耳畔廝磨,含住霜落小巧的耳垂,禮貌又君子地問:“我能親你嗎?”
啊——這種事還要問嗎?以前不都是直接上嗎?
霜落想不明白,兩個連孩子都有的人,親吻還要問對方一句可以嗎?這種覺好奇妙,就像是開始了一段段純純的初。雖然奇怪,但還喜歡的。
霜落故作姿態:“我說不能你就不親了嗎?”
魏傾搖頭:“我就是問問,親是要親的。”
哼,就知道。
霜落撅起,魏傾適時俯,一口采攫到的芳香。小姑娘的和記憶中一樣香甜潤澤,他剛開始還能輕輕的啄,小口小口的咬,後來實在想的又控制不住,魏傾手掌大力地抵住的後腦勺,舌頭在貝齒上掃一圈,撬開牙關攻城掠池。
一時間潺潺的水聲伴隨魏傾急促的呼吸在臥房此起彼伏。他不管不顧,像一頭野,勢必要采下原野上最的花朵。把它捧在手心,含在裏,最後吃幹抹盡吞腹中。
霜落沒被他這麽激烈的吻過,即便兩人做最親的事時也沒有,當然也有可能是那時腦子混沌記不清了。被魏傾激烈地在下索吻,這種覺讓沉溺其中又害怕。
喜歡他的吻,甚至喜歡他的暴,願意與他相親互訴衷腸,也願意一生一世這樣被他對待。但霜落又莫名地不安,覺得……自己快被親死了。
不知糾纏了多久,停下來時兩人都的不行。霜落好像一個溺水的人好不容易得救,大口大口地呼吸空氣。魏傾與額頭相抵,在霜落的額頭,眼睛,鼻尖又輕輕蹭了蹭。
霜落的一只手還停在魏傾間,明顯覺到那裏不一樣了。
猜你喜歡
-
完結2229 章
帝凰之神醫棄妃
大婚當天,她在郊外醒來,在衆人的鄙夷下毅然地踏入皇城…她是無父無母任人欺凌的孤女,他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鐵血王爺.如此天差地別的兩人,卻陰差陽錯地相遇.一件錦衣,遮她一身污穢,換她一世情深.21世紀天才女軍醫將身心託付,爲鐵血王爺傾盡一切,卻不想生死關頭,他卻揮劍斬斷她的生路!
448.5萬字8.38 388648 -
完結1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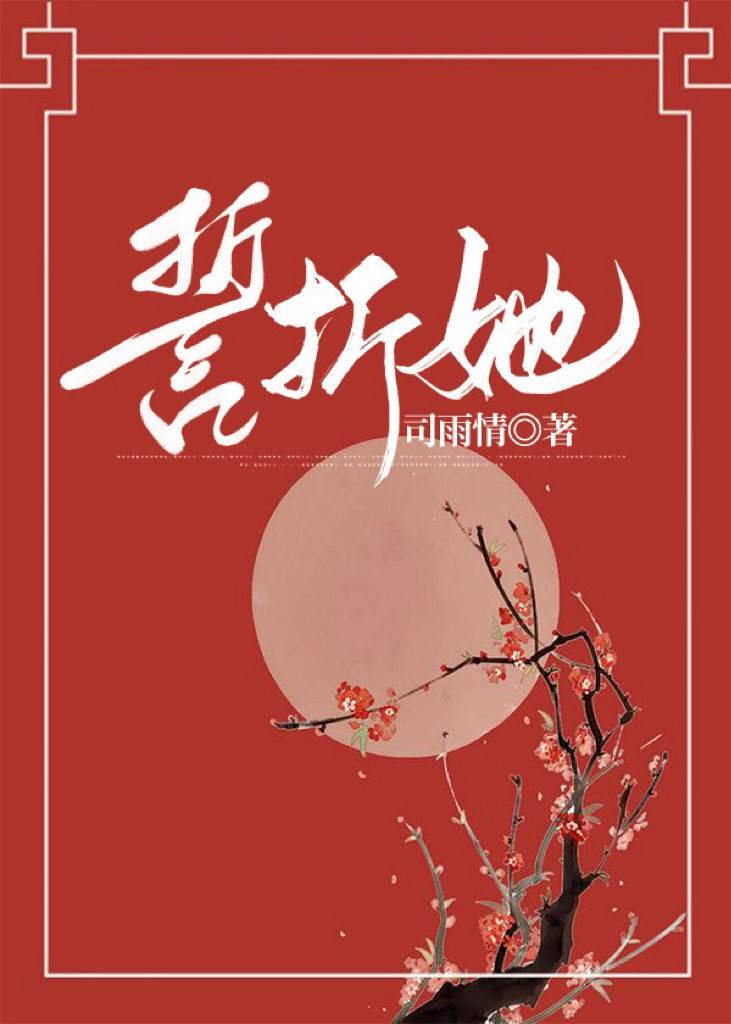
妄折她
昭華郡主商寧秀是名滿汴京城的第一美人,那年深秋郡主南下探望年邁祖母,恰逢叛軍起戰亂,隨行數百人盡數被屠。 那叛軍頭子何曾見過此等金枝玉葉的美人,獸性大發將她拖進小樹林欲施暴行,一支羽箭射穿了叛軍腦袋,喜極而泣的商寧秀以為看見了自己的救命英雄,是一位滿身血污的異族武士。 他騎在馬上,高大如一座不可翻越的山,商寧秀在他驚豔而帶著侵略性的目光中不敢動彈。 後來商寧秀才知道,這哪是什麼救命英雄,這是更加可怕的豺狼虎豹。 “我救了你的命,你這輩子都歸我。" ...
40.2萬字8.18 69839 -
完結164 章

去父留子後,瞎眼國舅發了瘋
簡介: 沈枝熹隻想和宋漣舟要個孩子,卻不想對他負責。因為娘親說過男人沒有一個好東西,永遠都靠不住,男人唯一的用處,就是幫女人懷上一個孩子。厭惡男人的第一課,就是她的親生父親為她上的。她從未見過自己的生父,當年她父親讓她母親未婚先孕卻不負責,一走了之讓她們母女受盡了白眼。後來,她又被青梅竹馬背叛設計,因此徹底對男人死了心。但她需要一個屬於自己的血脈,所以救下了一個重傷卻長相貌美的男人。更慶幸的是,那個男人還是個瞎子。瞎子好呀,他不知道她長什麽樣,以後也就不用擔心他會回來糾纏。於是沈枝熹將他藏在了她的私密住處,日日撩撥,夜夜廝磨。懷上孩子後,又立即抽身棄了他。她走的幹淨,被棄的瞎子卻發了瘋。三年後,沈枝熹同女兒被擄至月京城,竟又遇上了當年那個瞎子。隻不過彼時的瞎子不僅眼睛好了,還搖身一變成了當朝國舅,皇後的親弟弟。看著他和自己的女兒長的八分像的臉,沈枝熹心焦的不行。
30.8萬字8.18 1287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