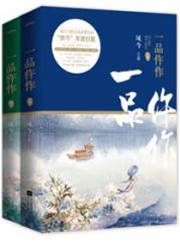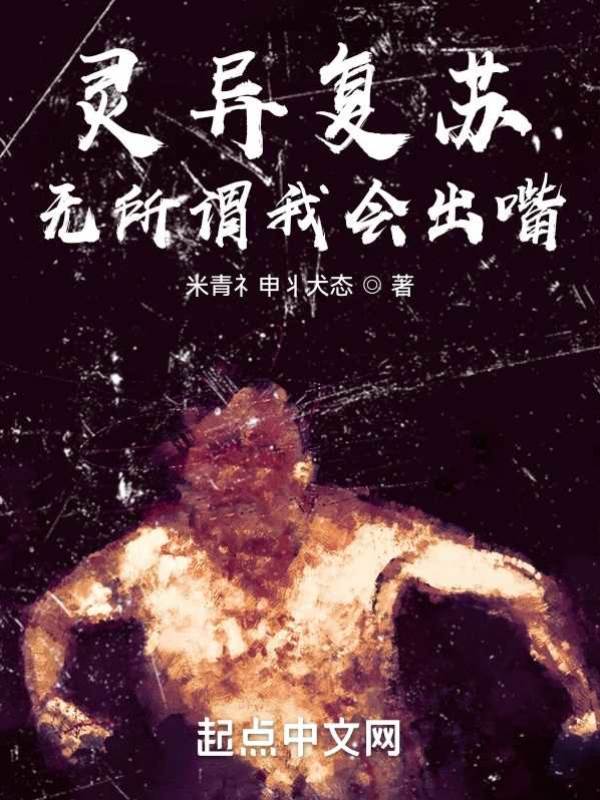《濱江警事》 第十章 涉江的都歸我管
;
「等會兒就去抓黃牛?」
「先去看看,我們要麼不打擊,打擊就要把他們一網打盡,不能撿了芝麻丟了西瓜。Google搜索」
打擊投機倒把,抓票販子,很刺激啊。
韓渝咧笑道:「好的。」
徐三野是個如假包換的行派,吃飽喝足回宿舍換便服,又翻找出一個手提包,扮旅客帶著韓渝直奔白龍港。
白龍港雖然是重要的水路通樞紐,但終究是一個村。
白天旅客很多很熱鬧,晚上有些冷清。
因為晚上只有一條客靠港,客運碼頭的售票廳和候船廳都關門了,只有出口有人等著接親朋好友下船,還有幾個騎坐在托車上的人和幾個騎三黃包車的人等著拉客。
不遠的長途汽車站關門了,幾個國營商店也關門了。
村民開的小商店晚上營業,櫃檯上有一臺電視機,門口坐著好多村民看電視納涼。;
兩個旅社門口亮著燈,住一晚兩塊五,不過看著下旅社的人不多。
還有人在前面擺康樂棋和撞球,一樣沒什麼人玩。
徐三野見有人賣冰,正推著一輛后座上綁著個白大木箱的自行車走了過來,迎上去問:「冰怎麼賣的?」
「一角一支。」
「不是五分錢一支麼,怎麼漲價了。」
「現在什麼東西不漲價呀,而且我這是油的!」
「來兩支。」
徐三野掏出錢,買了兩冰,遞給韓渝一,撕開外面的紙,邊吃邊繼續閒逛。
剛吃了他買的豬頭,現在又吃他買的冰,韓渝正覺得不好意思,一個抱著孩子的婦迎上來問:「同志,去哪兒的?」
「去東海的,怎麼了。」
Advertisement
「東海大著呢,你們是去十六鋪,還是去吳鬆口?」
「十六鋪。」;
「有沒有買到票。」
「你有票?」徐三野停住腳步。
婦回頭看看後,笑道:「明天早上的,十五一張,要不要。」
「十五一張,幾等艙的?」
「五等艙。」
「這也太貴了,去售票廳才一塊七!」
「售票廳是一塊七,但也要能買到。」
「我們已經買到了。」
「真的假的?」
「騙你做什麼。」
徐三野不想打草驚蛇,帶著韓渝接著往前走。
婦抱著孩子跟了上來,追問道:「要不要下旅館,你們自己去要兩塊五,我帶你們去只要兩塊。」
「我們已經住下了。」徐三野不想被黃牛記住自己的樣子,加快腳步甩開。
逛了不到半個小時,竟遇著四個黃牛。
倒賣的票價都一樣,去十六鋪碼頭的五等艙船票都是十五塊錢一張。;
徐三野越想越覺得有搞頭,一邊往回走一邊低聲問:「鹹魚,有沒有記住剛才那幾個票販子的樣子,再見著他們能不能認出來。」
「我記得第二個,他下上有顆痣。」韓渝下意識看了看後。
「這可不行,以後要注意觀察,要記住嫌疑人的相貌特徵。等把船修好,等將來有時間,我教你怎麼辦案。」
「好的,謝謝徐所。」
「別謝了,走,我帶你去個地方。」
「去哪兒。」
「去了就知道了。」
徐三野回到所里,騎上邊三。
韓渝本想坐在斗子裡,結果他說坐斗子裡太顛,讓坐后座。
第一次坐托車,韓渝真有些興,可坐了不大會兒就到了目的地——距沿江派出所兩公里的四廠派出所。
Advertisement
值班民警認識徐三野,對徐三野很尊敬。
徐三野問清楚他們所長在哪兒,帶著韓渝直奔四廠鄉電影院。;
今晚放電影,從電影院門口的大海報上看好像放的是《殘酷的》,彩寬熒幕的,看海報就知道很好看。
四廠派出所的丁所站在外面跟一個鄉幹部說話,見徐三野來了連忙上前敬禮。
「徐所,你怎麼來了,是不是看電影的,電影都放一半了。」
「看什麼電影,我們是來找你的。」
丁所長看看站在邊上的韓渝,笑問道:「徐所,這就是剛分到你們所里的鹹魚?」
徐三野笑道:「你怎麼知道的。」
「你昨晚大鬧政工室,搶了金盾賓館,連食堂的電飯煲好像都被你順走了,局裡誰不知道,哈哈哈。」
「別瞎說,我是借的。鹹魚,別愣著了,趕丁所啊。」
「丁所好。」韓渝緩過神,連忙問好。
丁所長只知道局裡往沿江派出所塞了個孩子,沒想到這孩子是真小,不拍拍韓渝的胳膊,轉看著電影院說:「想不想看電影,我送你進去看會兒。」;
好久沒看電影了,並且裡面放的是《殘酷的》。
韓渝真想進去看看,正不知道該怎麼說,徐三野臉一正:「看海報就知道不是什麼正經片子,鹹魚才多大,怎麼能讓他看這些,你這不是帶壞小孩麼。」
電影名字極力,海報的力更大,上面有一個人,濃妝艷抹。
丁所長也意識到讓小鹹魚看這個電影不合適,轉看著海報笑道:「反正都快結束了,看個結尾也沒意思。過幾天放《紅蜘蛛》,演的是我們公安破案的,到時候我讓老章帶你來看,看那個有意思。」
Advertisement
「這還差不多。」
「謝謝丁所。」
「不用謝,又不是外人。」
丁所長笑了笑,拉著二人走到一邊:「徐所,到底什麼事。」
徐三野直言不諱地說:「我要修船,沒錢。」
丁所長愣了愣,苦笑道:「沒錢你應該去找楊局,找我有什麼用。」;
「找楊局一樣沒用。」
徐三野環顧了下四周,低聲道:「我開始想著管長江水域的部門很多,比如剛併農業局的水產局,現在是漁業主管部門,還設了個漁政管理站。
又是宣傳《漁業法》,又是到發放國家和省里漁業法細則的,搞得像那麼回事。
本來以為他們很重視長江漁政,而且他們也沒執法船,打算跟他們合作,看他們能不能出點錢,跟我們一起把船修起來,到時候兩家一起用。」
徐三野不只是子野、野心大,路子也野。
丁所長覺得這個思路不錯,笑問道:「你找過農業局嗎?」
「找了。」
「他們怎麼說。」
「他們說人員沒全部到位,真正擁有執法權的幹部只有三個,各鄉鎮的漁政員大多是兼的。他們現階段主要是宣傳政策法規,主要忙著給漁船漁民辦證。」
徐三野深吸口氣,接著道:「而且我們陵海不但有江,一樣靠海。相比長江漁政,他們更關心海洋漁政。;
江上河上的全是一點點大的小漁船,漁民一個比一個窮,連漁民證人家都捨不得花錢辦,他們懶得管很正常。」
丁所長想了想,掏出香菸說:「人家既是執法部門也是經營單位,水產局雖然撤銷了,水產公司還在,我估計他們正忙著組織海邊的漁民出海打漁賺錢呢。」
Advertisement
「所以農業局那邊沒希。」
「你可以找找通局,他們的水上通運輸管理所,現在也加掛港監的牌子,變了什麼地方港監,可以說是水上通運輸的主管部門。」
「找過了,他們一樣是忙著辦證,偶爾開他們的小通艇在河轉轉,幾乎不管江面上的事。」
徐三野頓了頓,嘀咕道:「我還去找過剛立的環保局,照理說他們應該關心長江污染。結果他們人員沒到位,經費也很張。連職能都沒明確,上級有文件卻沒執行細則,現階段主要是搞調查研究。」
他不管到哪兒都不會消停,不然就不是徐三野了。
丁所長很清楚他想修船,那這船肯定是要修的,下意識問:「那怎麼辦。」;
「白龍港有不票販子,投機倒把,群眾意見很大。」
「徐所,這歸濱江港公安局的白龍港派出所管,你手不太合適。而且倒賣船票打擊難度太大,要抓現行,要人贓俱獲才能理。
我配合他們打擊過幾次,不是只搜到一兩張船票,就是買黑市票的旅客急著上船走,連筆錄都沒時間配合我們做。」
「我是沿江派出所長,只要涉及長江陵海段的各類違法犯罪行為我都有權管!」
徐三野大手一揮,接著道:「至於打擊難度大,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你們都是臉,那些票販子認識你們,躲著你們;二是你們沒找對方式方法,三是你們決心不夠大。」
第一點,丁所長很認同。
至於第二點和第三點,丁所長不敢茍同,甚至不敢摻和。
徐三野可是敢把一個喝多了耍流氓的副鄉長吊起來打的人,天不怕地不怕,什麼事都幹得出來,不然也不會被發配來做沿江派出所長。
那些票販子要倒大霉,搞不好會出事。;
丁所長不想被他連累,連忙道:「徐所,你說得對,這事我們真幫不上忙,我們要是過去只會幫倒忙。」
怎麼打擊那些投機倒把的票販子,徐三野早想好了,摟著丁所長的肩膀笑道:「那些票販子被你們打擊過,有案底有前科。我不要你出人,只要你提供點那些票販子的況。」
「這個沒問題。」
「就這麼說定了,相關的材料,你讓老章明天給我帶過去。」
「行。」
……
PS:簽約狀態終於改過來了,厚求打賞。
不求打賞多,不敢讓各位兄弟姐妹破費太多,只求把榜填滿好看。
猜你喜歡
-
完結283 章

一只斷手
這是一個燒腦的故事。 空降的刑偵隊長,孤兒院長大,一個思維縝密、行事冷靜、重情重義的男人,他生下來的使命就是保護弱者,面對罪惡,他永遠不會選擇盲從或者妥協,罪惡在引領著,正義的利劍已然出鞘,一點一點抽絲剝繭,你才知道真正的幕後話事人到底是誰~ 不毀你的三觀,只挑戰你的智商!
56.6萬字8 12658 -
完結4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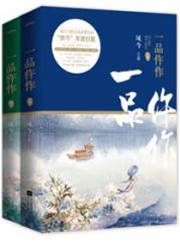
一品仵作
這是一個法醫學家兼微表情心理學家,在為父報仇、尋找真兇的道路上,最後找到了真愛的故事。聽起來有點簡單,但其實有點曲折。好吧,還是看正經簡介吧開棺驗屍、查內情、慰亡靈、讓死人開口說話——這是仵作該乾的事。暮青乾了。西北從軍、救主帥、殺敵首、翻朝堂、覆盛京、傾權謀——這不是仵作該乾的事。暮青也乾了。但是,她覺得,這些都不是她想乾的。她這輩子最想乾的事,是剖活人。剖一剖世間欺她負她的小人。剖一剖嘴皮子一張就想翻覆公理的貴人大佬。剖一剖禦座之上的千麵帝君,步惜歡。可是,她剖得了死人,剖得了活人,剖得了這鐵血王朝,卻如何剖解此生真情?待山河裂,烽煙起,她一襲烈衣捲入千軍萬馬,“我求一生完整的感情,不欺,不棄。欺我者,我永棄!”風雷動,四海驚,天下傾,屬於她一生的傳奇,此刻,開啟——【懸疑版簡介】大興元隆年間,帝君昏聵,五胡犯邊。暮青南下汴河,尋殺父元兇,選行宮男妃,刺大興帝君!男妃行事成迷,帝君身手奇詭,殺父元兇究竟何人?行軍途中內奸暗藏,大漠地宮機關深詭,議和使節半路身亡,盛京驚現真假勒丹王……是誰以天下為局譜一手亂世的棋,是誰以刀刃為弦奏一首盛世的曲?自邊關至盛京,自民間至朝堂,且看一出撲朔迷離的大戲,且聽一曲女仵作的盛世傳奇。
203萬字8 29155 -
連載13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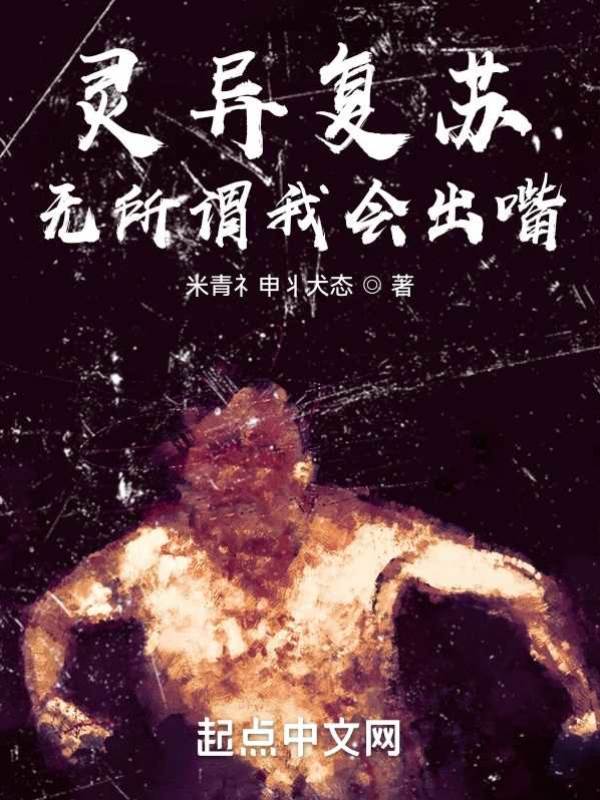
靈異復甦?無所謂我會出嘴!
每天看十個地獄笑話,再攻擊十坨答辯,然後隨機抽取十名幸運路人激情對線,最後再對佛祖進行毫無悔改之意的懺悔。 終於,我的功德掉完了,但我也無敵了。 我本以爲我只是無敵於人類, 直到白天下葬的死者被我在晚上從墳裡刨了出來...... 江湖術士,通天法師,半步仙人,自在真神; 冤魂擾心,厲鬼傷人,兇煞毀德,煞神滅道。 靈異復甦在即,百鬼夜行或在今朝! 不過,現在有個很重要的問題… 誰能告訴我爲什麼我用佛法修出了邪術啊?!
32.9萬字8.18 4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