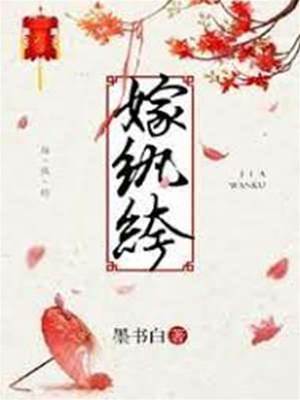《小嬌奴》 第17章 逼她穿肚兜
沒錯,是海棠紅的肚兜,可是春芽卻如同被火炭燙了手一般,立即將那肚兜推開。
避之不及。
云晏沒想到竟然是這個反應,不由得長眸瞇起,“你這是什麼意思?你不是一直小心眼兒地跟爺討還肚兜呢麼?怎麼,爺現在還你了,你反倒還不高興了!”
“三爺說的沒錯,奴婢是一直跟三爺討還肚兜來著,”春芽藏不住滿眼的失,“可三爺現在拿給奴婢的這條,卻不是奴婢的!”
“不是奴婢的東西……奴婢不要。”
眼前的這條,是嶄新的。
“你的那條已是舊了。尺寸也不合適。”云晏臉上浮起怒意:“這是同樣的,爺給你選了更好的料子;全新的,尺寸更適合你,你為何不要?”
春芽想起布庫那管事的話:布庫里所有海棠紅的料子都被三爺要去了,說是給阮姑娘裁裳。
所以眼前這塊的用料,必定是給阮杏裁之后剩下的布頭!阮杏用剩下的,為什麼要給?
縱然份低微,可是他憑什麼就認定,會撿阮杏的剩!
虧他還說因為今天乖,才賞給的;可他當真不明白,這哪里是賞,這分明是對最兇殘的懲罰!
抬眸涼涼瞟他:“新的又怎樣?奴婢倒不稀罕。三爺喜新厭舊,可惜奴婢卻只留曾經的舊。”
高高揚起下,眼睛里閃爍著不馴:“奴婢就喜歡自己那條舊的,還請三爺將奴婢那條舊的賜還。至于這條新的,三爺拿去送給別人吧!”
云晏瞇眼打量。雖然口口聲聲自稱“奴婢”,可是此時在他面前,除了桀驁之外,哪里有半點的卑微認命?
Advertisement
他不由得無聲冷笑,譏誚而又漫不經心:“你說爺喜新厭舊?那你說,誰是新,誰又是舊?”
“聽你的意思,你是想說,你才是爺的舊人?而爺喜歡,卻了見異思遷?
他背轉去,對不屑一顧。可又想到什麼一般,忽地又回轉來盯住眼睛,“你要是真這麼想,那你就是個蠢的!”
“爺便與你說個明白:爺與你相識不過數月;可是,是與爺一起長大,我們自青梅竹馬。我與有十幾年的分,你又憑什麼覺得你可以跟相比?”
春芽心口被他的譏諷狠狠搗了一拳,疼得無法呼疼,只能以苦笑掩飾。
是啊,他跟阮杏是青梅竹馬,拿什麼跟阮杏相比!沒錯,他說的一點都沒錯!
的笑映云晏眼底,攪起暗黑的波瀾:“你笑什麼?你敢笑話爺?”
春芽收回目,淺淺搖頭:“三爺誤會了。奴婢哪里是笑話爺呢,奴婢是謝三爺醍醐灌頂,讓奴婢清醒過來了。”
云晏瞇眼:“是麼?”
春芽故意天真無邪地沖他眨眼:“對呀。奴婢十六歲,正是做夢的年紀。這年紀的奴婢總是會忘了自己的份,做些永遠都不可能實現的夢。”
“是奴婢錯了,奴婢沒有資格做這些夢。可是奴婢自己醒不過來,多虧三爺將奴婢給醒了。“
這話聽起來表面是恭順的,可云晏卻只覺刺耳:“你這話不說也罷!”
怎麼辦,他又想掐死了!
揚州瘦馬從小的所學,不都是為了取悅郎君的麼?可學的是什麼,學的是要將他活活氣死八百回!
Advertisement
“那這肚兜,你究竟要還是不要?”他忍著不快,盡力平靜地問。
春芽冷笑著別開頭去:“奴婢謝三爺的賞。只是奴婢這次不需要。”
云晏皺眉,頗有些惱怒,便劈手一把將肚兜奪回來,攥進掌心。
“不要就算了。你不識抬舉,總有識抬舉的人。明兒爺就拿去送旁人。”他想了想:“對了,不如就送給“合歡樓”的花魁珠兒姑娘,”
“人家珠兒姑娘藝雙全,名京師,卻也無論是爺給什麼全都恩戴德,比你有良心!”
他忽然又欺近,垂下臉來俯視春芽:“爺倒不明白,就憑你,一個小小奴婢,竟然還敢挑三揀四。”
云晏拂袖而去。
.
沒出幾日,阮杏就穿了一海棠紅的來“明鏡臺”顯擺,逢人就問:“我好看麼?”
雖說老侯爺言不守孝三年,侯府眾人都不必穿素服,整個侯府也已經恢復了往日的富麗堂皇。但,這樣大喇喇穿一紅,還是“明鏡臺”上下都頗有些側目。
可是側目歸側目,又有誰敢阮杏一下呢。
是佟夫人的外甥,又是云晏的心上人,這侯府里除了大夫人和新家主云毓之外,沒人敢對說一個不字。
所以阮杏拉著綠痕搖曳擺的時候,就連綠痕都不得不違心地贊一聲:“阮姑娘真是人比花。”
綠痕都這麼說了,阮杏就更得意,搖晃著擺到了春芽面前來。
“到你說了,我好看麼?”
春芽盯著一的海棠紅,咬貝齒。
阮杏見春芽不說話,便繼續炫耀:“其實這倒不是我最的,可是阿晏他非我穿。他把整個侯府布庫里這個的料子都給我拿去了,說這個就給我一個人穿。”
Advertisement
“他還說啊,這春明的時節,我穿這最是艷。侯府里,再沒第二個人能比得上我的。”
阮杏的話,如一把一把的尖刀,番扎在了春芽心上。
春芽垂下眼簾:“阮姑娘名字里占了個‘杏’字,奴婢以為阮姑娘更喜歡杏黃。”
“香墨彎彎畫,燕脂淡淡勻。藍衫子杏黃,獨倚欄桿無語點檀……秦游的詞句這樣,奴婢原以為阮姑娘是這樣的人呢。”
阮杏眨眨眼:“我聽懂了,你是想說我穿這紅的不唄!”
“你會詩句,以為我不會是怎的?”
一說到詩詞,阮杏可絕不服輸了。因為盧巧玉就有“才子”之名,也因此云毓對盧巧玉總是比對好。
阮杏覺著在詩詞這塊斗不過盧巧玉,難道還斗不過一個丫鬟了!
畢竟,父親也是兩榜進士的出!
阮杏搜腸刮肚:“有了!誰說就只有‘杏黃’的,我就給你找個紅的!”
春芽淡淡斂眉:“奴婢聽著呢。”
阮杏揚起一臉的得意,“好,你聽著:‘滿園春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瞧,這不是紅的嗎?”
春芽靜靜抬眸。
眾人:……
眾人的反應讓阮杏有些心虛。
的丫鬟墨兒忙扯扯袖子:“小姐,好像不對……”
阮杏也低聲音問:“哪不對了?”
墨兒搖頭:“奴婢也不明白。”
阮杏心下別扭,便瞪春芽:“你作弄我?”
春芽微微蹙眉:“阮姑娘詩,都是阮姑娘自己選的,怎地了奴婢作弄?”
阮杏一扭頭,正瞧見云毓和盧巧玉從外頭進來。
Advertisement
忙提著擺跑過去:“毓哥哥,你評評理,我穿這紅子,是不是‘一枝紅杏出墻來’?我說的對不對?”
云毓:……
盧巧玉卻險些笑出來。
盧巧玉這一要笑,阮杏就更不高興了。捉著云毓的袖子,一臉的防備:“毓哥哥方才去了哪?怎麼跟在一起?”
盧巧玉收回笑意:“我姑母要二哥給老侯爺寫一篇祭文,這才要我幫二哥參詳。”
“怎麼,阮妹妹想幫忙?不如我推了這個差事,請阮妹妹來幫二哥撰文,如何?”
阮杏自然聽得出盧巧玉話中的揶揄,氣得扭跑出門。
“我算看出來了……你們一起欺負我!”
“你們等著的,我現在就找人去問個明白。若我確認是你們故意作弄我,我跟你們沒完!”
見阮杏氣跑了,綠痕趕上前與云毓將前后果稟報了一遍。
盧巧玉聽到是春芽引出的阮杏這句詩,便遙遙笑著向春芽眨眼。
云毓卻眼底微冷。
他抬步走向“止水堂”,僧飄擺,如片片飛雪。
“你跟我進來!”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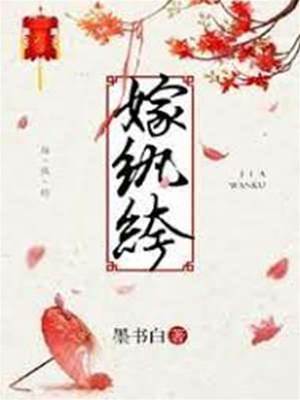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50163 -
完結1573 章

絕色神醫:驚世五小姐
【重生,1v1雙強甜寵,雙向奔赴。】 蘇慕绾重生到十四歲那年, 她還未和謝景年退婚, 她的爹娘還在,哥哥還未墜崖,壹切都還來得及, 這壹世她要讓蘇挽秋和謝珩亦付出代價,上壹世欠她的,她通通都要討回來。 這壹世,她不會再讓謝景年早逝,哥哥也不會落得壹個身死的下場,且看她如何妙手回春,手撕渣男賤女…… 某個午後: 壹絕色女子枕在壹位極俊極雅氣質出塵的白衣男子腿上,紅唇微啓,語氣慵懶又帶有壹絲魅惑:“阿景,這輩子妳都別想再逃~” 他薄唇輕啓,滿眼寵溺的低垂著眸子,看著懷中的小人兒:“嗯,不跑,我裏裏外外都是妳的。”
363.2萬字8.18 249619 -
完結522 章
寵后之路誤惹狼君萬萬歲
辛鳶對天發誓,當年她撿到家裏那頭狼時純粹是因為愛心,要是她知道那頭狼會有朝一日搖身一變成為九五至尊的話,她絕對……絕對會更早把他抱回家! 開玩笑,像這樣美貌忠犬霸氣護妻的狼君還能上哪找?不早點看好,難道還等著別人來搶嗎?某狼君:放心,誰來也搶不走! 辛鳶:我得意地笑了~
91萬字8 200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