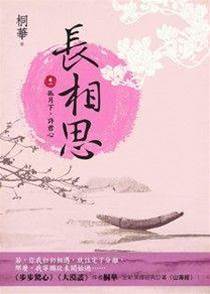《明月棲山阿》 第7章 長風
依言找一旁的小沙彌要來了紅綢與筆墨。
前世也曾許了願,願家人安康,侯府順遂,結果卻是用自己的姻緣和命換來的這一切。
這次,細細思索半晌,竟也想不出什麽別的願來。
不信神佛,也不信什麽願真。心裏空落落的倒像無的浮萍,水裏的浮木。
寶琴候在旁,悄悄背過去。
“小姐快點許願吧!寶琴絕不看!”
催促的話音剛落,一陣煦風吹拂,滿天菩提花洋洋灑灑迎風起舞。
看著紅綢上飄落的幾粒菩提花與耳邊勾人心的風聲。
沈玉芙提筆,福至心靈,瀟灑不羈的寫了四個字:願為長風。
但願為長風,無拘無束,繚繞遠空。
將紅綢用寺裏特製的木牌掛好,讓寶琴轉過來。
Advertisement
“喏。”
“姑娘你許好願啦!”
沈玉芙笑盈盈地看。
寶琴歡歡喜喜的接過墜著木牌的紅綢,使出渾的力氣,把木牌用力往菩提樹上揚去。
這一樹菩提枝繁,眾人為求穩妥,倒是老老實實將紅綢係在不高不矮的枝上。
沈玉芙視線隨著紅綢在空中劃過的弧度而,最後瞧著它勾上了高高的枝頭,心裏才鬆下一口氣。
也不盼什麽神佛能夠實現的願,不過好歹是一份念想,勉強能支撐著打起點生氣。
寶琴指著高高枝頭上輕飄著的紅綢:“小姐小姐!我掛的高不高!”
沈玉芙瞧著寶琴一臉求誇獎的期待模樣,開口便誇讚:“掛的那般高,可得多謝寶琴了,回去再給你買一盒聚福齋的糖蒸酪如何?”
Advertisement
寶琴抿嘿嘿笑著:“唯願姑娘願真,酪其實也沒那麽重要啦!”
沈玉芙眼帶笑意看著,又回頭看了眼那滿樹的飄綢。的發頂落了幾粒瑩白如米般的菩提花,寶琴又笑著湊過來說要幫打理幹淨。
二人在這無人的寶寺後院倒也難得自在一番,笑鬧起來。隨後慢慢走遠,沈玉芙便帶著寶琴去了另一側的偏殿進香祈福。
二人走後不久,卻是一陣狂風刮過。
那紅綢墜著木牌在細枝上隻鬆鬆繞了一圈,又掛得那般高,木牌竟也被風直接吹落,徒留那截紅綢在空中著打了個旋兒,眼看就要落到地上。
所幸一隻手及時接住了那將要飛落泥上的紅綢。
顧如琢手指修長,掌心攥著紅綢了,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
Advertisement
他比沈玉芙二人還要早些時候便到了此,不過順著小道去了趟後山散心,回來時便見著兩位姑娘在此。
他站在有些泥濘的山路上,遠遠便瞧見了沈玉芙二人,卻又不好此時下山,唐突了兩位姑娘。大慶國民風雖然開放,但也不好被人瞧見孤男寡共在一。
顧如琢頓了頓步子,繁茂的林木也恰好能遮掩他的形。
他此時才略微抬眼認真看去。
樹下有一人兮,雲鬢花容,穠纖得衷,修短合度。春風輕拂,菩提花洋洋灑灑散落半空。這風也來的恰到好,輕輕掀起一闕雪白的角與肩後如堆雲般的長發。
人如畫,想來畫中仙,也不過如此。
顧如琢又低頭看了眼手中紅綢,憶起那小丫頭背過去的模樣。
他不是神佛,怎好窺探他人的願景。
但他也實在心生好奇。
來廟裏的姑娘眷無非求姻緣便是求家人安康,那般如畫如仙的姑娘,又會許什麽願呢?
他平手中紅綢,卻隻見上麵落拓不羈的寫了四個字。
顧如琢啞然失笑。
仙人果然與眾不同。
猜你喜歡
-
完結474 章

姑娘今生不行善
盛京人人都說沛國公府的薑莞被三殿下退婚之後變了個人,從前冠絕京華的閨秀典範突然成了人人談之變色的小惡女,偏在二殿下面前扭捏作態,嬌羞緊張。 盛京百姓:懂了,故意氣三殿下的。
94.2萬字8 13581 -
完結369 章

權臣心上撒個嬌
蕭懷瑾心狠手辣、城府極深,天下不過是他的掌中玩物。 這般矜貴驕傲之人,偏偏向阮家孤女服了軟,心甘情願做她的小尾巴。 「願以良田千畝,紅妝十里,聘姑娘為妻」 ——阮雲棠知道,蕭懷瑾日後會權傾朝野,名留千古,也會一杯毒酒,送她歸西。 意外穿書的她只想茍且偷生,他卻把她逼到牆角,紅了眼,亂了分寸。 她不得已,說出結局:「蕭懷瑾,我們在一起會不得善終」 「不得善終?太遲了! 你亂了我的心,碧落黃泉,別想分離」
65.4萬字8.18 6732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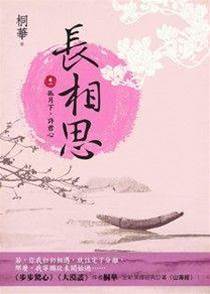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57 -
完結790 章

重生后我被繼兄逼著生崽崽
上輩子的謝苒拼了命都要嫁的榮國候世子,成親不過兩年便與她的堂姐謝芊睡到一起,逼著她同意娶了謝芊為平妻,病入膏肓臨死前,謝芊那得意的面龐讓她恨之入骨。一朝重生回到嫁人前,正是榮國侯府來謝家退婚的時候,想到前世臨死前的慘狀,這一世謝苒決定反其道而行。不是要退婚?那便退,榮國侯府誰愛嫁誰嫁去!她的首要任務是將自己孀居多年的母親徐氏先嫁出去,后爹如今雖只是個舉人,可在前世他最終卻成了侯爺。遠離謝家這個虎狼窩后,謝苒本想安穩度日,誰知那繼兄的眼神看她越來越不對勁? ...
106.2萬字8.18 218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