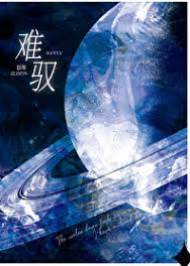《晚風》 第 35 節 湖風吻山茶
哥哥是京圈出了名的浪子。
和我在一起后,開始收心上岸。
所有人都說他我如命。
可他們不知道。
我早就聽到了他和兄弟的對話。
「你對林聽是認真的?」
他笑了聲,語調嘲弄。
「玩玩而已。
「我只是好奇,跟妹妹接吻是什麼滋味?」
1
宋思硯回家時,我眼疾手快地關掉了那封匿名郵件。
穿白襯衫的男人斜倚在玄關,微仰著頭,單手扯松領帶,含糊不清地喊我:
「聽聽。」
我沒理他,假裝專心致志地看漫畫。
下一秒,腰間多出一雙手,將我抱坐在桌子上。
漫畫掉落在地。
悉的冷松木香混著酒氣撲面而來。
「看什麼這麼出神?
「哥哥你都不應。」
我掙扎著想下去,卻被他按住了大。
宋思硯撿起漫畫,隨意瞥了一眼,嚨溢出一聲輕笑。
「原來聽聽喜歡這樣……」
炙熱的鼻息過我的耳廓。
我往后躲,吻卻落了下來。
齒廝磨的前一刻,我的腦海中忽然閃出那封郵件的容。
那是一段手機錄音。
有人問宋思硯:
「你對林聽是認真的?」
他笑了聲,語調嘲弄:
「玩玩而已。
「我只是好奇,跟妹妹接吻是什麼滋味?」
說來可笑。
我就是林聽,也是宋思硯的繼妹。
想到這,我猛地推開了他。
宋思硯愣了下,眼底褪去,只余一片清明。
他向來不會對我生氣,俯了下我的腦袋,我早點睡。
門關上的瞬間,我的眼淚不可控制地流了下來。
宋思硯追了我五年,我們在一起兩年。
這七年,他把我寵上了天。
所有人都說他我如命。
可我今天才知道,他對我,只是玩玩而已。
Advertisement
2
我十五歲就認識宋思硯了。
他是家世顯赫的天之驕子,績優異,長相出眾,幾乎沒有哪個孩不喜歡他。
我也一樣。
所以當我媽把我帶進宋家,讓我宋思硯哥哥時,我覺得我的天都塌了。
偏偏眼前的年不知,還溫地我妹妹。
宋思硯是個很好的哥哥。
他每天放學會來班里等我,接過我的書包,再遞來一包小零食。
他會幫我排隊打飯,我吃什麼不吃什麼,他記得清清楚楚。
某次測,我跑完一千米難地吐了,本應在上課的他沖到現場,背著我跑去醫務室。
第二天因為逃課被罰寫三千字檢討,他還邀功似的朝我笑。
「聽聽,哥哥對你好不好?」
我沒有回答。
因為我可恥地發現,宋思硯對我越好,我就越喜歡他。
我以為自己把這份心思藏得很好。
直到十七歲那年,我媽發現了我的日記。
怒火攻心,把我關進臥室,直接扇了我一掌。
「林聽,你腦子進水了是不是?
「宋思硯是你名義上的哥哥啊!
「如果被你宋叔叔知道,我們會被趕出去的,難道你還想回去過苦日子嗎?」
我媽揪著我的耳朵,越說越激。
我被打蒙了。
好半天沒緩過神。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離開的,回頭時,正好跟站在門口的宋思硯對上目。
「疼嗎?」
年骨節分明的手遞來藥膏。
我下意識捂住臉上的掌印,接過藥膏就想關門。
「等等。」
宋思硯單手抵住門框,整個人順勢了進來。
「剛才,我聽到了。」
腦子轟的一聲。
我漲紅了臉,語無倫次。
「不是,哥,我沒……」
剩下的話還沒說出口,宋思硯突然牽住了我的手。
Advertisement
溫暖干燥的掌心包裹著我的。
他子微傾,視線與我齊平。
漆黑的眼睛像一汪深潭,仿佛要將我吸進去。
「別我哥。
「你姓林,我姓宋。
「我們算哪門子兄妹,嗯?」
3
我還是拒絕了宋思硯。
喜歡是一回事,真正在一起又是另一回事。
可能我潛意識里也覺得,兄妹是不被世俗接的。
我沒有勇氣沖破樊籠。
被拒絕后,宋思硯像變了個人。
正值高三的他開始逃課,跟京圈里的其他公子哥們混在一起,點一堆兔郎開派對。
我給他打過很多次電話,都被拒接。
那段時間,宋思硯的名聲很差。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京圈出了名的浪子。
宋叔叔氣得肝疼,又無可奈何,給了我一個地址,讓我勸宋思硯回家。
去之前,我做足了心理準備。
可推開包廂門的那一刻,我還是清楚地聽見了心碎的聲音。
宋思硯躺在沙發上,指尖夾了煙,似乎喝醉了,任由一個人親吻他的角。
我竭力抑制抖的聲線,開口喚他:
「宋思硯。」
音樂太吵了,完全覆蓋掉了我的聲音。
他閉著眼,沒有聽見。
我走過去,直接拔掉了電源頭。
短暫的安靜過后,所有人的視線集中在我上。
「誒,不是,妹妹你誰啊?
「存心找不痛快呢。」
有個紅吊兒郎當地問我。
我沒理他,徑直走到宋思硯面前。
「宋思硯,跟我回家。」
我想把他推醒,手腕卻被紅拽住。
「你眼,等等,我想起來了。
「硯哥后媽帶來的妹妹?」
紅認出我后,不由分說地把我拉到懷里,一邊吹口哨,一邊讓人給我倒酒。
「妹妹難得來一次,陪哥哥喝兩杯咯。」
Advertisement
辛辣的烈酒遞到我邊。
男人的力氣太大,幾乎是在著我喝。
我嗆得眼淚直流。
后忽然傳來桌子被踹翻的聲音、腳步聲,然后是一句悉的:
「聽聽?」
我淚眼蒙眬地轉過頭。
宋思硯看清我的臉,忽地罵了句臟話,狠狠踹了紅一腳。
「你媽的。
「誰讓你用臟手?!」
4
宋思硯發了很大的火,差點把包廂砸了。
跟我回家時,特意離我好幾米遠,我讓他過來,我有話想問他。
他搖頭拒絕:
「不要,我上臭。」
我只好過去,耐心地問他: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不接我電話。
為什麼跟他們廝混。
為什麼讓別人親你。
宋思硯始終低著頭,不敢看我,好半晌才支支吾吾道:
「我跟我爸說,我喜歡你。
「他說他死都不可能答應,我沒辦法,只好演了這出戲。
「你看老頭子急得,都讓你來找我了。」
我盯著他角明顯的口紅印。
心中酸。
宋思硯察覺到我的視線,拿手背狠狠過瓣,小心翼翼地解釋:
「我剛才喝醉睡著了,不知道有人親我。」
我一言不發。
他急了。
拼命,皮都破了也不停手。
我無奈地嘆了口氣:
「好了,先回家,宋叔叔還在等你。」
那天,宋思硯走進書房,直到天黑才出來。
見到我,猛地將我抱在懷里。
他喜極而泣:
「聽聽,我爸同意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當時的心,驚訝欣喜之余,好像又多了幾分煩躁不安。
我不確定。
我是不是在膈應宋思硯被別的人親了。
抑或是擔心他裝墮落裝得那麼像,以后會不會真墮落。
于是,我晾了宋思硯五年。
Advertisement
這期間,他的兄弟都勸我:
「硯哥邊現在連只母蚊子都沒有,整天圍著你打轉。
「如果硯哥對你不是真心,我們就去吃屎。
「林聽,你就當可憐可憐他,答應他吧。」
宋思硯追我那五年,溫,從沒對我發過脾氣。
偶有,他就捧著一束白山茶,等在我宿舍樓下,一站就是一整天。
我跟他說你走開,我現在不想看見你。
他嗯了聲,乖乖挪去我看不見的角落,繼續等,像一條被拋棄的小狗。
宋思硯對我好到,兩年,有時候明明是他錯,我卻舍不得兇他。
我越來越他,也越來越離不開他。
直到那封匿名郵件,給我當頭一棒。
我才明白——
墮落過的人,哪有那麼容易上岸。
5
「聽聽,睡醒了?」
我一夜未眠,睡眼惺忪地起床,聽見宋思硯的聲音。
他等在浴室門口,心地好牙膏,遞給我。
「愣著干嗎?
「要我給你刷啊。」
我扯了扯角,口中的泡沫四散開,鏡中映出宋思硯寵溺的眼神。
「早餐想吃什麼,我給你做。」
我安靜地洗漱完,沒有理他。
宋思硯挑了下眉,指節叩過我的鎖骨。
我仰起頭看他。
他被我盯得眸漸深,偏頭吻了下來。
瓣相,呼吸融。
一吻結束。
他饜足地勾了勾:
「今天怎麼這麼乖?」
以前氣氛很好或者適合接吻時,我總會推開他。
因為我每次都忍不住想起那個人親他的畫面,心百般抵。
這次,我卻沒有躲。
指腹劃過他瀲滟的瓣,我面無表地問:
「跟妹妹接吻是什麼滋味,你會到了嗎?」
空氣一片死寂。
宋思硯愣了幾秒,臉微變。
「聽聽,你……」
我靠在洗手臺邊,平靜地注視著他。
「你在說什麼?」
宋思硯一臉茫然。
我有耐心地掏出手機,點開那段下載好的錄音,放給他聽。
悉的對話再次回在耳邊。
我的心仿佛被一無形的線纏住了,越收越,幾乎不過氣。
等播放完畢,宋思硯才抬眸看我。
他沒有半分慌,反而低笑了一聲。
「這是 AI 合的。
「聽聽,我喜歡你快喜歡得瘋掉了。
「怎麼可能說這種話?」
其實,我不是沒懷疑過這段錄音的真實。
可我實在太了解宋思硯,他說話時的語氣、腔調,跟錄音里如出一轍。
而且問他問題的兄弟,我也能聽出來是誰,鬼才信是 AI 合。
我回手,避開他的,后退了一步。
「宋思硯,我們還是分手吧。」
清晨的悠然落進他的眼底。
他沉默又委屈地著我,好像我欺負了他似的。
「不要。
「因為一段來歷不明的錄音,你要離開我?
「這對我不公平。」
我看了他很久,企圖從他的神中找出一破綻,可是沒有。
好像錄音里說只是玩玩我的人,不是他。
好像他真的清清白白。
「你是不是覺得我好騙的,哥?
「覺得哄我幾句,我就會相信,對嗎?」
時隔七年,我第一次沒有他的名字。
而是他哥哥。
宋思硯抱我抱得很,幾乎想把我進骨子里。
「不是這樣的,聽聽。」
他的呼吸噴灑在我的鎖骨,繾綣地纏上我的脖頸。
「你總得給我時間,讓我證明。」
我不想讓他蹭,著他的后頸,把他的腦袋提起來。
他乖乖站好,音帶啞。
「我現在真的很你。」
語氣很真誠。
但我不信。
6
我坐在宋思硯的車上,整個人有點混。
明明剛才拒絕他送我上班,他卻像沒聽見似的,直接抱起我塞進副駕。
抵達畫室樓下,他扣住我的腰肢,把我在座椅上親了很久。
我掙不開他的桎梏,只能嗚嗚地抬腳踹他。
「放開……」
急之下,我咬了他一口。
宋思硯吃痛松開了我,毫不在意地挑。
「嘶,這麼兇啊。
「開始討厭哥哥了?」
我抬眼瞪他。
他低笑一聲,了我的腦袋。
「乖,晚上我來接你。
「到時給你一個代。」
他口中的代,大概是指查清那封匿名郵件是誰發的。
車門解鎖。
我立刻跳了下去,頭也不回地沖進畫室的專屬電梯。
調整好急促的呼吸。
電梯門緩緩闔上。
突然,一雙锃亮的皮鞋出現在視野里。
「勞駕。」
猜你喜歡
-
完結49 章
黑白
他是至純的黑色,她是純淨清透的白。 從遇到她起,他就不曾打算放走她,這是一種執念。 哲學上這樣定義它,一個人過分專注於某事某物,長時間淪陷於某種情緒,這一情結就會成為有形,將之束縛住。而他,有執念,亦有將之執行的資本。 於是他終於出手,親手折斷了她的翅,從此把她禁在身邊。
13.8萬字8 8139 -
連載994 章
一夜驚婚夫人超有錢
五年前,蘇晚心識人不清,被最親近的人陷害出軌神秘陌生人,父親身死,送進精神病院,流言加身萬劫不複。五年後,她從國外攜萌寶歸來華麗變身,卻被孩子的便宜爹纏上,聽說本以為便宜爹身無分文,還要賣身接客賺錢?為了寶寶有個爹,蘇晚心豪擲三百萬,“彆工作了,你帶孩子,我養你,每個月三百萬。”突然被養的男人:???助理:“老闆,太太買房看上那棟三千萬的彆墅是我們開發的。”費總:打一折,送她!助理:太太說太便宜了,要再買十套!費總表示,十套彆墅,難道我送不起?房子隨便送,錢隨便花,都是他家的,肥水不流外人田!一夜驚婚夫人超有錢
96.6萬字8 178121 -
完結953 章

結婚後,殘疾大佬站起來了
被人陷害,她與他一夜荒唐,事後,她代替妹妹嫁給輪椅上的他。 都說傅家三爺是個殘廢,嫁過去就等於守活寡。 誰知她嫁過去不到三個月,竟當眾孕吐不止。 眾人:唐家這個大小姐不學無術,這孩子一定是她揹著三爺偷生的野種! 就在她被推向風口浪尖的時候,傅景梟突然從輪椅上站了起來,怒斥四方,“本人身體健康,以後誰再敢說我老婆一個不字,我就讓人割了他的舌頭!” 感動於他的鼎力相助,她主動提出離婚,“謝謝你幫我,但孩子不是你的,我把傅太太的位置還給你。” 他卻笑著將她摟進懷中,滿心滿眼都是寵溺,“老婆,你在說什麼傻話,我就是你孩子的親爸爸啊。”
96.6萬字8.18 118489 -
完結1725 章

夫人她是個小作精
醫院裏一場驚心設計的陰謀,季溫暖從豪門真千金,淪為了親爹不疼,親媽不愛的鄉下野丫頭。十九歲,親媽終於接她回家,隻為逼她把婚事讓給假千金妹妹。腦子一熱,季溫暖盯上了前未婚夫的小叔叔。眾人皆知,有權有錢又有顏的秦家四爺小的時候被綁架,受了傷,從此吃齋念佛,生人勿近。家財萬貫隨便花,還不用伺候,完美!“四爺,我看您麵若桃李,命犯爛桃花,隻有做我的男人,方能逢兇化吉。”某人眸色沉沉,“叫大叔,就答應你。”“大叔。”某天,季溫暖發現實際情況根本不是傳聞的那樣,她要分手!“不分手,我把錢都給你。”
162.5萬字8 98972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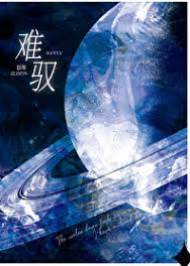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18 11698 -
完結202 章

暮夏婚約
顧念一在24歲這年同一個陌生人結婚,平靜的生活被打破。 彼時,她只知道陸今安是南城首屈一指的陸家長子,前途無量的外科醫生。 顧念一與陸今安的第一次見面是在民政局,他遲到了2個小時,矜貴清雋、棱角分明的面容中,盡顯疏冷。 婚後的兩人井水不犯河水,結婚證被陸今安隨意扔在抽屜裏。 某天,顧念一去醫院,無意間撞見矜貴落拓的男人與朋友在辦公室閒聊,被問及這樁突如其來的婚事時,陸今安淡漠開口:“不過是完成老人的囑託罷了。” 不繼承家族企業、不爲情所動的人,怎會上心婚姻。 — 婚後某日,顧念一在次臥獨自落淚,陸今安猶豫之後將她擁在懷裏,任由淚水打溼他的襯衫。 翌日,陸今安笨拙搜索如何安慰女生,奔波在全城尋找顧念一喜歡的玩偶的所有聯名款。 朋友控訴,“怎麼哄老婆了,這是上了心?” 陸今安腳步一頓,眸色深沉,“不想她哭。” 後來,一場百年一遇超強降雨襲擊南城。 外出採集信息的顧念一被暴風雨困住,與外界失去聯繫。 推開她面前擋板的是陸今安。 顧念一第一次見到陸今安狼狽的樣子,單薄的襯衫被雨水打溼,手指骨節處帶着斑駁血跡。 一步一步走近她,溫柔地說:“老婆,抱抱。”
28.3萬字8 940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