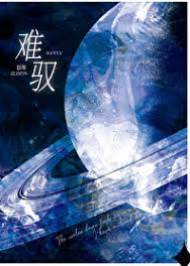《前妻歸來》 第159章 此地無銀三百兩
曾經他那雙拒人之千里以外的冷眸如今如一剪秋水般深邃的看了一眼懷裡的樊奕菱,他的角噙著一抹邪魅的笑,好看的桃花眼睛散發著迷人的,這時的冷沉風挑戰般的看向門口的來人。
門口的人見二人抱在一起,原本勾魂懾魄的明眸變得森,宛如純種的草原惡狼在冬日荒涼的乾燥中覓食般艱難,他衝過去,一把扯開冷沉風,用力將冷沉風推出去,一手將樊奕菱摟著自己懷裡,一手指著冷沉風大罵:“你個變態!”
冷沉風退了幾步站定腳,“你不是不要了嗎?幹嘛這麼激?讓你去找找他你都不願意,你現在來幹嘛?”
被說的頓時啞口,曾經他是多麼沉靜與高傲,而此時卻除了有憤怒,還有點兒可憐像,屬於他的那王子般的認真與威嚴已經然無存。
尷尬的角蠕了幾下,沒有對上冷沉風的話,轉頭抓著樊奕菱的胳膊,從頭至腳打量了一下,確定安好,才放心的說:“樊奕菱,對不起,我……”
“現在姓冷!”冷沉風截斷的話,指著對樊奕菱說:“奕菱,你考慮好,他是不是真的你。”
“住!”回頭瞪著冷沉風,聽到他奕菱,他就生氣,他還每次樊奕菱都連名帶姓,冷沉風這個東西,總是樊奕菱小名。
“我沒有和你說話,我在和妹妹說話,你算什麼東西?”冷沉風走進一步,冷冷的對說:“你這種朝三暮四,喜新厭舊的花花公子,不配我們奕菱,你最好放開他從哪來滾哪去!”
“你又想捱打!”一字一頓的說著,輕輕推樊奕菱出懷,好像用力都會疼似的,對冷沉風橫眉冷對,一副又要打他的樣子。
Advertisement
“!以前我看在燦燦的面子上,我讓著你,今天我到想教訓一下你!你這個僞君子!你一邊哄我妹妹,一邊還和別的人上牀!”冷沉風狠狠的朝過一拳去,“更可氣的是,你盡然還敢惦記著燦燦!我今天我非要教訓你一下不可!”
本來是要還手的,可一聽冷沉風后面的話,原來這貨不是給樊奕菱出頭了,只是藉著給樊奕菱出氣的由頭,他真正的目的是生氣他惦記著燦燦了。
“砰”的一拳,冷沉風的拳頭就在了的臉上,這一拳可真是夠用上力了,正像每次打他那樣,擡起頭時,就覺裡有鹹鹹的味道,覺到角有流下時,知道出了,他了一下角。
如果冷沉風好好說,也許他會解釋一下的,可是,冷沉風盡然敢打他,他揮起拳頭,兩人打起來。
“別打了,你們住手。”樊奕菱害怕張,可是那兩人就像是千年的仇人一般,扭打在一起,樊奕菱同以前一樣,圍著他兩在地上轉了幾圈後,發現自己的話對此時打的火熱的兩人毫無作用,拿起包包朝外面走去。
門口,樊奕菱留下一句話:“你們兩都死在這裡,就當我花五十億給你們兩買了墓地!”
兩人停下來一起朝門口追去。樊奕菱已經從外面把門鎖了,兩人搖著門,“奕菱,開門,別鎖門。”
“樊奕菱!你幹嘛?快把門打開,聽我解釋。”
“你有什麼好解釋的?都和別人懷上孩子了!你還解釋個屁!”冷沉風鄙夷的看著。
“找死你……”
“這間門都不許給我打開!”的半截話後,就聽到樊奕菱在外面對保安和員工說,接著樊奕菱的腳步聲越來越遠。
Advertisement
被鎖在屋裡的兩人一起朝窗戶跑去,然後兩人又一起回了頭,樓層不算高,也就一共七層,而他們正在第七層上。
第二天,樊奕菱在校園裡被燦燦截住,燦燦首先道了歉,之後又說:“奕菱,鑰匙呢?”
“什麼鑰匙?”
“你辦公室的鑰匙!你想鎖他們到什麼時候?”
“那是我給他們置辦的墓地!”樊奕菱扭頭就走。
燦燦追上去,跟在樊奕菱的後,“奕菱,別鬧了,昨晚我爸媽到找呢,冷沉風家也快急死了,你快把他們放出來吧。”
“不放!”樊奕菱倔強的走,也不停步。
“你想把他們關到什麼時候啊?!”燦燦停住腳步在原地跺腳。
“關到他們死!”樊奕菱回頭回了一句然後毅然離開。
燦燦回到家裡,告訴騰項南和寧雪,樊奕菱把和冷沉風關了辦公室裡。
騰項南不以爲然,認爲樊奕菱就是鬧小孩子脾氣,讓出出氣就會把和冷沉風放出來的。再說了,人樊奕菱關關他們兩,教訓他們一下也可以啊,就讓奕菱關著他們吧。
寧雪推開騰項南,瞪著他,對燦燦說:“那找人把門打開不就行了,都關了一夜了,氣也消得差不多了吧?”
“媽,樊奕菱安頓了中心的保安,不許讓外人進去,誰也不許打開那扇門,我去過,本連大門也進不去。”
歐笑笑站在樓梯口聽到了他們的談話,朝樓上走去。
樓上,歐笑笑到了一新。
歐笑笑比一新高半頭還多呢,一個十四五碎的小孩站在面前,可一點兒也不怕,反而覺得自己報仇的機會來了,就一新那,早就在第一次見面時就惹下了,可還記著愁呢。
Advertisement
一新當著那麼多人的面,給下不了臺,有人在時需要裝著可憐才能得到同票,現在樓上就和一新,歐笑笑心裡直得意自己機會來了,要好好教訓一下這個不知死活的小丫頭。
讓從此就怕了自己,在歐笑笑的生涯裡,還沒有鬥不過的人呢!
一新到沒想多,就是看見了歐笑笑心裡就不爽,大大咧咧的朝歐笑笑走過去,隨口就說:“喲!老母這是去哪兒了?不在屋裡好好下蛋,出來小心把小夭折了。”
本來歐笑笑想找茬罵一新幾句在收拾的,沒想到這個死丫頭盡然又先罵,歐笑笑擡手朝著一新打去,“你這著小賤人!今天姑就撕了你的!讓你囂張!”
一新雖然個子小,可是,和騰項南一直有練拳,鍛鍊,騰項南也給過一些基本的防,歐笑笑本不知道這些,只知道眼前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丫頭沒個子高,沒心眼多。
看見歐笑笑擡起掌來,一新把花拳繡一點兒也放在眼裡,反而揚著小臉等扇過來的耳。
歐笑笑心裡直笑一新傻,小個子一個,盡然不躲,還揚起小臉等捱打,以爲不敢打嗎?歐笑笑纔不會怕!到時候就算一新告狀,就說一堆一新的壞話,大人們也不會怪他。
於是,歐笑笑用足了全力氣,朝一新扇去掌,就在歐笑笑的手落下的時候,一新輕巧的一蹲,歐笑笑的就超前傾去。
結果因爲站不穩重心,眼看就要摔倒的時候,歐笑笑擡步往前好幾步,總算沒跌倒,就在歐笑笑就要站穩的時候,一新朝著的屁上狠狠的踢去一腳。
Advertisement
“啊!”歐笑笑一個狗吃屎爬了地上。翻起來照著一新又打去。
一新出手快,一把上去揪住歐笑笑披散的大卷發拉著就拖在了牆上,歐笑笑雙手護著頭,按著被一新揪疼的頭髮,慌張的本顧不上還手。
說一新快會罵人,可是大家都還不知道,一新的打架比罵人那可強的不是一星半點兒。像歐笑笑這種貨,就是上功夫,潑辣也就是蠻用力,想和一新小朋友打架,簡直自找死路。
一新早就看不順眼了,每天抹的跟鬼似的,在騰家招搖,還把那個笨蛋樊奕菱走,雖然那個笨蛋笨,但是比歐笑笑可多了。
一新一聽歐笑笑盡然這樣罵,一新是誰啊?吃這套?一新揪著歐笑笑的頭髮,一隻手猛扇歐笑笑的臉,而且左右臉都開工,歐笑笑護著頭皮,又要護臉,一瞬間都傻了。
“姑到到看看誰先撕了誰的,敢在騰家囂張?誰給你的膽子?賤貨!啪啪!”
歐笑笑用盡全力推開一新,連連後退,哆嗦著說:“你……你敢我!我的肚子裡可懷著你哥的孩子呢!”
一新扔掉手裡那把歐笑笑的頭髮,“呸!”的吐了一口,譏諷的說:“誰知道是誰的野種?你賠懷我們騰家的兒孫?你有那命嗎?”
隨著一新一步步的近,歐笑笑也見識了的力氣和兇猛,嚇得失,手捂在肚子上,繼續後退,“你別過來,孩子掉了你可擔不起……”
“我呸!”一新朝地上吐了一口,“我把你這孽種打掉,我家祖先還得謝我呢!還得給我記上一大功勞呢!”
一新說著擡腳就朝歐笑笑的肚子踢去。
“啊!”歐笑笑一下子就被一新的鐵腳踢的跌倒在地上了,哇哇的朝樓下大:“救命啊,救命啊!”
樓下騰項南夫婦和燦燦聽到歐笑笑的聲,燦燦急著就往上跑,騰項南和寧雪到互相看看,不不慢的朝樓上走去。
他們知道,這會就歐笑笑和一新在樓上,是歐笑笑喊救命,又不是他們的寶貝兒喊救命,他們可不著急。
燦燦跑到樓上,一看歐笑笑坐在地上捂著肚子哭,一新挽著袖子,一副俠肝義膽向前衝的樣子,趕抱住一新,“一新,你幹嘛打?”
“姐,你不知道,敢罵我!還想打我!”一新推著燦燦,燦燦和一新力氣差不多大小,又比一新個子高,抱著一新,一新就不了了。
慢吞吞走上來的寧雪和騰項南看著眼前的景,似乎不驚訝,也似乎和他們沒有關係似的。
歐笑笑見了寧雪和騰項南,站起來跑到騰項南的面前,抱著騰項南的胳膊就哭著說:“叔叔,一新踢我肚子,我……”
騰項南嫌棄的推開歐笑笑的手,往後退了一步,寧雪不高興的看著歐笑笑抱過騰項南胳膊的手,在騰項南退後的時候,往騰項南前面站了一步。
冷的臉,寧雪淡漠的問:“怎麼了這是?”
“阿姨,一新踢我的肚子,我肚子現在好疼啊。”歐笑笑捂上自己的肚子。
“那就去醫院吧。”寧雪沉這臉,站在不,好像在徵求歐笑笑的意見,看用不用去醫院。
“我不去醫院!”歐笑笑口而出的話,讓騰項南和寧雪淡漠的臉上泛起一波瀾,歐笑笑臉上頓失,捂著肚子站在原地趕說:“我害怕,我不了了。”
“那就醫生來。”寧雪眼底閃過一狡黠,對燦燦說:“燦燦,去給醫生打電話,讓他快點來一趟。”
寧雪將快點二字說的很重,說的時候,看著歐笑笑的臉。
“阿姨,我估計沒事,一新也沒有踢用力我……”
“胡說!”一新在燦燦放開時,跑到寧雪的邊抱著寧雪的胳膊,“媽,我很用力踢了,還好好的,看來的肚子有問題!我見電視和言小說都寫,跌倒就能流產,你看看,我都踢那麼重,還跌倒了,都沒事,肯定有問題!”
“你,胡說!醫院裡超聲波怎麼會有誤?”歐笑笑有些吞吐的言詞,心裡也慌了。
“笑笑,先回屋去休息,一會兒讓大夫給你來檢查一下。”寧雪淡淡的味道,不像剛纔那麼冷漠了,好像心比剛纔好了一般。
猜你喜歡
-
完結49 章
黑白
他是至純的黑色,她是純淨清透的白。 從遇到她起,他就不曾打算放走她,這是一種執念。 哲學上這樣定義它,一個人過分專注於某事某物,長時間淪陷於某種情緒,這一情結就會成為有形,將之束縛住。而他,有執念,亦有將之執行的資本。 於是他終於出手,親手折斷了她的翅,從此把她禁在身邊。
13.8萬字8 8139 -
連載994 章
一夜驚婚夫人超有錢
五年前,蘇晚心識人不清,被最親近的人陷害出軌神秘陌生人,父親身死,送進精神病院,流言加身萬劫不複。五年後,她從國外攜萌寶歸來華麗變身,卻被孩子的便宜爹纏上,聽說本以為便宜爹身無分文,還要賣身接客賺錢?為了寶寶有個爹,蘇晚心豪擲三百萬,“彆工作了,你帶孩子,我養你,每個月三百萬。”突然被養的男人:???助理:“老闆,太太買房看上那棟三千萬的彆墅是我們開發的。”費總:打一折,送她!助理:太太說太便宜了,要再買十套!費總表示,十套彆墅,難道我送不起?房子隨便送,錢隨便花,都是他家的,肥水不流外人田!一夜驚婚夫人超有錢
96.6萬字8 178121 -
完結953 章

結婚後,殘疾大佬站起來了
被人陷害,她與他一夜荒唐,事後,她代替妹妹嫁給輪椅上的他。 都說傅家三爺是個殘廢,嫁過去就等於守活寡。 誰知她嫁過去不到三個月,竟當眾孕吐不止。 眾人:唐家這個大小姐不學無術,這孩子一定是她揹著三爺偷生的野種! 就在她被推向風口浪尖的時候,傅景梟突然從輪椅上站了起來,怒斥四方,“本人身體健康,以後誰再敢說我老婆一個不字,我就讓人割了他的舌頭!” 感動於他的鼎力相助,她主動提出離婚,“謝謝你幫我,但孩子不是你的,我把傅太太的位置還給你。” 他卻笑著將她摟進懷中,滿心滿眼都是寵溺,“老婆,你在說什麼傻話,我就是你孩子的親爸爸啊。”
96.6萬字8.18 118489 -
完結1725 章

夫人她是個小作精
醫院裏一場驚心設計的陰謀,季溫暖從豪門真千金,淪為了親爹不疼,親媽不愛的鄉下野丫頭。十九歲,親媽終於接她回家,隻為逼她把婚事讓給假千金妹妹。腦子一熱,季溫暖盯上了前未婚夫的小叔叔。眾人皆知,有權有錢又有顏的秦家四爺小的時候被綁架,受了傷,從此吃齋念佛,生人勿近。家財萬貫隨便花,還不用伺候,完美!“四爺,我看您麵若桃李,命犯爛桃花,隻有做我的男人,方能逢兇化吉。”某人眸色沉沉,“叫大叔,就答應你。”“大叔。”某天,季溫暖發現實際情況根本不是傳聞的那樣,她要分手!“不分手,我把錢都給你。”
162.5萬字8 98972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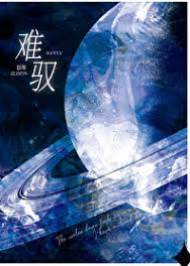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18 11698 -
完結202 章

暮夏婚約
顧念一在24歲這年同一個陌生人結婚,平靜的生活被打破。 彼時,她只知道陸今安是南城首屈一指的陸家長子,前途無量的外科醫生。 顧念一與陸今安的第一次見面是在民政局,他遲到了2個小時,矜貴清雋、棱角分明的面容中,盡顯疏冷。 婚後的兩人井水不犯河水,結婚證被陸今安隨意扔在抽屜裏。 某天,顧念一去醫院,無意間撞見矜貴落拓的男人與朋友在辦公室閒聊,被問及這樁突如其來的婚事時,陸今安淡漠開口:“不過是完成老人的囑託罷了。” 不繼承家族企業、不爲情所動的人,怎會上心婚姻。 — 婚後某日,顧念一在次臥獨自落淚,陸今安猶豫之後將她擁在懷裏,任由淚水打溼他的襯衫。 翌日,陸今安笨拙搜索如何安慰女生,奔波在全城尋找顧念一喜歡的玩偶的所有聯名款。 朋友控訴,“怎麼哄老婆了,這是上了心?” 陸今安腳步一頓,眸色深沉,“不想她哭。” 後來,一場百年一遇超強降雨襲擊南城。 外出採集信息的顧念一被暴風雨困住,與外界失去聯繫。 推開她面前擋板的是陸今安。 顧念一第一次見到陸今安狼狽的樣子,單薄的襯衫被雨水打溼,手指骨節處帶着斑駁血跡。 一步一步走近她,溫柔地說:“老婆,抱抱。”
28.3萬字8 940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