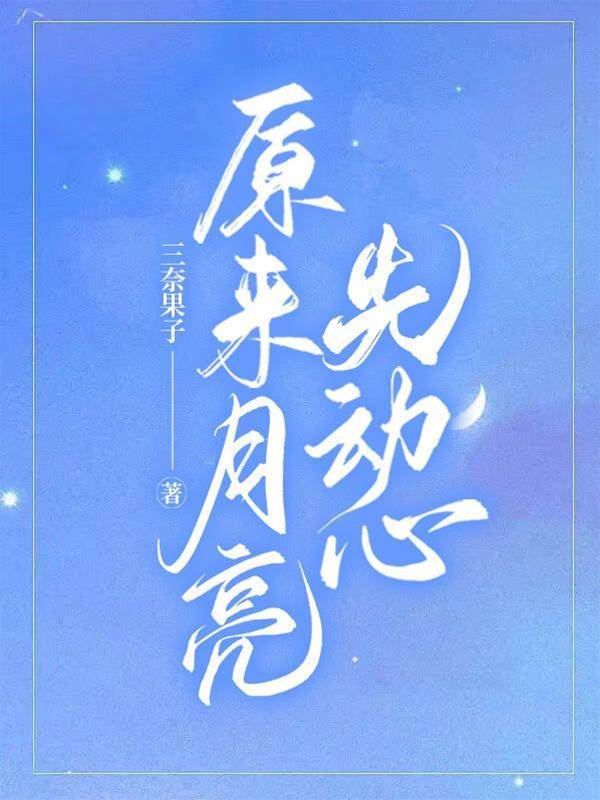《黃雀雨》 第46章 #46
然后又翻箱倒柜,找到了那瓶安-眠藥。
他不知恐懼更多,還是憤怒更多,直接把整瓶藥,連同撕碎的書一同沖進了馬桶里。
后來凌雪梅回家,應當很快就發現東西沒了,找他質問,他半哀求半勸說,讓凌雪梅想一想他,再想一想妹妹。
他們已經沒了爸爸,不能再沒有媽媽。
他讓凌雪梅答應他,不要再有輕生的念頭。
他是長子,他馬上就年了,任何事,他都可以替去扛。
在他不斷地懇求之下,凌雪梅終于答應,不會再尋死。
之后的那一陣,凌雪梅似是從丈夫去世的沉痛打擊里恢復過來,又變回了那個溫可親的模樣。
陸家死氣沉沉的氛圍,似乎也終于稍有起。
然而,這樣的日子只過了三個月不到,那年夏天的某個傍晚,凌雪梅消失了。
沒留下任何東西,也沒帶走任何東西。
報警之后,直到第四天,陸西陵接到電話,讓他去派出所認尸。
還穿著常穿的那條素碎花長,只是整個人,已經高溫的湖水泡脹得面目全非。
那時他沒有別的想法,背過去就吐了。
之后的整整兩個月,他幾乎每晚都做噩夢。
夢醒來,一個人坐在黑暗里,既覺得怨恨,又覺得后悔。
怨恨在于,答應過,發過誓,說過不會拋下他們兄妹不理。
而后悔在于,或許,那瓶安-眠藥能夠讓走得輕松一些,那麼漂亮溫的人,死狀卻那樣可怖。
Advertisement
他更多的,是憎惡自己的自私與無能為力。
父親去世以后,爺爺對凌雪梅更加刻薄,他總覺得,是凌雪梅攛掇得陸頡生放棄文職工作去做野外考察。
前些年害得他們父子不能團聚不說,現在又間接害死了陸頡生,要是陸頡生安安穩穩坐在辦公室里,哪會到什麼狗屁山洪泥石流。
彼時爺爺怨氣沖天,以淚洗面,妹妹休學在家。
撐了半年,再也撐不了。
于是,第二次的道別無聲無息,半封書都不曾留下。
人世間總用教條規訓,“為母則剛”,好像做了母親的人,就不可以自私,不可以弱,就理應奉獻犧牲,掙得一個“偉大”名聲。
人類虧欠無數母親,只肯許以“偉大”的空頭支票。
甚至,他似乎都在用這條法度去要求凌雪梅,直至現在才全然醒悟。
如果放棄生命,和陸頡生重逢,是對而言更自由的選擇,那麼,沒關系。
他已經承擔起了長子的責任。
而可以自由地做一個人,而不必是母親。
陸西陵將還剩一截的煙,碾在煙灰缸里,手,抬起了夏郁青埋在他肩頭的臉頰,一時啞然失笑,“這也要哭啊?”
夏郁青嗚咽一聲,“我心疼阿姨,也心疼你。”
“那你親我一下。”
夏郁青抬頭輕一下。
“太敷衍了。”
夏郁青再一下。
陸西陵笑了聲,仿佛無奈,手的耳朵,“走吧,睡覺去。”
Advertisement
搖搖頭,仿佛非要取得他的認可不可,第三次抬頭去親他,不再蜻蜓點水。當舌-尖輕掃過他的,將要退開時,他驀然手,一把按在腦后。
主權替,抓他的領,對抗一種力盡失,沉沼澤的錯覺。
陸西陵退開,夏郁青低下頭,將額頭抵在他頸窩。
他側低頭,手指拂開了頭發,出發燙的耳朵,他輕笑著了一下,目隨即自耳后掃去,看見背后,脊骨微微突出的第一節。
他用微涼手指輕。
夏郁青抬起頭來,與他目相對。
只一瞬,他結微,折頸垂頭,一秒鐘也沒再猶豫,直接將吻落在脊骨骨節,像將一粒火星,投干枯的蘆葦叢。
只為親吻已經遠遠不夠。陸西陵一把抱起,回到臥室。
絕對的黑暗予以夏郁青絕對的安全,他想讓不要那樣張。
緩慢而耐心的,像是將一首夜曲的序章,彈奏過無數回合。
陸西陵在黑暗里一遍一遍吻,比在皮上烙下一枚不可更改的印記還要鄭重,“……痛就跟我說。”
搖頭,雙臂擁抱他,微的聲音里有種決然的堅定,“我不怕。”
*
等日出是突發奇想,因為天已經要亮了。
這樓層足夠高,臺的視野也足夠開闊。
夏郁青新換的干凈睡外面,又披了一張薄毯,抱膝坐在放置于落地窗前的坐墊上,過黯淡夜,去捕捉江面上船只的燈火。
Advertisement
一陣冰涼上臉頰。
夏郁青一下脖子,手接過指名要的冰可樂。
陸西陵坐下,支起一條,轉頭看一眼,順便將肩頭落的薄毯往上撈了撈,輕聲問:“有沒有哪里不舒服?”
夏郁青別過目,不好意思看他,拉開拉環時,搖了搖頭。
——自詡不怕的人,真正到了那個時刻,卻莫名其妙怕得要死,明明是完全可以忍的痛覺,卻好像本控制不住眼淚。陸西陵嚇到,要退出也不讓,就這麼抱著他,噎噎地讓他繼續。
說,覺得自己約怕的是一些象的東西。
從前反正是一無所有,做什麼都有種豁出去的孤勇。
現在卻會害怕失去。
夏郁青喝了一口冰可樂,發出微微暢快的一聲嘆。
隨即將可樂遞給陸西陵,“你喝嗎?”
陸西陵搖頭。
一時促狹的心思,自己喝了一口,偏頭湊過去,剛要到他的,突然慫了,立馬往后退。
陸西陵自然不讓,手摟住的后頸,將按回來,這個人總在奇怪的地方大膽,又沒本事大膽到底。
陸西陵吞去那一口可樂,這才笑說:“也就這點膽子。是不疼了是嗎?”
“……你什麼意思。還不夠是嗎?”
“你覺得呢?”
夏郁青打他一下,“……我會死的。”
“怎麼死?”陸西陵挑眉。
立即雙手蒙住耳朵。
鬧了一會兒,夏郁青將易拉罐放遠,枕在他肩膀上。
Advertisement
不過片刻,便開始打呵欠。
“青青。”
“嗯?”夏郁青轉頭看一眼,為他驟然嚴肅的語氣。
臺的燈沒開,只有客廳里亮了一盞落地燈,外面夜一分淺似一分,出黑被洗褪后的天。
在黯淡的線里瞧,他不笑時,眉目總有薄雪微霜的冷,可這樣的人一旦燃燒,卻是焚盡一切的熱烈。
而是他的火種。
陸西陵平聲說:“以后的事,誰也說不準。你或許不會永遠擁有某些東西,但你一定永遠擁有我。”
“永遠嗎?”
“永遠。”
可以不必相信其他人,但或許可以相信陸西陵。
他從來沒有對食言過。
夏郁青最終還是沒有等到日出,在天亮之前,就已經趴在陸西陵的上,呼呼地睡了過去。
陸西陵喝完了那一罐可樂,拿手機替錄了一段日出的視頻,而后連人帶毯子地一把抱了起來。
某人喝了可樂沒刷牙,希不要明天睡醒了嚷著牙疼。
猜你喜歡
-
完結581 章
總裁的午夜情人
黑暗房間,男人將柔軟甜美的女人壓在牀上,溫柔又瘋狂,不顧她的求饒…第二日他全酒店通緝,發誓找到昨夜青澀又惹火的女人."我娶你!"身邊的女人層出不窮,他最終伸手指向了她,這一刻她以爲找到了幸福,滿懷期待嫁給他,可後來才知道,他要的不過是一份天價遺囑.
141.9萬字7.91 88485 -
完結645 章
大佬她真不想當團寵啊
聽說池家那位從小被養在農村,連高二都沒讀完的大小姐被領回來了!眾人幸災樂禍等著看笑話。可沒想到——京都頂級四大世家為什麼全都巴巴的把孫子、兒子送來和池歸同班?享譽世界的醫學大拿為什麼如此親切又熟識的和池歸聊天?還有傅家那位心狠手辣,無人敢惹的太子爺,為什麼畫風突變,天天在群裡曬池歸?其他人:「我女友做飯好!」「我寶貝彈琴好!」傅斯:「我老婆屍體解剖的好。」眾:……池歸:……這些人好煩啊。
66萬字8.18 99167 -
連載2850 章
慕少嬌妻是大佬
(夏安心慕北宸)【傻妻+超甜寵妻護夫+男強女強+馬甲】從小生活在鄉下的夏安心,嫁給了慕家殘廢,不僅毀容還眼瞎的男人。所有人都在笑話,傻子和丑八怪是天生一對。可就在眾人捂嘴大笑時,慕北宸摘掉眼鏡,撕掉面具,從輪椅上站了起來。整個都城的女人都瘋狂了。誰說這是殘廢丑八怪,這是個超級鉆石王老五,絕頂男神。男人霸道抱住夏安心,語調狹冷,“誰說我老婆是瞎子?嗯?”一堆馬甲嘩嘩掉。神秘神醫是她,催眠大師是她,著名歌手也
273.3萬字8 139516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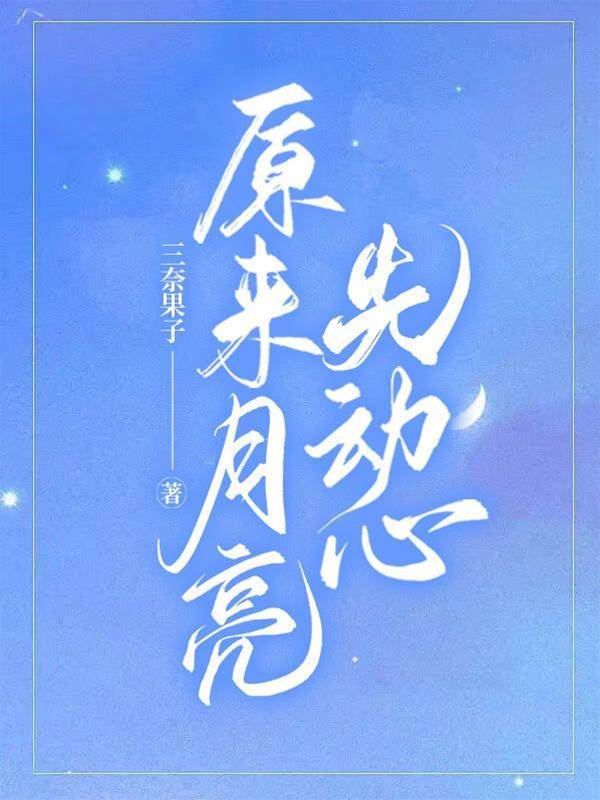
原來月亮先動心
【已簽約出版】原名:《喝醉後,我錯撩了閨蜜的小叔》【蘇撩 甜寵 教授 七歲年齡差 校園 救贖】【蘇撩腹黑小叔X古靈精怪少女】江落是十足的手控,為了一張手照,搭訕了一位帥哥,不料事後發現,對方居然是她閨蜜的小叔!江落腰板挺直,站姿乖巧:“小、小叔好。”……多年後,南大突然傳出生物學係的高嶺之花傅教授已經結婚的謠言。同事:“傅教授,這些謠言都是空穴來風,你別信……”“澄清一下,這不是謠言,”傅紀行冷靜補充,“我確實結婚了。”!!!江落跟傅紀行扯證時,她正讀大四。扯完證回去的路上,男人手裏拿著小本子,溫聲提醒:“喊了我這麼多年的小叔,是不是該換一下稱呼了?”“什、什麼稱呼?”“比如……”男人的吻落在她唇上——“老公。”
21.2萬字8 8278 -
連載284 章

可婚不可離
以前,薑沅隻是覺得陳妄隻是散漫,婚後才知道他是真的沒心。 她就是一個自作多情的笑話,心涼了,她果斷離婚,不做糾纏。 眾人都等著看陳妄迫不及待的娶青梅。 可等來等去,卻看到高貴冷豔的男人,去搶前妻的婚,“老婆,重婚犯法。”
50.8萬字8 931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