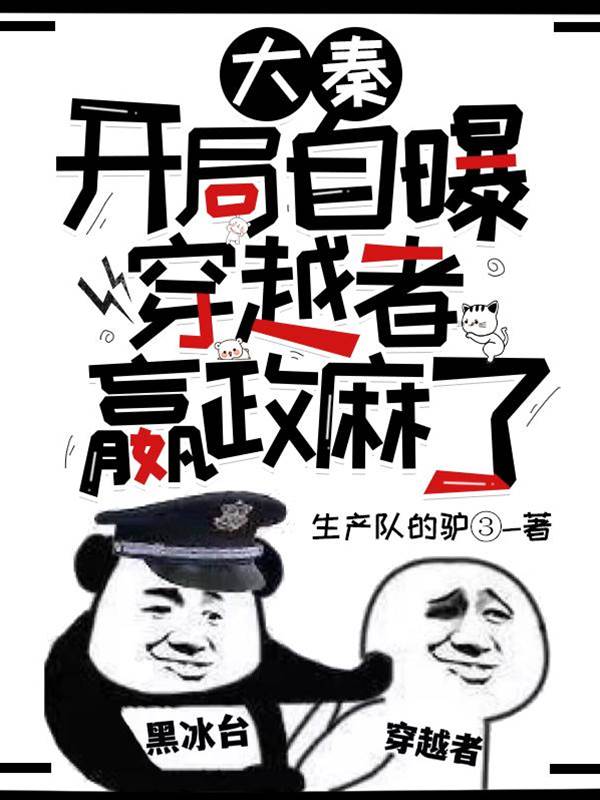《寒門狀元》 第二六七五章 如爾所願
沈溪留在宣府跟朱厚照相持不下。
最初朱厚照視而不見,到底沈溪不在他行宮門前賴着不走,他不用擔心隨時被沈亦兒教訓。
但隨着時間推移,朱厚照心中的不安逐步加深,生怕京城那邊出子。
“自古以來,皇帝不坐鎮京師必定會整出一些幺蛾子來,本來沈尚書可以在京城幫朕看着,絕對出不了事,但沈尚書就是要跟朕對着幹,不肯回去,若真有人惦記朕的皇位,朕該怎麼應對?”
朱厚照雖然貪玩好耍,但他很清楚自己的玩心是建立在朝政託付於可以信任的大臣手上,他明白爲皇帝沒有退路,大明皇室的鬥由來已久,篡位功的遠的有靖難之役,近的則是奪門之變,不的就是他登基後的安化王和寧王之,輸者不僅輸掉皇位,甚至還危及生命,在這件事上飽沈溪薰陶的朱厚照,有着非常深刻的認知。
當朱厚照說出這番話時,旁邊有聆聽者,便是前來給朱厚照奏事的張永,因皇帝之言類似於自言自語,彷彿帝王把心真實說出來,張永不敢主接茬。
但朱厚照並不介意張永聽到自己的心聲,側首問道:“張永你且說,朕該如何讓沈尚書回京師?有什麼好辦法?”
張永心想:“要有辦法的話何至於陷如此僵局?這司禮監掌印可真不好當,什麼破事都要詢問我的想法……我又不是沈尚書肚子裡的蛔蟲,怎麼知道如何才能勸他?”
心中腹誹不已,但張永哪裡敢表出來,想了想試探地道:“回陛下,京師事務不,六部跟閣配合無間,還有陛下英明指點,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大明江山穩若泰山,怎會有人威脅社稷穩定?”
Advertisement
朱厚照皺眉不已:“朕問的是如何讓沈尚書回心轉意,主返回京城做事,你跟朕說的什麼狗屁話?”
張永低下頭道:“老奴認爲……想要讓沈尚書回去……只需陛下您下一道聖旨便可。”
“切!”
朱厚照語氣中帶着幾分不屑,“如果發道聖旨就能把人打發回去,朕也不至於現在如此被……之前不也讓人去傳過話了嗎?”
張永湊上前,低聲道:“陛下您忘了,您是君而沈大人是臣,君要臣死臣都不得不死,何況是安排他去一個地方?陛下給出限期讓他必須走,他非走不可!”
朱厚照煩惱地道:“萬一他不走,還要跟朕說那些請辭的話,撂挑子不幹呢?”
“這個嘛……”
張永未料到朱厚照會刨問底,思索好一會兒後才爲難道,“若真如此,那說明沈大人心意已決,倒不如……全他。”
朱厚照怒不可遏:“好你個張永,朕算是看出來了,你不是給朕出主意,而是想挑唆朕跟朝中肱大臣的關係……你也知道沈尚書是朕什麼人,他既是朕的先生,皇后的兄長,又是國公、閣大學士、吏部尚書,你知道他對朝廷有多重要?有他在朝中,那些魑魅魍魎一概不敢出來造次,你讓他離朝,朕就了辟邪的門神,那些牛鬼蛇神都會來找朕的麻煩。”
張永道:“陛下,或許從某種角度而言,沈大人是門神,擋住小鬼,但若門神的槍口不對外,而對呢?”
本來朱厚照很氣惱,但在聽到張永的話後,突然愣住了,呆滯半天也沒回過神來。
張永卻覺自己把握到了朱厚照的脈搏,順着梯子往上爬,又補充道:“沈大人以前在朝的確兢兢業業,老奴幾次在他邊共事,佩服沈大人卓爾不羣、剛正不阿的態度,知道他爲國爲民,爲大明江山社稷,嘔心瀝,但人心總會變的。”
Advertisement
“變什麼?”
朱厚照斜眼問道。
張永回答:“陛下喜歡以史爲鑑,那老奴不妨請陛下回想一下,自古以來那些有權有勢的大臣,都是以如何方式收場的呢?”
朱厚照深吸一口氣,若有所思:“不得善終之人居多,那也是帝王的猜忌心太重,但這不代表君臣之誼不能善始善終,不是有很多正面案例?像劉備和諸葛亮,唐太宗和魏徵……”
張永提醒道:“陛下所說,乃是君強臣弱時,可別忘了史書上還有王莽篡位、安史之以及陳橋兵變的先例!老奴絕非挑唆陛下跟沈大人之間的關係,但請陛下想一下,這幾年沈大人是否因爲朝中肱,而對一些老臣,甚至對陛下指手畫腳?許多時候都拿一些事跟陛下要挾?”
朱厚照不說話,顯然心中已有見。
這是朱厚照自帶的防心使然,他對每一個進諫的大臣都天生帶着反,哪怕對沈溪又敬又怕,但約也會有一種憎惡,他自然不是完全沒想過沈溪會謀反之事,只是一次次在心把這種可能給否決了。
張永道:“陛下之前誤會老奴跟沈大人走得近,完全在於老奴之前做事,很多地方不得不仰仗他,老奴知道錯了,但由始至終老奴的忠心全在陛下這邊。請陛下明鑑。”
說着,張永跪地叩拜,等候朱厚照降罪。
朱厚照擺擺手:“講這些沒用,沈尚書這會兒又不結黨,還主還兵部尚書之職,不可能威脅大明江山社稷……你先想想怎麼把他打發走,回京城最好不過。”
張永道:“以老奴所知,沈大人想往江南籌備與佛郎機人的戰事,那老奴不妨做一種假設,若是沈尚書如願前去赴任,對陛下、對朝廷有何損失?陛下可以設地地想一想,其實很多事沈尚書在江南也可完。”
Advertisement
“嗯?”
朱厚照皺眉看向張永。
張永語氣變得緩和許多,再道:“沈尚書坐鎮南京,既滿足其願,他離開宣府也能讓陛下高枕無憂,朝中事務也不擔心沒人打理。”
朱厚照皺眉沉思,開始認真思考這個建議的可行。
但此前朱厚照考慮跟沈溪的關係,耗費太多心力,此時頭腦很混,半天不得要領,最後不耐煩地甩袖道:“此事先等等,實在不行,就讓沈尚書去江南……朕確實不想他留在宣府這邊,朕做什麼事都不自在,煩死了!”
……
……
因爲生平最敬畏之人在邊,朱厚照行事有了制約,這些天心煩意,神萎靡不振。
再加上張永不斷進言,讓朱厚照改變心意,最後下達了讓沈溪往南京“公幹”的聖旨,讓沈溪暫時離開宣府往南京,算是皇帝對大臣的妥協。
這次由張永前去傳旨。
當張永在驛館見到沈溪後把事說出來,眉飛舞,倒有邀功的意味……看看,要不是我,你還在跟陛下冷戰,現在你可以如願以償去江南,躲開京城的是是非非,君臣矛盾也可以解除。
沈溪神冷漠:“我的意思是前往新城履職,而不是南京。”
張永笑道:“二者有區別嗎,沈大人?您去南京或者新城,都是往江南,您既是監國,又是吏部尚書,還擔負籌備朝廷對外戰事的職責,您在南京,要往新城視察,還不是一句話的事?您甚至都不用跟陛下請示。”
沈溪打量張永一眼,似笑非笑地道:“張公公用心良苦啊。”
張永先是一愣,迅即意識到沈溪是在挖苦他。
因爲誰都能看出來,沈溪往江南,益最大的便是他這個剛上任的司禮監掌印太監。
Advertisement
張永既完皇帝的託把沈溪攆走,又讓沈溪遠離朝廷核心,讓司禮監的職權擴大,否則沈溪留在京城,司禮監掌印太監形同虛設,朝中所有事務近乎被沈溪壟斷,這不是張永希看到的況。
張永辯解:“鄙人乃是一片好意,沈大人若不領便罷。”
沈溪卻搖搖頭:“相反,我得好好謝張公公代爲斡旋。”
張永笑道:“那是當然,咱們畢竟是一條心,還有便是擰公公……最近他也很爲難,陛下爲了沈大人不奉詔而至宣府,以及遲遲不肯離開,焦頭爛額,對邊人多有苛責……您離開對誰都有好。”
沈溪苦笑道:“看來我的到來,讓很多人都很難做。”
“這……在下倒不是要指責沈大人……”張永強行辯解。
沈溪一擡手打斷張永的話,“張公公所做之事,本人銘記於心……張公公放心,我無論做何事都秉承規則,咱們間井水不犯河水,今日之事多謝了。”
“沈大人客氣。”
張永上說得漂亮,心裡卻在嘀咕:“你不走,我就算是相也要聽你的,而且還不得不聽,因爲陛下對你言聽計從,小事你理,大事也聽你的,那我做司禮監掌印還有何趣味可言?更何況張苑是你的人,這次你不知如何施展的手段,又把張苑給弄回朝來,莫非是想找機會替代我?”
張永顯然對沈溪有了諸多意見,當初靠結沈溪上位,現在如願,卻認定未必如皇帝所言是沈溪舉薦他的,下意識地爲排沈溪找理由。
這也是畏懼之下的自然反應,他很清楚只要沈溪想對付他,或者將他弄出司禮監,不過是舉手之勞。
沈溪起:“既然陛下聖旨已下,本即刻找人收拾行囊,可能要先回京師一趟,稍後便啓程。”
“沈大人要走?”
張永一時間沒反應過來,本來他還以爲沈溪不肯輕易就範。
沈溪道:“再不走,或許會爲別人的眼中釘中刺,本不想爲人所惡,便如某些人所願好了。”
沈溪屬於那種“知識趣”之人,當意識到跟皇帝離心離德後,他會選擇合理的方式避開京城場紛擾,躲到江南去,偏安一隅。
但他的舉很難得到朝們認同,他們自然覺得沈溪另有目的,跟沈溪有一定過節,或者對沈溪滿是猜疑和妒忌之人更會覺得他有“詭計謀”,紛紛猜測他採取的是“以退爲進”的戰略。
沈溪從宣府出發,快馬加鞭趕往京城。
朱厚照沒有給沈溪定期限,在他看來最好沈溪中途就改變主意,這樣他這個皇帝就不用考慮何時回京城了。
“陛下,該爲沈大人準備的,均已備好,但沈大人沒領,似是對陛下有些許意見,走的時候老奴想去送行,也沒給機會。”
張永終於把沈溪送走,覺得自己走了一步好棋,他怕回頭沈溪就讓他吃癟,不敢在皇帝跟前直接中傷,而是通過旁敲側擊來潛移默化。
朱厚照道:“他既先回京城,那事還有得商量,朝廷的事非要他置不可,那些老臣和勳臣都不是省油的燈啊。”
張永請示:“要不陛下就派老奴回京師,由老奴來幫沈大人打理朝事?”
朱厚照瞄了張永一眼:“朕需要你在邊做事,你回京作何?司禮監那邊不是有張苑麼?反正他沒到宣府,就讓他在京城打理朝政……”
“李公公也在京城。”張永一聽不妙,趕補充說明。如今他在皇帝邊這幫太監中最提防之人非小擰子,而是曾長期擔任他上司的張苑。
朱厚照卻打斷張永的話:“他理朝事比你有經驗,更不要說那個什麼李興……你先把閣轉來的上奏理好,朕不想每次都親自過問。”
……
……
沈溪回到京城,正門外樑儲和張苑帶人恭候。
作爲閣首輔,樑儲在前司禮監掌印張苑面前表現得很恭謹,接到沈溪的馬車後,一行人相繼上馬車或轎子,往京城而去,等大隊人馬離開,封鎖的城門才重新開放,給過往百姓造不小影響。
猜你喜歡
-
完結1694 章
娶個皇后不爭寵
爭寵?!爭爭爭…爭個屁!給娶進宮已經夠倒黴了,還要和上千的女人爭一個種馬男人?開玩笑,她雖然本性不是什麼貞節烈女,也是來自一夫一妻制的社會,未來絕對要一世一雙人滴,所以她明哲保身,在宮中混吃混喝,坐吃等——皇上下旨廢后出宮!至於皇上嘛?偶爾氣氣有益健康.
93.7萬字8 153673 -
完結593 章
王爺,王妃又去盜墓了
二十一世紀盜墓世家最優秀的傳人,穿越成被抄家的將軍府的三小姐。麵對被抄家一分錢都冇有窘境,三小姐說:要致富,先盜墓。咦?這個墳堆裡有個男人,有氣兒,活的,長的還不錯……咦?這家是誰?這祖墳埋的太好了,龍脈啊,必出天子,趕緊抱大腿……哇!這個墳墓裡好多金銀珠寶,還有絕世兵書,發財了發財了……
99.1萬字8 118957 -
完結96 章
合歡宗的女修絕不認輸
姬玉穿書了,穿成了個四處留情修煉風月道的女炮灰。她穿過來的時候,原主剛撩撥完男二冇幾天,就不甘寂寞地在秘境裡勾搭了男主宗門內不少弟子。 他們為她瘋為她狂,為她哐哐撞大牆,甘心獻上一切機緣法寶。 眼下,她剛給男主下完藥,正打算驗收成果。 很快她就會發現,男主根本冇中毒,他都是裝的,隻為順藤摸瓜找到她的洞府,尋回那些不爭氣同門的本命法寶,順便救下了向她尋仇反被綁的女主,來一場英雄救美的浪漫邂逅。 殼子裡換了人的姬玉看著麵前眼角泛紅旖麗脆弱演技卓越的男主,一言難儘道:“說出來你可能不信,我剛纔給你吃的不是合歡散,是七種毒蘑菇製成的獨門毒藥,你現在這個反應是不對的,你應該眼前飄著一堆小人,並跟著它們翩翩起舞纔對。” 說完,她豪邁地往後一靠,抬抬手道:“來吧,起舞,請開始你的表演。” 左右也是個死,還不如死前口嗨一下,反正她活著的每一秒,都要浪起。
45.1萬字8 8642 -
完結71 章

作精美人穿書了
系統告知,沈云棠穿成了爽文里事兒賊多的作精女配。 “你穿成了泡澡要用鮮牛奶,三天換一個廚師;虐待老公那寄居在家里、未來會成為大佬的弟弟;還時常找上商業大佬老公公司鬧事的,大!作!精! 最后被溫柔善良的小太陽女主對比打臉,人人厭恨,下場凄慘!” 沈云棠皺起漂亮的眉:“才不要。” 系統:“那麼聽我的話,從討好弟弟開始……” 沈云棠:“牛奶泡澡有腥味,我只用一克八萬的純手工精油。” 沈云棠:“我的廚師從十年前開始日日為了我的口味學習精進,菜系隨我的心情變化而變,不習慣外人。” 沈云棠:“什麼弟弟,住在我家就要守我的規矩,我睡美容覺不喜歡家里有一盞燈,他能八點上床睡覺嗎?不能就滾出去。” 沈云棠:“老公?誰要管一個臭男人的事?” 系統:……、、到底原主是作精還是她是作精??? 沈云棠冷著小臉醒來,看著床邊兩眼陰鷙的少年,懶聲道:“沒長手嗎?給我穿鞋。” 剛剛重生回來、上輩子被虐待得茍延殘喘,正準備報復的弟弟:“……?” 拒人千里之外的商業帝王老公回家,正冷聲要教訓這個無理取鬧的女人。 沈云棠:“抱我下去。我的鞋底值二十多萬,不能沾水。” 沈云棠:“沒吃飯嗎?這點力氣?” 身家千億的老公:“……?” 我他媽一身手工西裝就能沾水了? - 溫妍妍知道自己是一本書里的女主。 她只要一直溫柔善良、善解人意,就能讓被女配弄得心力交瘁的男主和他的大佬弟弟愛上自己。 他們甚至會為了得到她的愛而爭搶。 溫妍妍一直等著這一天,可為什麼她不但沒等到女配被離婚趕出豪門,劇情還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 沈云棠憑一己之力,早已把所有人作到了她的三觀里。 ——啊,順著沈云棠不是世界上最正常的事嗎? // 所有人為你俯首稱臣。 【女主最美,永不翻車】
30.9萬字8.18 7537 -
連載1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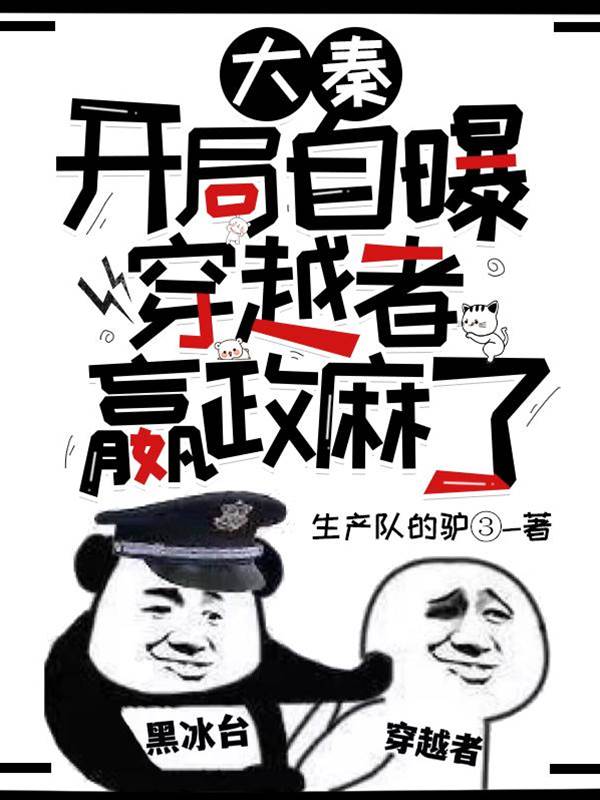
大秦:開局自曝穿越者,嬴政麻了
始皇帝三十二年。 千古一帝秦始皇第四次出巡,途经代郡左近。 闻听有豪强广聚钱粮,私铸刀兵,意图不轨,下令黑冰台派人彻查。 陈庆无奈之下,自曝穿越者身份,被刀剑架在脖子上押赴咸阳宫。 祖龙:寡人横扫六国,威加海内,尓安敢作乱犯上? 陈庆:陛下,我没想造反呀! 祖龙:那你积攒钱粮刀兵是为何? 陈庆:小民起码没想要造您的反。 祖龙:???你是说……不可能!就算没有寡人,还有扶苏! 陈庆:要是扶苏殿下没当皇帝呢? 祖龙:无论谁当这一国之君,大秦内有贤臣,外有良将,江山自然稳如泰山! 陈庆:要是您的贤臣和内侍勾结皇子造反呢? 祖龙:……谁干的?!我不管,只要是寡人的子孙在位,天下始终是大秦的! 陈庆:陛下,您的好大儿三年就把天下丢了。 祖龙:你你你……! 嬴政整个人都麻了!
247.2萬字8 983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