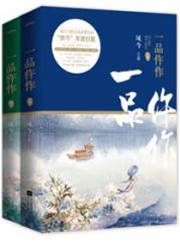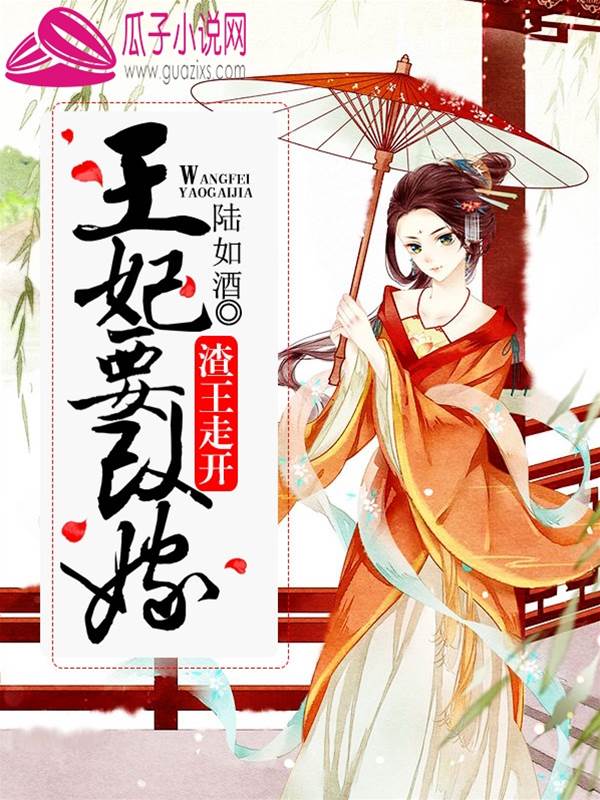《盲妾如她》 第25章 第 25 章[四合一]
俞姝仍跟著和尚走著,忽覺一陣風同山風全然不同,徑直卷了過來。
男人悉的氣息將包圍,“怎麼又跑?有沒有傷?!”
俞姝怔住了。
“五爺?”
以為只是傳了令,沒想到人也來了?
俞姝昨日還特特問了他的行程,看來都是白問了。
他并沒跟說實話。
也是... ...
俞姝默然垂了眼眸,從他邊退開半步,人山風從兩人中間呼嘯而過。
這般,五爺抬起要護在邊的手,頓在了半空,
上干干凈凈沒有灰塵,手里還拿著幾株草藥,神淡漠地仿佛這危機四伏的后山沒有危險,而他才是讓避閃的存在。
男人手下微攥,收了回去。
他沉聲問,“為何又跑?誰帶你下來的?你有沒有想過,若是走失了,遇到賊人了怎麼辦?”
他那麼多問題,俞姝沒有回答。
只是道,“婢妾沒事。”
五爺從京城一路奔來,一聽不妥就來尋找。
懸著一顆心找了半晌,終于找到了人,卻只得了這般敷衍的四個字。
烈烈山風吹在詹五爺心頭。
他抿了抿,盯著看了幾眼,沒有言語,只同一旁的和尚道了句“師父辛苦了”,自己轉了,讓姜扶了俞姝回去。
山風凜冽了一時。
只是他們剛走了沒多遠,便有侍衛來報。
“何事?”
“國公爺,發現了那伙人的行蹤,穆將軍已領兵去追了!”
俞姝心下了一。
默默攥了帕子,聽見那五爺沉聲吩咐。
“告訴穆行州,盡量活捉。屆時嚴刑審問!”
*
衛澤言也看出來追上前來的人,想要活捉他們的想法。
他抓住朝廷兵這等想法,鋌而走險抄險路而過。
Advertisement
若是穆行州讓人了□□或者火/槍,他們必然要亡。
但穆行州領了要活捉的命,□□火/槍在手邊猶豫,只幾息的工夫,到底讓衛澤言逃了。
衛澤言帶人很快就沒林中,逃出生天。
衛澤言聽到穆行州氣惱地勒馬的聲音,長舒一氣。
不過他們一行也完全不敢放松。
他看了一眼遠凝夜空中的星一般的京城,頭也不回地奔著虞城而去。
襄王要打虞城,定國公還要來一招螳螂捕蟬黃雀在后,虞城危矣!
只是他不由想到了今日見到俞姝的形。
姑娘的頭發挽了起來,雖然穿著華服,確實婦人打扮?
衛澤言眼皮跳了一下。
知道定國公的行,而定國公前些日納了妾。
韓姨娘麼... ...
衛澤言一時無法證實什麼,他只能一鞭子到了馬上。
“加速返回虞城!”
萬萬要趕在襄王和詹司柏手前,讓俞厲得到這個要消息。
*
靈螺寺后山。
詹五爺走在前,他的妾走在后,他不開口,亦不出一聲。
沒過多久,就到了詹淑慧落進的深坑里。
五爺看見詹淑慧的眼神,掩飾不住地對他的妾打量,而他看過去,詹淑慧又急忙錯開了目。
他沒有破任何人,只是在回到禪房的時候,獨獨了俞姝過去。
他覺得自己也不該過于意氣用事,他的妾也只是與淑慧相仿的年紀罷了。
“方才發生了什麼事?”他和緩了口氣,問。
俞姝沒想到這位五爺還真的要刨問底。
但肯定不能如實把自己的事都說出來,但若是只說到詹淑慧和魏連凱夫婦這一層,也就把魏連凱夫婦的事直截了當地說出去了。
那倒也與無關,但是,方才沈氏聽見了和衛澤言的傳話聲。
Advertisement
一旦五爺尋了沈氏說話,不定沈氏就會說出來。
而且剛才,詹淑慧明顯也沒有多言。
既然如此... ...
俞姝道,“慧姑娘要尋靈泉,結果落深坑,婢妾跟了采草藥的師父,去給慧姑娘采止藥來。”
半句沒提魏連凱和沈氏。
俞姝這麼說了,并不能看到那五爺的神。
但詹五爺看著自己的妾,臉上徹底沉了下去。
沒說實話。
明明詹淑慧眼神躲閃很有問題,明明需要止草藥,讓和尚一個人去就可以了。
可一個字都不肯跟他多說。
詹司柏說不出自己此時此刻是怎樣的滋味。
他只是看著他的妾,親手壘砌一道山海的屏障,橫在與他之間。
禪房里氣氛底下,只有檀香氣息游走。
詹五爺也一句話都不再多問,最后看了一眼俞姝,抬腳出了禪房。
俞姝不知他這是什麼態度,向他的方向“看”過去,但他已出了門。
穆行州剛好回來了,聲音滿是頹喪。
“五爺,屬下追擊不利,被那伙人逃了。”
詹司柏聽了沉默下來,禪房里的俞姝,卻一口氣呼了出來。
但穆行州又道了兩句。
“屬下辦事不利,請五爺責罰。但這伙人確實是從靈螺寺后山逃遁的,咱們封山急,他們竟然也能及時逃遁,屬下懷疑... ...有應!”
俞姝聽見這話,剛松了半口的氣,又摒了回來。
似乎到了那位五爺在遲疑之后,轉頭看過來的目。
俞姝垂著頭站著,半分沒。
五爺也不知怎麼回事,竟然在穆行州說“有應”的一剎那,想到了自己的妾。
難道他寧愿懷疑妾是應,都不肯相信其實只是跟自己疏離冷淡嗎?
Advertisement
他說不清自己是什麼覺,沉著臉同穆行州一道,去見巡查搜山的兵。
男人走了,悉的腳步遠去,很快消失在了俞姝的耳中。
扶了窗沿,慢慢坐了下來。
... ...
方才那點怪異的想法,早被詹司柏了下去。
一個盲,能做什麼應呢?
只不過封山搜人的兵,也都沒有什麼異常。
但有個兵上前報了一樁事。
“國公爺,我們在后山攔住了兩個倉皇下山的人。”
兵說著猶豫了一下,看了看威嚴的定國公,有在國公爺的目下,道。
“那二人乃是京城商戶魏連凱和其妻沈氏。”
詹司柏挑眉。
男人突然想到了什麼,不住回頭俞姝所在的禪房方向看了過去,眉頭鎖了起來,
就在這時,寺廟里忽然一。
“五爺!夫人癥犯了!”
俞姝也在倉皇的喊聲里,從禪房索了出來。
“夫人犯了癥?”
姜說宴夫人確實有癥,是以輕易不出門,“但靈螺寺里沒有太醫啊!這可怎麼辦?!”
話音一落,俞姝就聽到了那五爺而沉的命令聲。
“立刻去京城請太醫!我與夫人沿路迎過去!凡有誤事者,當即杖斃!”
三聲令下,寺院里凌的腳步聲陡然變得有了目的,而那五爺的腳步聲也變了一變。
他先是急急奔了過去,而后腳步聲一重,又向山下奔去,幾乎一院子人的腳步,追著他往山下去。
他是抱了宴夫人下山了嗎?
俞姝循聲“看”過去,匆忙之間,約察覺有目掃過來。
聽到了他對的冷聲吩咐。
“你自行下山吧。”
話音落地,腳步聲隨消失。
寺院里一下冷清起來。
Advertisement
鄭氏因為詹淑慧落進坑里崴了腳,和住持商量在此住上一晚。
而俞姝卻不得停留。
天已經不早了,昏暗的視野更加暗下來。
聞聲過來的詹淑慧嘖了一聲,“五爺抱著夫人回去了,韓姐姐要自己回去了呢!”
在宴夫人面前,一個妾算什麼呢?
倒是鄭氏好心問了一句,“姨娘怎麼回去?”
靈螺寺地方有限,國公府上山沒有大張旗鼓,來時僅有的一輛上了山的馬車,已經送宴夫人回京了。
如果還留下馬車的話,那麼只在山下。
俞姝謝過鄭氏關心,“我走下去好了。”
山路陡峭,寒風凜冽。
俞姝瞧不見下山的臺階,每一步都走的艱難。
姜小心扶著俞姝,主仆二人用了近一個時辰,才到了山下。
幸好還有馬車等候。
*
定國公府,正院一派忙碌,老夫人親自過來看宴夫人,守在宴夫人床前一步不離。
詹司柏被榮管事從幾個太醫中請了過來。
榮管事回了話,“五爺讓老奴去查魏家的事,已經有眉目了。”
他說魏連凱夫妻為了這個兒子傷了不神。
“魏北海確實是與人斗毆,而且是當先出手打人的。人家也不是善茬,使了銀子讓衙門關著他不放。”
榮管事說著,瞧了五爺一眼,“衙門的人您也知道,免不了捧高踩低,知道您與魏家不和,便也故意出難。”
他說到此一頓,輕聲問了一句。
“五爺,要不要老奴跟衙門說一聲,把人放了。”
無非就是放不放人的事,又不是什麼大事。榮管事是這樣想的。
可他瞧著五爺臉不大對勁。
半晌,那五爺開了口,“此事不必管。”
榮管事一愣。
不用管的意思,就是任著衙門繼續扣人了?
他有些鬧不清五爺的心思了,但這是文澤過來稟了一聲。
“五爺,姨娘回來了。”
話音落地,那五爺就吩咐了下去,“請姨娘過來。”
俞姝被到了正院,自然也聽到了太醫們的急診治。
倒是想去探問一番,卻被那五爺徑直去了西廂房。
庭院里腳步雜,西廂房靜悄悄的,指點了一盞孤燈在高案上。
詹司柏瞧瞧自的妾,見上還滿是從外面帶進來的寒氣,蒙眼的帶落了下來,被纏在了手腕上。
詹司柏看著俞姝,想想自己之前對兩次三番的誤會,他覺得這一次,總要再給說清楚的機會。
他不由地問了。
“今日是不是見了什麼人?你說吧,我不怪你。”
要是實話實說了,他也就真不怪了。
畢竟魏家況復雜,不知怎麼應對也是有的。
可他那話落進俞姝耳中,卻令俞姝怔了怔。
今日著實見了不人,比如,衛澤言。
在他先行回府,而快到天黑才趕到的時間差里,他是不是已經見過沈氏,甚至問出了什麼呢?
俞姝心下提了起來,不知他到底是何想法,抿著沒有回應。
但的態度落在詹司柏眼中,讓男人眉頭瞬間了下來。
還是不肯說嗎?
他訝然看著,“你沒想好怎麼說嗎?”
俞姝在他含義不明的話語里,仍舊沉默。
這一次,男人也沉默了。
見了魏家人,卻一分都不肯給他,來來回回他問了好些遍,始終保持緘默。
對他就這麼戒備?
相反,才見了魏連凱夫妻一回,就想維護他們?
他不由語氣沉了幾分。
“看來... ...你要替魏家在我面前求了,是嗎?”
俞姝在這問話里,終于明白了他指的到底是哪件事。
提著的心一松,慶幸自己方才沒有多言。
不過眼下也不好多說什麼了,就順著他的話。
“看來五爺都知道了。”
誰想這話一出,那五爺突然哼笑了一聲。
“若我不派人去查,你也是不肯說得,不是嗎?”
俞姝一愣,沒明白他這麼問是什麼意思。
但這整個西廂房,氣氛卻陡然一變。
俞姝盲著一雙眼,什麼都看不到,只是聽到坐在上首的五爺,忍不住笑了一聲。
這一聲里,是俞姝聽不懂的緒。
他說,“魏連凱一家是什麼樣的人,你全然不知,卻就想去維護包庇他們。”
男人說道此頓了一下,那讓人聽不懂的緒更重了幾分。
俞姝聽到他沉沉的聲音,“可你夫君與你朝夕相,你全然不信,只一味地提防質疑... ...可真是好!”
這話如浪一般劈頭蓋臉席卷過來,俞姝懵了懵。
猜你喜歡
-
完結239 章
休夫
挺著六月的身孕盼來回家的丈夫,卻沒想到,丈夫竟然帶著野女人以及野女人肚子裡的野種一起回來了!「這是海棠,我想收她為妾,給她一個名分。」顧靖風手牽著野女人海棠,對著挺著大肚的沈輕舞淺聲開口。話音一落,吃了沈輕舞兩個巴掌,以及一頓的怒罵的顧靖風大怒,厲聲道「沈輕舞,你別太過分,當真以為我不敢休了你。」「好啊,現在就寫休書,我讓大夫開落胎葯。現在不是你要休妻,而是我沈輕舞,要休夫!」
65.8萬字8 77347 -
完結4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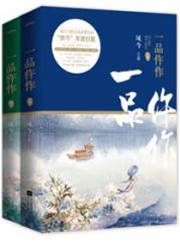
一品仵作
這是一個法醫學家兼微表情心理學家,在為父報仇、尋找真兇的道路上,最後找到了真愛的故事。聽起來有點簡單,但其實有點曲折。好吧,還是看正經簡介吧開棺驗屍、查內情、慰亡靈、讓死人開口說話——這是仵作該乾的事。暮青乾了。西北從軍、救主帥、殺敵首、翻朝堂、覆盛京、傾權謀——這不是仵作該乾的事。暮青也乾了。但是,她覺得,這些都不是她想乾的。她這輩子最想乾的事,是剖活人。剖一剖世間欺她負她的小人。剖一剖嘴皮子一張就想翻覆公理的貴人大佬。剖一剖禦座之上的千麵帝君,步惜歡。可是,她剖得了死人,剖得了活人,剖得了這鐵血王朝,卻如何剖解此生真情?待山河裂,烽煙起,她一襲烈衣捲入千軍萬馬,“我求一生完整的感情,不欺,不棄。欺我者,我永棄!”風雷動,四海驚,天下傾,屬於她一生的傳奇,此刻,開啟——【懸疑版簡介】大興元隆年間,帝君昏聵,五胡犯邊。暮青南下汴河,尋殺父元兇,選行宮男妃,刺大興帝君!男妃行事成迷,帝君身手奇詭,殺父元兇究竟何人?行軍途中內奸暗藏,大漠地宮機關深詭,議和使節半路身亡,盛京驚現真假勒丹王……是誰以天下為局譜一手亂世的棋,是誰以刀刃為弦奏一首盛世的曲?自邊關至盛京,自民間至朝堂,且看一出撲朔迷離的大戲,且聽一曲女仵作的盛世傳奇。
203萬字8 29155 -
完結977 章

嫡女醫妃權傾天下
她是簪纓世家的嫡長女,生而尊貴,國色天香,姿容絕世; 上一世,她傾盡所有,助他奪得天下,卻換來滿門抄斬; 上一世,害她的人登臨鳳位,母儀天下,榮寵富貴,而她被囚冷宮,受盡凌辱; 重生于幼學之年,她再也不是任人擺布的棋子,一身醫術冠絕天下,一顆玲瓏心運籌帷幄,謀算江山; 這一世,她要守護至親,有仇報仇,有怨報怨; 這一世,她要讓那個縱馬輕歌的少年,無論刀光劍影,都長壽平安!
177.9萬字8 62454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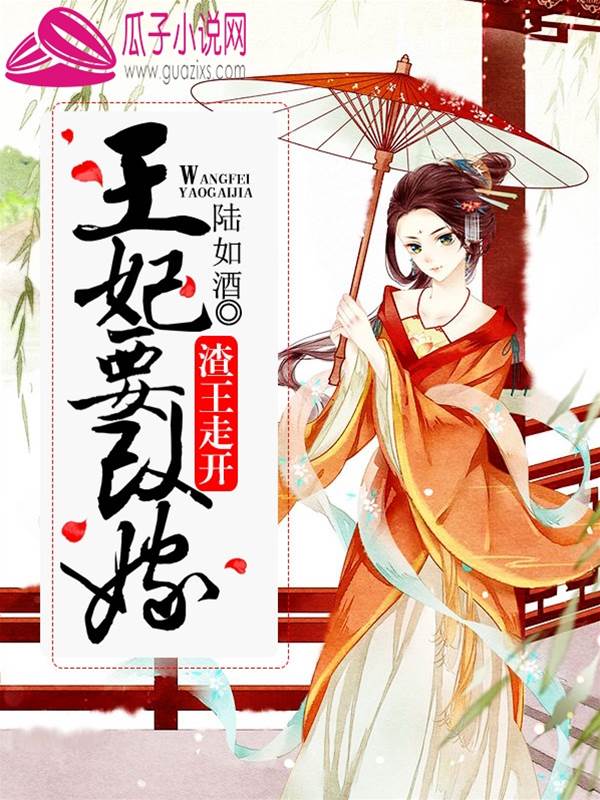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3499 -
完結86 章

東宮嬌藏
裴幼宜是齊國公獨女,憑著一副好樣貌和家中的背景,在汴京城中橫行霸道。京城的貴女,個個視都她為眼中釘肉中刺。直到這天,齊國公犯錯下了獄,裴幼宜也跟著受了牽連,正當她等候發落之際,宮中傳出消息,她成了給太子擋災之人。擋災這事說來滑稽,加上國公爺被冷落,連帶著她在宮裏的日子也也不好過同住東宮的太子趙恂惜字如金,性格冷漠,實在是個不好相處的人。好在二大王趙恒脾氣秉性與她相當,二人很快就打成一片。衆人皆以為,裴幼宜以如此身份進了東宮,日子應該不會好過。結果裴幼宜大鬧宮中學堂,氣焰比起之前更加囂張。衆人又以為,她這樣鬧下去,過不了多久就會被太子厭煩,誰知……裴幼宜每每掀起風波,都是太子親自出手平息事端。擋著擋著,太子成了皇上,裴幼宜搖身一變成了皇後。-------------------------------------趙恂從宗學領回裴幼宜,今日犯的錯,是與慶國公府的**扭打在一起。裴幼宜眼圈通紅,哭的三分真七分假,眼淚順著腮邊滑落,伸出小手,手背上面有一道輕不可見的紅痕。太子皺眉看了一陣,次日便親臨慶國公府。第二日慶國公**頂著衆人錯愕的目光給裴幼宜道歉,裴幼宜不知她為何突然轉了性子,以為是自己打服了她,于是揚起小臉眼中滿是驕傲。遠處趙恂看見此情景,無奈的搖了搖頭,但眼裏卻滿是寵溺。閱前提示:1.雙C,1V1,微養成2.架空仿宋,務考究。4.年齡差5歲。5.尊重每一位讀者的喜好,不愛也別傷害。內容標簽: 勵志人生 甜文搜索關鍵字:主角:趙恂,裴幼宜 ┃ 配角:很多人 ┃ 其它:
27.9萬字8 19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