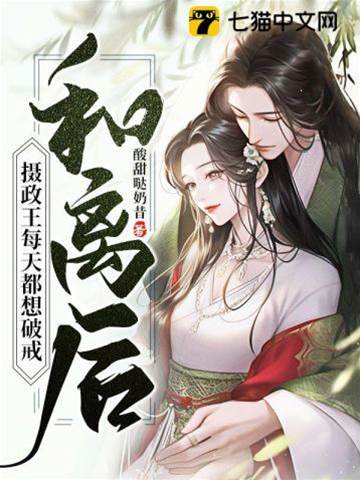《毒妃重生:盛寵太子爺》 第50章 恩師
「府上五小姐沒有來麼?」許錦言將宋婉婉向上抱了抱,笑著向王氏問道。王氏還沒有說話,許錦言懷裡的宋婉婉卻扳著指頭道:「大姑姑二姑姑三姑姑四姑姑都來了,只有姑姑沒來。」
許錦言一怔,其他國公府的小姐都是按照一二三四排列的姑姑,只有宋雲闕是姑姑。
看著懷中宋婉婉的目便是一,誰說小孩子不懂事,小孩子的心裡有時候比大人還通曉,們知道誰待好,誰待不好,誰是真實意,誰又是虛假意。
這樣看來,宋婉婉還真是像的兒佩玉。那時佩玉不過四五歲,許茗玉一天到晚的變著法兒討好佩玉,又是做服又是給零。
但佩玉還是一副不喜歡許茗玉的樣子,饒是許茗玉使出渾技倆,佩玉還是一直都對親近不起來。因著佩玉對許茗玉的這般表現,許茗玉心裡也極度不悅,還私下老和抱怨,說佩玉待人冷漠。
可許茗玉怎麼會知道,佩玉是這世上最可的孩子,雖然出王家,但一點貴族小姐的傲氣都沒有,對待下人善良有禮,從不髮脾氣。
這樣的孩子若是能對一個人這樣冷漠,那隻能說明,這個人本就是心懷叵測。
四五歲的佩玉能看明白的事,而卻怎麼也看不明白。連累佩玉付出了花朵一般的生命,才大徹大悟,但這一輩子,卻再也沒有補償佩玉的機會。
許錦言下翻湧的心思,笑著對懷中的宋婉婉道;「是因為姑姑病了麼?」
「雲闕向來子不好,這些宴會從來都是不參加的。若是許小姐想見雲闕,過幾日可來府一敘。」王氏了宋婉婉的臉蛋,輕嘆道。
Advertisement
王氏雖嫁進英國公府有些年頭,但王氏年紀並不大,如今雖然是五歲孩子的母親,年齡也不過才二十齣頭。大不了府上的這些小姐幾歲。
但若說府上那位小姐和王氏脾氣相投,能說上幾句真心話,那也就只有子素來不好的五小姐宋雲闕了。雖然五小姐平日里總是一副冷冰冰的樣子,不善言辭,自己的丈夫宋宏也素來不喜歡這個最小的妹妹。但是王氏和宋婉婉卻都一致的很喜歡五小姐,只可惜雖然宋雲闕天資聰穎,才學遠遠高出府上的其他小姐,但子太弱又從小患病,這樣的宴會也只能呆在家中靜養。
許錦言點了點頭,沒有再繼續往下問。雖然很想問問宋雲闕到底是什麼病,但是心裡清楚宋雲闕的病其中必有,也就止住了說下去的話。
前世的雲雀雖然在軍營里盡折磨,之後被許恪搭救,勉強活了下來。但許錦言印象中的雲雀子並沒有這麼脆弱。若是前世的雲雀早就得了重病,本不過軍營里那種非人的待。
而今生那日在英國公府所見的宋雲闕,雖然面蒼白,但同說話的時候頗有氣力,微通黃老之,所以一眼便看出宋雲闕絕非久病之人。
但王氏口中的宋雲闕可是子弱的不得了,人多的地方都不能來。
無論是前世還是今生,這與所見的宋雲闕都大相徑庭。
唯一的可能是宋雲闕是在裝病,可宋雲闕貴為英國公府嫡出的五小姐,又何必做出裝病這種事呢?
正細細思索著,懷中的宋婉婉卻激的大聲道:「三伯伯!」
Advertisement
三伯伯?許錦言聞聲看去。
只見一群世家公子自男席緩緩場,前面領銜的是一臉嚴肅的王嚴崇王閣老。
看來是清塵書院的學子們到場了。
許錦言抱著宋婉婉的手一,接著臉上就浮現出安的笑意。看著王嚴崇王閣老緩緩而行,一臉嚴肅的模樣。笑意愈深,連淚花都快笑出來了。
是王嚴崇王閣老,前世因而死,恩大於天的老師。「許姐姐,你笑什麼呀?」宋婉婉看著許錦言的笑容不解的道。
許錦言看著王嚴崇的背影笑:「你不覺得前面走的那個老爺爺看起來很慈祥麼?」
宋婉婉和王氏一起睜大了眼睛,妄圖從王嚴崇上找到一一毫和慈祥這個詞語能聯繫起來的氣質。
王氏看著王嚴崇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冷模樣,打了個,乾的笑道:「許小姐,你說的不會是王閣老吧?」
王閣老,嗯?慈祥?
王氏倒吸了一口冷氣,這話若是被清塵書院的學子聽見,恐怕要全書院笑掉一的牙。誰不知道王嚴崇是出了名的嚴厲冷酷,只要是清塵書院出的學子,一聽見王嚴崇三個字就嚇得魂不附,有的出了書院好幾年,在街上看見王嚴崇都要繞著走。
府上的三爺今年就在清塵書院就讀,回回書院放假歸來,都要在婆母的面前哭訴上好幾個時辰,痛斥王嚴崇心狠手辣。
這樣的人?慈祥?
王氏很想手許錦言的額頭,看有沒有在發燒。
許錦言看著王嚴崇嚴肅的面孔,角勾起,臉上是發自心的笑意。
Advertisement
老師還是和前世一樣,總是一厚重的黑服,面孔板的平平整整,一點笑模樣沒有。沉嚴肅的模樣能嚇到一群小孩子。
可其實老師只是人前才擺出這樣一副嚴肅的模樣,背後卻對好的不得了。
老師剛開始授業於,那時還是個不學無的許家蠢貨,聽著老師的課十分費勁,上課的時候也老是心不在焉。後來有一次老師讓背《兵法》,背了幾個字就實在背不下去了,老師氣的痛罵一頓,雖言語激烈,但手上三指寬的戒尺只狠狠的擊在面前的桌子,毫都沒有到。
而卻依然被嚇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會哇哇大哭。老師看一哭,也了驚嚇,手足無措的過來安。看著老師安人還嚴肅的臉卻哭的更為大聲,最後老師沒了法子,居然畫了大花臉扮作老虎來逗笑。
看著原本嚴肅至極的老師卻「嗷嗚嗷嗚」的擺出那樣一副稽的模樣,這才破涕為笑。
是一直知道的,以嚴厲冷酷著稱的王嚴崇王閣老只是看著嚴肅,但真的是很慈祥很慈祥的人。許恪還沒席,就不斷的向席張,一黛披風的許錦言抱著紅蝴蝶宋婉婉本就無比顯眼,許恪隨便一看,許錦言便映了他的眼簾。
許恪記得那件披風,那是母親最喜歡的服,母親穿那件披風的時候英氣而沉靜,但如今被妹妹穿來,披風卻更顯的華貴溫婉。
上一次在清塵書院門口許錦言突然對自己的態度轉了個彎,許恪雖然驚喜不已,可也怕許錦言的態度會再次變化,所以這一次一來,他便小心翼翼的看向了許錦言。
但他的眼眸剛落在許錦言的上,就發現許錦言也正在看他,還彎向他笑了笑,隨後像是還說了什麼,許恪瞇眼,仔細的分辨許錦言的口型。許錦言說了兩個字。
哥哥。
哥哥……許恪心裡一熱,落了座。
猜你喜歡
-
連載3698 章

九公主又美又颯
眾臣:世子爺,你怎麼抱著世子妃來上朝?世子咬牙切齒:娘子隻有一個,丟了你賠?她是戰部最美年輕指揮官,前世被渣男背叛,慘死斷情崖底。重活一世,開啟瘋狂稱霸模式。一不小心,還成了世子爺捧在掌心的寶。太監總管:皇上不好了,世子府的人打了您的妃子!皇上躲在龍椅下瑟瑟發抖:無妨,他們家世子妃朕惹不起!
325萬字8.46 896878 -
完結1308 章

厲王的替嫁王妃(沈朝陽蕭君澤)
因身份低微,她被迫替嫁廢太子。那人心中只有白月光,厭惡她欺辱她,卻不肯放過她。她委曲求全,與對方達成協議,助他權謀稱帝,助他穩固朝政外邦,以此換取自由身。可誰知,他一朝登基稱帝,卻再也不肯放過她。“你說過,得到這天下就會放過我。”“朝兒……你和天下朕都要。”可如若這江山和美人只能擇其一,他又會如何抉擇?愛江山還是要美人?
238.3萬字8 158648 -
完結5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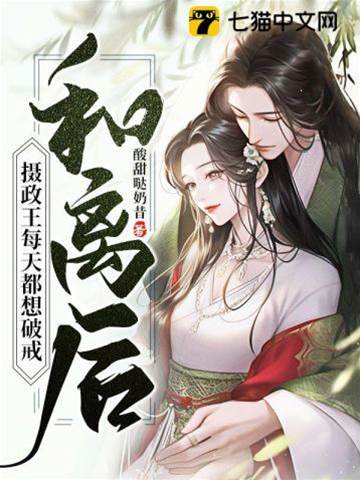
和離後攝政王每天都想破戒
葉芳一朝穿越,竟然穿成了一個醜得不能再醜的小可憐?無才,無貌,無權,無勢。新婚之夜,更是被夫君聯合郡主逼著喝下絕子藥,自降為妾?笑話,她葉芳菲是什麼都沒有,可是偏偏有錢,你能奈我如何?渣男貪圖她嫁妝,不肯和離,那她不介意讓渣男身敗名裂!郡主仗著身份欺辱她,高高在上,那她就把她拉下神壇!眾人恥笑她麵容醜陋,然而等她再次露麵的時候,眾人皆驚!開醫館,揚美名,葉芳菲活的風生水起,隻是再回頭的時候,身邊竟然不知道何時多了一個拉著她手非要娶她的攝政王。
99.6萬字8 9486 -
完結232 章

陛下輕點罰,宮女她說懷了你的崽
為了活命,我爬上龍床。皇上不喜,但念在肌膚之親,勉強保了我一條性命。他每回瞧我,都是冷冷淡淡,嘲弄地斥一聲“蠢死了。”我垂頭不語,謹記自己的身份,從不僭越。堂堂九五至尊,又怎會在意低賤的宮婢呢?
43.7萬字8.18 6651 -
完結242 章

教不乖,佞臣替人養妹被逼瘋
【傳統古言 廢殺帝王權極一時假太監 寄人籬下小可憐 倆人八百個心眼子】少年將軍是廝殺在外的狼,窩裏藏著隻白白軟軟的小兔妹妹,引人垂涎。將軍一朝戰死沙場,輕躁薄行的權貴們掀了兔子窩,不等嚐一口,半路被內廠總督謝龕劫了人。謝龕其人,陰鬱嗜殺,誰在他跟前都要沐浴一番他看狗一樣的眼神。小兔落入他的口,這輩子算是完……完……嗯?等等,這兔子怎麽越養越圓潤了?反倒是權貴們的小團體漸漸死的死,瘋的瘋,當初圍獵小兔的鬣狗,如今成了被捕獵的對象。祁桑伏枕而臥,摸了摸尚未顯孕的小腹。為了給兄長複仇,她忍辱負重,被謝龕這狗太監占盡了便宜,如今事得圓滿,是時候給他甩掉了。跑路一半,被謝龕騎馬不緊不慢地追上,如鬼如魅如毒蛇,纏著、絞著。“跑。”他說:“本督看著你跑,日落之前跑不過這座山頭,本督打斷你的腿!”
42.7萬字8.18 1579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