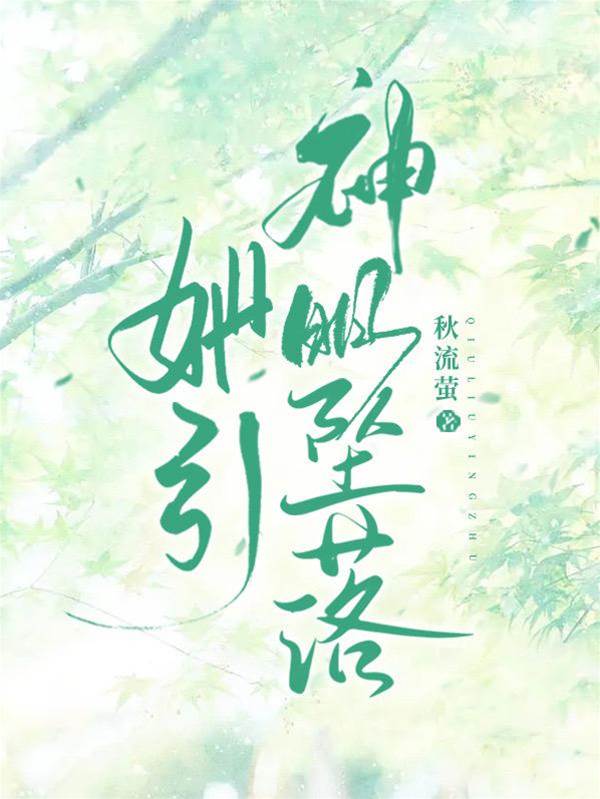《荒野植被》 29
“不會人你不能學?你是廢?”許言譏諷道,“別找理由了,不就是不,我沒見過這種讓人心寒的。”
他其實已經要站不穩,如果手邊能到什麼東西,他必定就砸過去了,可許言仍強撐著,冷聲說:“滾,我不想再見到你。”
真要命,里有什麼在飛速瓦解,一廂沉浸的,竭力自愈的傷口,孤注一擲的恐懼,自欺欺人的安……許言已經能夠坦然接沈植不自己,接種種意難平,可他無法面對這種事實——里說著他的人,竟然那樣殘酷地將他的一腔意踩在腳底,整整四年。
這算是什麼狗屁的,如果這就是沈植能給他的所有,如果許言早知道……他一定一定,不會在沈植說要試試的時候,回答‘好’。
“許言。”沈植還記得不久前許言眼里掉下的淚,混糅著臉上不合時宜的笑,復雜得刺目——許言第一次在他面前哭。沈植啞著嗓子說,“是我的錯,對不起。”他不知道此刻除了道歉還能做什麼,他只明白,遲來的告白是利刃,除了傷人,一無是。
客廳里一片寂靜,許言急促的呼吸聲逐漸變為不能遏制的嗚咽,他坐在沙發上,手肘撐著膝蓋,眼睛埋在掌心里,說:“沈植,你真狠的。”
“我拜托你,就當我以前在犯賤,今天是最后一次,你放過我,行嗎?”
沈植到一難以言喻的恐慌自心頭升起,他朝許言走過去,許言卻突然抬起頭,眼里和臉上的淚水在昏暗中著模糊的微,他說:“我已經被你弄這樣了,別過來,別讓我恨你。”
他那點命懸一線的自尊,到底還是在今天破了防,唯一能做的就是借黑暗藏自己的丑態,如果沈植非要拆穿,許言真的會恨死他。
Advertisement
“走吧,沈植。”許言哽咽著說。
沈植的嚨里干像沙漠,幾乎發不出任何聲音,他緩緩轉往門口走,從影走向亮地帶,然后關上門,留給許言完整的、可供躲避與獨自發泄的安全空間。
他至此才真正明白自己錯在哪里——不是不會人,而是在不會人的同時冷地傷人。許言那麼他,滿腔沛滾燙的意恨不得全都奉獻,可他卻往一顆炙熱的心上連續不斷地澆了四年多的冰水,眼看它僵、失,最后滿是傷痕地被許言收回去,小心翼翼地想要再次捂熱,祈求它放棄妄想,以后只為自己跳。
他今天的告白,擊潰了許言那條撐的防線。他確實沒資格說他,許言在這段里飽寂寞、失、孤獨、打擊,傾其所有卻得不到回應,而自己是罪魁禍首——冷漠自我,偏執盲目,別扭擰,作繭自縛。他對許言虧欠無數,哪配說,只說又怎麼夠。
隔著一道門,沈植聽見許言極度忍痛苦的哭聲,沒過幾秒,門里傳來一聲重響,玻璃水杯砸到門上,又破碎落一地,仿佛將沈植那些繃著的神經也砸斷。碎片在口炸裂,迸五臟六腑,里翻滾著玻璃刺,痛得他垂下頭弓起后背,整個人都想蜷起來。
作者有話說:
再晚走兩秒,那個玻璃杯就砸你頭上噢。
第28章
許言早上洗完臉之后對著鏡子照,眼睛只是有點腫,狀態還行——年人總是必備自愈能力。簡單收拾完,許言打開門,今天是本年最后一天上班,后天就是除夕了。
關門,許言略過面前站著的人,朝電梯走。沈植還穿著和昨晚一模一樣的服,手里拎著一碗打包好的熱餛飩,他開口許言的名字,然而嗓子太啞,‘許’字出口時幾乎聽不見聲,喑啞如氣音。
Advertisement
許言很快邁到電梯前,按鍵,靜等電梯上來。沈植走到他旁,把餛飩遞過去,低聲說:“我送你去公司,你在車上吃。”
沒回應,許言無于衷,電梯門打開,他走進去,雙手兜,懨懨地靠在角落里,沈植站在他邊,垂著眼沉默。電梯降到車庫,許言掏出鑰匙解了車鎖,沈植突然拉住他:“許言。”
許言這才抬頭看他,沈植臉上的疲態很重,眼底紅布,輕微發白——許言可悲地發覺自己到現在竟然還會為這個人心疼。他甩開沈植的手,不開口說任何話,可沈植又拉住他,低頭把裝餛飩的包裝袋掛到他腕上,說:“那你在自己車里吃了再走。”
車庫里安靜得沒聲音,許言掂了掂手里的餛飩,然后走到一邊,把它扔進垃圾桶。
他轉上車,駛離車庫,后視鏡里,沈植立在原地的影漸漸遙遠,許言只是看著前方,目不斜視。
今天沒有拍攝,一上午都在對著電腦歸檔圖片資料,午休時許言跟陸森站在茶水間里,陸森問他:“上次跟你說的事,考慮得怎麼樣了?”
許言搖搖頭:“不知道,暫時還沒想好。”
“沒事,決定好了就告訴我。”陸森拍拍他的肩,“我個人覺得對你來說是不錯的,去黎待一兩年,回國了就能把你升上來,其他人也不會有想法。而且也算是去深造學習了,你之前沒有專職攝影師的履歷,趁這次去富一下。那邊的雜志社有個旅游板塊,你又拍風景,可以試試的。”
許言知道陸森是為他好,但他之前從沒有出國的打算,突然有這樣的選擇擺在面前,多會有些猶豫。
“嗯,我再好好想想。”許言說。
Advertisement
陸森點了一下頭,朝門口揮手打了個招呼:“Chloe。”
許言跟著轉頭,看見湯韻妍正走進來,便朝笑了下。
“我去看看后期那邊。”陸森抬手看了眼表,“你們繼續休息。”
陸森走后,只剩下他倆,氣氛算不上尷尬,只不過許言不知道該說什麼,干脆就不說話喝水。湯韻妍接了杯水,跟許言并肩靠在流理臺邊,對著杯口輕輕吹了口氣,說:“沈植這幾天都沒回去。”
這開場直白,許言愣了下,說:“哦,這樣。”
“我和他從初中就是同學。”湯韻妍雙手捧住杯子,看著地面,“高三我跟他告白,他答應了。”
許言靜靜聽著,雖然他不知道湯韻妍跟自己說這些是為什麼。
“追他的人很多,我問他為什麼答應跟我在一起,他說不知道。不過這確實是他能說得出來的答案。”湯韻妍說著,笑起來,那笑容莫名有種對小孩子的無奈,“后來我想想,他大概是覺得我跟他很像,理,不稚,也不天真。”
“但我其實沒那麼理智,那時候我覺得自己可以改變他,就讓他試著我小名,約他看電影,買手鏈……不過事實證明,沈植就是個花瓶,里的花瓶。”
“說他外表,看起來像是不缺經歷,或者總是別人對自己的,但都不是,他對待很生疏很陌生,所以總像個旁觀者,好像在談的那個人不是他。”
“后來我跟他說了分手,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有種自己被甩了的覺。”湯韻妍笑笑,喝了口水,說,“我們這幾年一直有聯系,沒做,做朋友反而更合適。他大三的時候,有次突然跟我說,他的一個朋友跟他表白了。”
Advertisement
許言心里咯噔一下——說來說去,還是繞到他上了。
“我問他是怎麼想的,他說不知道。他一個考試拿第一,競賽得金牌的人,一遇到這種問題,回答永遠是不知道。”
“我問你喜歡他嗎,沈植說沒想過要和男生在一起,我說這不是一回事,你到底喜不喜歡他,沈植又說不知道。沒辦法,我只能問他,你喜歡你父母嗎,他回答不喜歡,我問他你喜歡我嗎,他說是對朋友的喜歡,我問他之前有沒有同跟他表白過,他說有,都拒絕了。”
“所以我最后問,如果是別的男生跟你告白,你會這麼猶豫這麼不清不楚嗎,沈植說,不會。”
“我以為這樣過后他心里應該已經有了很清晰的答案,但好像不是,你們在一起的這幾年,似乎不太對勁,我也不知道問題出在哪里,沈植后來什麼都不肯說。”
猜你喜歡
-
完結1115 章

寵妻撩人:老公持證上崗
江彥丞這輩子最落魄的那天遇見譚璿,她冷漠桀驁:「跟我結婚,這五百萬歸你。」他衣衫襤褸,身上有傷,不解地問她:「為什麼?我一無所有。」譚璿毫不在乎:「你的一無所有和口齒不清正符合我的伴侶要求,一年時間,配合我演好戲,我會力所能及給你想要的東西,除了愛情,一切都可以。」黑暗中,江彥丞斂下眉眼,捏著那張支票,唇邊的笑容變得森冷而危險。後來者通通都是將就。心機深沉如他,做慣了人生的主角,怎甘心隻做陪襯?許久後,露出真麵目的江彥丞捏住譚璿的下巴逼近:「老婆,全世界都知道我被你譚小七睡過,誰還敢嫁我?咱們這輩子隻能床頭打架床尾和,離婚可由不得你!」PS:天才女攝影師VS潛伏版霸道總裁先婚後愛的故?
179.2萬字8 26757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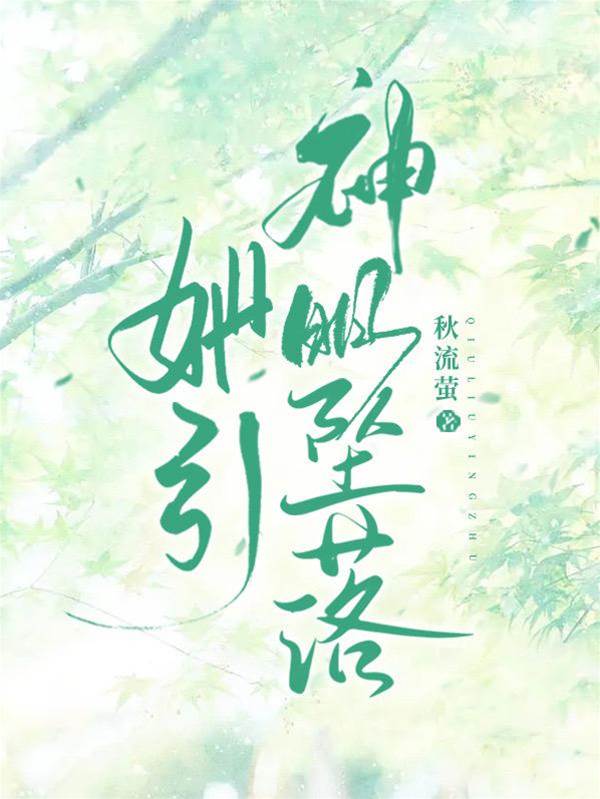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1700 章
霸氣萌寶:封少寵妻送上門
又名《報告爹地:媽咪已綁好》。幾年前,溫時雨和弟弟遭父親無視,受繼母繼妹欺淩,過得苦不堪言。幾年後,溫時雨遇到一隻軟萌酷帥的小萌寶。小萌寶初次見麵,就摟著她脖子,霸氣道:阿姨,我養你啊!溫時雨感動不已。後來,萌寶他爹出現,同樣霸氣道:女人,我養你啊!溫時雨:大可不必!封沉曄絲毫不理,豪車別墅鑽石,紮堆往她跟前送。後來實在不知道該送什麼,索性把自己也送過去。溫時雨一臉苦逼:能退貨嗎?封沉曄:一經送出,概不退貨!
155.9萬字8 59395 -
連載238 章

引野犬裝乖
[霸總x豪門總裁x獨寵x現代言情x1v1][先婚后愛x破鏡重圓x酸甜x救贖向] [專克男主的癲姐x每天都在揣摩老婆到底愛不愛他的別扭大狗] 晉城商貴圈內人盡皆知,賀京準有三宗罪—— 克父克母克老婆。 江寶瓷拍胸脯,對賀老太太保證:“死有窮可怕?您放心,我一定當好這個護身甲。” 賀京準冷面無情,江寶瓷笑盈盈:“老板,你的建模臉太冷,我給你講個笑話,要聽請扣1。” 賀京準煩不勝煩:【2。】 江寶瓷:“要聽兩遍呀,好吧好吧,那給你講兩遍喲。” 然而交易的真相很快便被發現了。 賀京準狠戾決絕:“你死心吧,我娶誰都不娶你!” - 江寶瓷真的走了。 又被接二連三的高管求上門,求她把某位負氣罷工的海運大佬哄回集團上班。 江寶瓷牽著兩人養的狗,走到一處橋洞:“你回不回?” 賀京準面色憔悴:“死活不用你管。” 江寶瓷呵笑,放開狗繩:“你兒子還你,正好要飯有個伴。” 從河邊綠柳下穿梭時,江寶瓷驟然駐足。 身后一人一狗默不作聲地跟著她。 見她望來,賀京準別開視線:“不要它,那就得要我了。” 他眼巴巴地:“老婆,帶我回家。”
39.8萬字8 21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