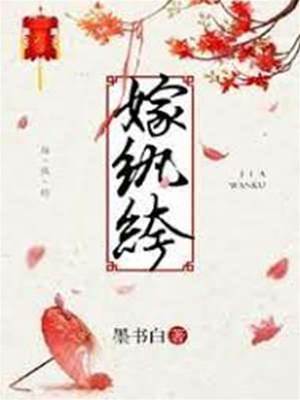《皇后,朕還傻》 第31章 朕的人,也敢欺?
手中的兔子一瞬間有些棘手,蕭容洲看著,眼眸一瞇的同時,糾結著什麼時候拿去給長影宰了。
面前的人,一顰一簇,都了如指掌,看著他認真的樣子也不忍心揭穿,徑直從他手里接過兔子,“剛想起,順兒在那邊無聊。”沖著他擺了擺手,“陛下累了,歇會吧。”
可能是心中太過歡呼雀躍了一些,蕭容洲幾乎是下意識的就將兔子遞給了江明煙。
看著又重新回到自己手里的兔子,江明煙挑了挑眉。
一瞬間,蕭容洲有些后悔,可現在在想反悔已經來不及了,他輕咳了兩聲,趕給江明煙騰地方,“辛苦夫人了。”
得了便宜還賣乖!
一頓飯在江明煙和桃英的忙活下,很快就做好了。四菜一湯,外加一只烤兔子,如此盛的一頓,是桃英一家過年才敢肖想的食。
兔子被烤的外焦里,散發著炙烤的香味。
順兒早就了,看著他睜著一雙大眼睛討吃的模樣,江明煙撕了一只兔子塞進他的小手中。順兒怕是從小到大都沒有吃過如此好吃的兔子,吃的滿油乎乎,桃英在一旁照料著。
江明煙看著歡樂,就連角都勾起了一個好看的弧度。桌子下的手被人捉住,的握著。
微微側目看了蕭容洲一眼,就這麼一瞬間似是從對方的眼中讀到了一與相同的信息在里面。
“你們怎麼不吃,快吃啊。”
桃英招呼著兩個人吃飯,幾個人圍坐在一張不大的方桌前吃的到是十分開心。
晚飯過后,兩人將行李從馬車上拿下放在了桃英準備好的房間里,出門散步去了。
今夜,天幕之上無星,漫無邊際的黑夜籠罩著整個鎮子,月昏黃的掛在天際,灑下來的輝將昏暗的道路的照亮,將兩個人并肩而走的影子拉長。
Advertisement
就算是婚之后,江明煙也沒有與蕭容洲像是這般一樣,靜靜的走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之上。
大梁村遠不如京都熱鬧,一夜,整個村中百姓皆已眠,整個街道靜悄悄的,偶有幾聲蛙聲伴著幾聲蟈蟈的聲響起。
從桃英家走到現在,兩個人皆沒有說話,靜靜的走著,卻越來越覺得像是老夫老妻似的歲月靜好。
“你……”
“你……”
兩個人幾乎是一口同聲,蕭容洲看著月之下子的側,頓住了聲音,“你先說。”
江明煙嗯了一聲,話語像是在口中醞釀了半晌,方才開了口,“我從來沒想到會有朝一日,與陛下這樣。”
“我也沒想到。”
他清潤的聲音之中夾雜著一子愉悅,就連自稱都在不知不覺之中變了。這讓江明煙覺得,仿佛與他的距離更進了一些。
突然覺得如果上輩子的選擇不是蕭云景的話,一切是不是就會變了一模樣。
甚至想問蕭容洲,那時的他與敵對了一輩子究竟是怎麼想的,而后來死后,他的出現又是為了什麼?
可這一切都已經沒了答案。
江明煙吸了吸稍微酸的鼻尖,揚起角,仰頭看著他,“陛下想說什麼?”
這樣的江明煙也是蕭容洲不曾見到的,記憶當中的人每次見到他總是張牙舞爪的,就算是能夠坐下來平心靜氣的說一會話,也是相顧無言,到最后不歡而散。
江明煙說的沒錯,他亦沒有想到會有一天,他們兩個人的關系會變,這讓他有些激,激地恨不得將他一直藏在心底的那個告訴。
將話在口中籌措了半天,鼓起勇氣張開了口,“我其實是想說……”
拐角,鼻間一瞬間飄散出濃郁的腥味,讓蕭容洲的聲音戛然而止的同時,轉過頭去看。
Advertisement
幾乎是同時,江明煙也到了不正常,看向前方拐彎。
只見,大梁村他們進村的土路上不知何時竟是站滿了黑人,月之下,刀鋒上泛著的輝來。
而在看過去的同時,一個黑人正將一個村民從屋子里拖出來,拖行的路上,鮮淋漓。
那人居高臨下的看著手中的人,就像是拎著一塊破布。因隔得有些遠,聽不清對方在說什麼,只見兩個人還沒有談兩句,男人便舉起手中的長劍一刀將人結果了。
上輩子見慣了戰場的江明煙,看見如此屠殺場景也不僅皺了眉宇。
如果猜的不錯的話,這群人屠村,是在找他們。
“走,快走。”
江明煙一把拉過立在側的蕭容洲轉就走。
“什麼人?!”
“陛下小心!”
隨著江明煙的一聲低呵,一道白夾著一抹冷急而來。江明煙拽著蕭容洲猛地退后幾步,整個人擋在了他的前。
冷箭著兩個人的角而過,斜地面之上。
月昏暗,江明煙順著長箭來的方向看過去,就瞧見有黑人正蹲在屋檐之上,彎弓將兩個人瞄準。
長街之上靜的出奇,任何風吹草皆是躲不開江明煙的耳朵,就這麼一瞬間,幾乎是聽見許多雜的腳步聲正在朝著他們兩個人近。
該死的,被包圍了。
再沒有了剛剛的氛圍,江明煙面的冷凝將手放在了腰間劍之上,回過去,一把拽住后蕭容洲的角。
“陛下,你聽我說。”
“要走一起走。”
不等江明煙的聲音再次響起,蕭容洲低沉的話語便已經在后響起。
聽著他越發堅持的聲音,江明煙的眉頭倏然蹙起,“我認真的,你聽好,一會,我去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你就立刻走,回桃英那里。”
Advertisement
單是看剛剛的形,這次來的人不再數,對方恐怕是想要將們置于死地。與往日的幾次不同,這次想要恐怕不易。
大梁村里已經死了太多的人了,不想再賠上蕭容洲,說過,要護好他的。
耳邊是不斷聚集的腳步聲,見立在側的蕭容洲正準備開口,江明煙再次將人打斷,“乖,聽話。我知道長影就在這周圍,去找他,他會護著你。”
說完這話,江明煙立刻就松開了那攥著他袖的手,然而腳步還沒邁出去多遠,就被蕭容洲一把拉住。
月之下,他的這整張面容攏在影里,一時間只看見那翻滾著的黝黑深邃的瞳仁。
“陛下,你……”
江明煙的話沒有說完,眼前驟然一黑。
月之下,一雙白玉修長的手托起了那即將過的。而此時,月從遮擋的云層之中探出頭來,像是染了紅月從天幕之上灑下一道皎潔月,正映照在蕭容洲的上。
拽地的雪長袍不染纖塵之,帶當風,隨風搖曳,長及腰腹的墨發如瀑。他抱著懷中倒下的江明煙,眸微凝。
一瞬間,那立在月之下的男人就像是變了一個人似的,俊無儔的面容像是粹了一層層寒冰,高的鼻梁,淡的就像是櫻花一般艷。
他站在原地,不變的是從容。
不知是誰下的命令,守在屋檐上的弓箭手拉開了弓。
箭之上出的冷白芒將男人的面容映照的清冷矜貴,晚風中,他就像是一朵玉蘭花,花開清雅無雙。
一聲輕嗤的不屑從男人的口中吐出,他像是沒有看到似的,自顧自的將江明煙放在一旁的柱子上靠著。
他站在那里,居高臨下的將人了半晌,又忽覺姿勢似乎是擺放的不太舒服,又將人挪了挪,挪的舒服了,這才角輕勾,滿意的直起腰來。
Advertisement
隨著他的腳步的移,寂靜的夜晚里,便是聽見幾聲清越之聲,定眼去瞧,聲音來,正是掛在腰上的一枚翠玉龍紋玉佩。
翠玉龍紋玉佩聲清脆,在夜里,聲聲催人。
“愣什麼,上。”
隨著一聲令下,圍在四周的黑人已經趕到近前的黑人,當即領命提著長劍就朝著蕭容洲砍去。
濃郁的殺氣撲面而來,冷白的劍直而來的同時,電火石之間,一雙修長白皙的手指將劍尖夾起。
幾人握著長劍想要再次向前,卻發現長劍竟然在他指尖無法撼分毫。
隨著男人慢慢直起腰,他們手中的長劍在他手里就像是一條長泥,被男人擰一串麻花,丟棄在一旁。
“你……”
當先的幾個人僅是一個照面,便被對方卸了武,出的眼睛里著一子恐懼。
對方卻像是染臟了手似的,從懷中掏出一條帕子,了手指,好看的眸之中閃出了一嫌棄。
幾個黑人見他好像在分神,當即撿起地上長劍想要再次襲上,哪知腳剛邁出去一步,脖頸之上倏然一涼,低頭一看,便是瞧見一雙如玉的修長手指正死死的掐著他們的脖頸。
“說,誰派你們來的?”
人被用力的手指掐的臉通紅,雙腳不停地在下面踢騰著。
許是蕭容洲看過來的眼神太過冷漠,以至于面前的人瞳里盡是恐懼之相,但盡管如此,蕭容洲卻依舊沒有聽到他想要的答案。
花這麼多人出,找他們不惜屠村,這樣大的手筆,蕭容洲一時間沒有想到究竟是誰敢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做出這樣的事。
就算是蕭云景也不敢這麼放肆的直接手殺他,更何況這些人的目標似乎不在他,而是江明煙。
想到此,蕭容洲的臉當即一沉,眉眼一瞇的同時,手中的力道稍稍加重了幾。
上挑的尾音,在寂靜的傍晚,顯得異常地清晰,
“怎麼?朕的人,也敢欺?”
作者有話要說:明天公司年會,零點更新預計會推遲到白天。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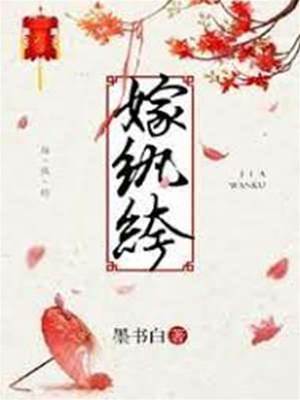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50163 -
完結599 章

世家
出身書香門第之家,有著京城第一才女之名,最後卻落了一個被賣商人妾,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悲慘境地。 重生歸來,連月瑤發誓,這輩子再不讓人操控她的命運。她要走一條全新的路,哪怕佈滿荊棘也要堅持下去。只是世事無常,命運的齒輪早已轉向,一切都偏離了她的預定。
211.1萬字7.73 117268 -
完結544 章
絕世小冤種
睜開眼死了兩遍,洛因幼變成了3歲人類幼崽。意外被面具將軍收養,結果……第一天,放火!第二天,打群架!第三天,眾將士跪在夜辭面前求他把熊孩子送走!
98.6萬字8.18 38915 -
完結176 章

小平安
永國公府十年前走丟的嫡女薛平安,被找回來了,公府衆人站在門口相迎,心思不一。 父母懷歉但又覺得平安生疏,姊妹擔心平安搶了她的寵愛,祖母煩憂平安養成一身鄉下壞習慣,大哥害怕平安長殘無法和豫王殿下完婚…… 直到馬車停下,車簾掀開,小姑娘露出俏生生的半邊臉。 衆人:“……”好可愛! * 一開始,豫王對這個突然歸來的未婚妻,嗤之以鼻,對太監道:“怕不是公府爲了婚約,找來的贗品。” 後來,公府巴不得去豫王府退親,理由是小平安還小,全家都捨不得,應該在家裏多待幾年。 豫王:“……” 退親?退親是不可能的,公府再這樣,他要去公府搶人了。
26.3萬字8.18 2313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