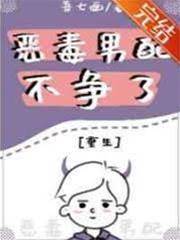《他生來就是我的攻》 182
武大的臉微微的有些紅了,他低聲說:“不, 不用了,我自己就可以。”乖,”許云天拍拍他的頭, “轉過,把背起來。”
武大雖然有點兒,但是鑒于已經和許云天是上過床的夫夫,他知道許云天的長短幾何,許云天知道他的深淺幾許,倒也沒什麼做不到的。
武大乖乖地翻了個,起脊背,趴在沽缸的一側,閉上了眼:“可以了。 ”“嗯。”許云天沉沉答應了一聲。
他看著武大那潔的脊背,看著那骨均勻的線條,嚨一。
“你在干什麼呢?”武大等了好久也沒覺到有油上,奇怪地抬起眼往旁邊一看,震驚地發現,許云天正在服!
他的上已經得干凈,那蘊含著兇猛的力量的,就這麼在外面,展現著男的荷爾蒙氣息。“你你你你服干什麼,”武大慌了,“我要油, 我不要”‘笨,”許云天手彈了彈他的腦殼,“ 我不了,水會濺到服上。武大眨眨眼,總覺得這個理由分外牽強。
可是他還沒來得及多想,許云天就已經打開了油瓶,滴了油在手心,開,溫熱的手掌上了武大的脊背。
番外看遍人間好風12
“唔
武大重新閉上了眼睛,著許云天的手在自己背上輕輕挲掃過。油的濃郁香氣很快被開,彌散在沽室的熱霧之中。
‘那邊, 那邊再一點。”武大背著手,閉著眼,盲指了一下某個地方。
許云天沙啞著嗓子,嗯了一聲,從油瓶里又滴下一滴在手心,隨后,往武大的腰上輕抹。
Advertisement
武大正被得渾舒暢呢,還沒來得及多會兒,就察覺到那只一直在自己背上挲的手,逐漸不老實起來,開始朝著某些地方。
“手,”武大皺了皺眉,“老實點兒。”“知道了。”
許云天輕輕哼了一聲,手上加重了力道。
“嘶”武大了口氣,轉頭嘟囔,“干嘛突然這麼用力, 覺你不是在油,好像是在洗菜。
許云天勾起角一笑。
可不就是洗菜嘛
洗干凈了你這道菜,下鍋,吃個干干凈凈。
武大渾然未覺,被許云天哄著翻過了。許云天手掌上沾著油,輕輕在武大的鎖骨、膛上,隨后,逐漸往下作愈加放肆起來。
武大被他的作弄得越來越,索睜開了眼睛,啪的一下打開了許云天的手:“行 了行了,你別了,我自己來吧。”
許云天看著武大的臉,看著他那雙被水霧潤的眼睛,轉把油瓶放在另一邊,站起,高高在上地看著武大。
“”武大觀察的許云天的模樣, “你這是什麼表?
許云天眨眨眼:“大, 油要,就得從里到外個遍才行。現在,你外面已經了一遍,那麼
武大也不是傻子,許云天這話一說,他就知道,這人又蟲上腦了。“你別靠過來,”武大瞪圓了眼睛,“我現在泡澡是為了的。”“我也是為了讓你。”
“你就是為了你自己的下半,”武大毫不留,冷面穿,一點兒不給許云天留份兒,“呸, 快走快走,我還想接著泡澡呢!”
‘大,你設地方可以躲,這事兒,你也躲不了。”
Advertisement
許云天眸逐漸深沉,他邁開了一步,打算再走近一點。
當他的腳落下的時候,腳下的怪怪的,的,的
許云天剛皺起眉頭,只覺得腳下那塊的東西猛地一溜,他的瞬間失去平衡,都沒來得及出聲,
萌反砰的一下直接砸在了的浴室地板上。
“哎,”武大被許云天搞出的大作嚇了一跳,“ 你這是”許云天整張臉皺在一起,痛得罵了一聲:“.”
武大驚訝地往旁邊一看,一塊溜溜的紫皂,安靜地躺在那里。”你,你踩著皂了,”武大旭尬地笑了笑,朝著許云天出手, “沒事兒吧?”許云天摔得直冷氣:“有事兒。 手,手好像摔折了
“手折了?”武大的臉變了變,飛快地從諾缸中起,小心翼翼地把許云天牽起來, “好像嚴重的,你等著啊,我——我去給你個醫生。”
說罷,他急匆匆地想要出諾室人。
他剛走了幾步,猛地又轉回來,從旁邊扯過一條中一件沽袍,用中簡單干了子,再披上沽袍“忘了,忘了
許云天看著武大的背影,看著這人慢慢往外走去,心里涌起復雜的緒。明明,就差那麼一步就能吃到抹好油的武大了。都是那塊狗屁的皂!
許云天吃痛地著氣,眼睛憤恨地看著那邊躺著的皂,恨不得把這塊東西踩個碎!
番外看遍人間好風13
武大迅速地來了醫生。
醫生看了看許云天的傷勢,上下檢查一番,老練地下了判斷:“手傷著了,可能有骨折。上也有淤青,你還是跟我去拍個片子觀察一下吧,來,起來。”
Advertisement
許云天黑著臉,一瘤一拐地跟著醫生往外走。武大在旁邊扶著他。
顧家睿和單梁本來正在收拾東西呢,聽到靜全出來了,他們看到一瘸一拐的許云天,驚訝地問道:“這怎麼了?”
武大輕輕說道:“摔傷了。
“摔傷了?”顧家睿皺著眉頭,“好好的怎麼會捧這樣”.
單梁盯著武大和許云天,看到他們倆穿的都是浴袍,武大諾袍之下出的一截皮還有異樣的油,心里明白了一。
‘早早的都告訴你們了,”白發蒼蒼的醫生在前面走著,搖了搖頭,“我知道你們年輕人力好,力旺。可也不能這麼瞎搞不是?
武大紅了耳,低下了頭。
“玩兒得這麼激烈,還在浴室里,年輕人啊,浴室的地多啊,”醫生停下腳步,扶了扶眼鏡,一副勸教模樣,“別說是我這副骨頭了, 就是你們摔在上面,那也不得了。
武大掩飾旭尬似的笑了笑:“記住 了,您的話記住了。
許云天一路無話,跟著醫生去了附近一家小醫院,一拍片檢查,果然是骨折了。醫生嘆著氣,又勸誠了一番,麻利地給許云天上了藥,包了紗布。等到他們終于回到湖邊別墅的時候,夜已經很深了。
許云天原本對這次湖邊別墅之旅充滿了期待,他還想著要在這兒好好滿足一番,解鎖各種玩兒法。為此,他還特意去搜索了幾部非常經典但又不可見人的影視作品,仔細觀學習了一番。
但他沒想到,到達湖邊別墅的第一天,新學的第一個玩兒法都還沒派上用場,他的骨頭就折了。這他媽還玩個蛋?
武大看著許云天黑炭的臉,了他的背:“你生 氣了?”“沒生你的氣。”許云天沉著臉。
Advertisement
他當然不會生武大的氣,他怎麼舍得生武大的氣?他是怪自己不爭氣。
怎麼就能那麼傻批地踩在皂上到,還偏偏摔了個骨折?這下好了。乖乖養病吧。
醫生可是嚴詞勸誠過了,不能有太劇烈的運,否則萬一造二次損傷,那恢復起來就更麻煩了。許云天心已經不復來時的喜悅和期待,看著自己糟心的手,嘆了口氣,歌息了。第二天起床的時候,他吃力地單手洗漱完了,來到了餐廳。
餐廳里飄滿早餐的香味。
武大拉著許云天坐下:“你手 別,想吃什麼,我給你夾。” 許云天臭著臉,用下示意了一下那邊的小籠包。武大夾起一個小籠包,放到許云天的邊。
許云天側著頭叼過了小籠包,嚼了兩下,臉這才好看了一些。
“咱們今天有什麼計劃嗎?”武大一邊給許云天夾著食,一邊隨意地問道。
單梁和顧家睿面面相覷,隨后,單梁咳嗽一聲:“按照咱們本來的日程表,今天應該是去湖上釣魚。釣魚?
猜你喜歡
-
完結194 章

變成人魚被養了
擁有水系異能的安謹,穿越到星際,成了條被拍賣的人魚。 斯奧星的人魚兇殘,但歌聲能夠治療精神暴動。 深受精神力暴動痛苦的斯奧星人,做夢都想飼養一條人魚。 即便人魚智商很低,需要花費很多心思去教育培養。 斯奧星人對人魚百般寵愛,只求聽到人魚的歌聲,且不被一爪子拍死。 被精神暴動折磨多年的諾曼陛下,再也忍不住,拍下了變成人魚的安謹。 最初計劃:隨便花點心思養養,獲得好感聽歌,治療精神暴動。 後來:搜羅全星際的好東西做禮物,寶貝,還想要什麼? 某一天,帝國公眾頻道直播陛下日常。 安謹入鏡,全網癱瘓。 #陛下家的人魚智商超高! #好軟的人魚,想要! #@陛下,人魚賣嗎?說個價! 不久後,諾曼陛下抱著美麗的人魚少年,當眾宣布。 “正式介紹一下,我的伴侶,安謹。” 安謹瞪圓眼睛:?我不是你的人魚主子嗎? 溫潤絕美人魚受v佔有欲超強醋罈子陛下攻
42.6萬字8 8679 -
完結2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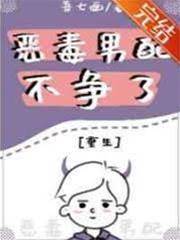
惡毒男配不爭了
生前,晏暠一直不明白,明明是一母同胞的親兄弟,為何父母總是偏愛弟弟,把所有好的都給他,無論自己做什麼都得不到關注。 越是如此,晏暠便越是難受,越是不平,於是處處都和弟弟爭。只要是弟弟想要做的事情,他也去做,並且做的更好。 但明明他才是做的更好的那個人,卻始終得不到周圍人的認可,父母,老師,同學,朋友望著他的眼神都是嫌棄的,說他善妒,自私,喜歡搶別人東西。 一直到死,晏暠才明白,他搶的是主角受的東西。他是一本書中為了襯托主角受善良的惡毒男配,是為了讓主角攻出現打臉,在主角受面前刷好感度的砲灰。 重生回來,晏暠一腳踹開主角,誰特麼要和你爭,老子轉個身,你哭著也追不上我。 他不再爭,不再嫉妒,只想安靜的做自己。讓自己的光芒,照在關注他的人身上。 = 很多年後,有人問已經成為機甲製造大師的晏暠。 「您是怎麼走上機甲製造這條路的?」 「因為遇見了一個人。」晏暠。
56.1萬字8 41611 -
完結135 章

當軟萌受嫁給暴躁總裁
冷酷不耐煩後真香攻×軟萌笨蛋可憐受 1. 江淮從小就比別人笨一點,是別人口中的小傻子。 他這個小傻子,前世被家族聯姻給了一個人渣,婚後兩年被折磨至死。 重活一次,再次面對聯姻的選項,他選擇了看上去還行的“那個人”。 在同居第一天,他就後悔了。 2. “那個人”位高權重,誰都不敢得罪,要命的是,他脾氣暴躁。 住進那人家中第一天,他打碎了那個人珍藏的花瓶。 那個人冷眼旁觀,“摔得好,瓶子是八二年的,您這邊是現金還是支付寶?” 同居半個月,那個人發燒,他擅自解開了那個人的衣襟散熱。 那個人冷冷瞧他,“怎麼不脫你自己的?” 終於結婚後的半年……他攢夠了錢,想離婚。 那個人漫不經心道:“好啊。” “敢踏出這個家門一步,明天我就把你養的小花小草掐死。” 3. 後來,曾經為求自保,把江淮給獻祭的江家人發現——江淮被養的白白胖胖,而江家日漸衰落。 想接江淮回來,“那個人”居高臨下,目光陰翳。 “誰敢把主意打他身上,我要他的命。” 4. 江淮離婚無門,只能按捺住等待時機。 與此同時,他發現,自己的肚子竟然大了起來。 那人哄反胃的他吃飯:老公餵好不好? #老婆真香# #離婚是不可能離婚的,死都不離# 【閱讀指南】:攻受雙初戀。 【高亮】:每當一條抬槓的評論產生,就會有一隻作者君抑鬱一次,發言前淺淺控制一下吧~
28.5萬字8 13197 -
完結115 章

咸魚少爺穿成反派的白月光
唐煜穿書前住的是莊園城堡,家里傭人無數,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錢多到花不完的咸魚生活。一覺醒來,唐煜成了小說里的廢物花瓶,母親留下的公司被舅舅霸占,每個月克扣他的生活費,還在男主和舅舅的哄騙下把自己賣給了大反派秦時律。他仗著自己是秦時律的白…
39.1萬字8 9920 -
完結103 章

懸日
寧一宵以為這輩子不會再見到蘇洄。直到酒店弄錯房卡,開門進去,撞見戴著眼罩的他獨自躺在床上,喊著另一個人的名字,“這麼快就回來了……”衝動扯下了蘇洄的眼罩,可一對視就後悔。 一別六年,重逢應該再體面一點。 · -“至少在第42街的天橋,一無所有的我們曾擁有懸日,哪怕只有15分20秒。”
47.2萬字8.18 16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