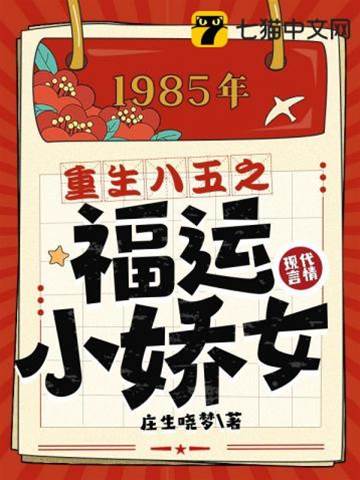《降落我心上》 第33章 33號登機口
這個衛生間只有兩個隔間, 其中一個門開著沒有人, 另一個就是剛剛發出怒罵的那個。
正在阮思嫻猶豫著是去上廁所還是先洗個手的時候, 隔間突然從里面被推開。
一個人氣沖沖地走了出來,到洗手臺前,夾著手機一邊洗手一邊說:“別別別, 你可別為他說話,我跟你說, 遠遠不止這些事, 算了,我現在還在世航, 我現在就帶團隊走, 我一刻也不留, 晚上你出來跟我喝酒我再跟你說。什麼?你有什麼事啊?你推了唄!一定要今天嗎?行了行了, 掛了。”
說完的同時也洗完了手, 半探著子去拿紙巾, 卻一不小心讓手機掉地。
“啪嗒”一聲, 聽起來很慘烈。
大概是人不順的時候做什麼都是坎, 閉眼深吸了一口氣, 甚至想一腳踩到手機上。
阮思嫻也在一旁愣住。
居然是鄭安。
鄭安最終還是彎腰去撿手機, 直起時,阮思嫻已經把紙巾遞到面前。
看到阮思嫻時也愣怔著,半晌沒去接紙巾。
這時候誰不比誰僵呢。
阮思嫻想破頭也想不到在隔間里罵傅明予的人是鄭安。
而鄭安肯定也很后悔自己迫不及待在世航吐槽老板結果被人家員工聽到。
一微妙的尷尬在兩人之間蔓延, 無形之間籠罩著全。
阮思嫻率先打破僵局, 若無其事地把紙巾塞在鄭安手里。
“地上臟, 吧。”
“謝謝啊。”鄭安一邊著手機,一邊裝作漫不經心地說,“你這腮紅好看的,什麼牌子什麼號啊?”
“……熱的。”
“哦。”
誰能想到,傅明予好歹一個航空公司太子爺,高一八七,臉長在當代的審點上了,卻是憑借一己之實力打翻了老天爺賞給他的滿漢全席,躲過了丘比特給他的箭林彈雨,功教育了當代看男人不要只看臉。
Advertisement
作為傅明予的下屬,作為仰仗他的錢包生活的卑微員工,阮思嫻一想到這點,就忍不住笑出聲。
已經出衛生間一步的鄭安突然回頭,有些惱:“你笑什麼?”
怎麼又被抓包了。
阮思嫻有點郁悶,但是好笑還是大于郁悶的,握拳抵著角,想遮住自己的笑容。
“我笑了嗎?”
鄭安這下不是惱了,是氣惱。
“你是不是聽到了?”
阮思嫻憋著笑點頭:“我不是故意聽的,但是你實在太大聲了。”
鄭安鼓著眼睛看著阮思嫻,阮思嫻越發想笑:“我還以為是誰這麼膽大包天敢在世航罵我們傅總呢,原來是你啊,我之前還以為你喜歡他呢。”
“誰會喜歡這種出爾反爾的自大狂啊!”
阮思嫻瞇眼看,“這樣啊……”
鄭安被看得些底氣不足,倔強地抬了抬下,“OK,我之前是有一點喜歡他,不過現在不可能了,誰會喜歡這麼一個神經病啊!”
說完,頓了一下,似乎是出于人的直覺,歪著頭看阮思嫻。
“你喜歡他啊?”
阮思嫻臉上的笑意瞬間消失地干干凈凈,冷笑一聲:“誰喜歡他那種自狂?我瘋了嗎?”
話音落下,小小的衛生間詭異的沉默了片刻。
鄭安竟然從阮思嫻的話里還聽出了幾分討厭的意味。
好奇地打量著阮思嫻,問道:“真的假的?”
阮思嫻覺得自己今天話是真的多,而且也沒必要跟鄭安解釋,于是轉就要走。
鄭安一把拉住,“難得遇到一個討厭傅明予的人,走啊,晚上一起喝酒去?”
“……不了吧?”
“走啊,我請客。”
“不了,我晚上有約。”
Advertisement
“什麼約啊?重要嗎?不重要就推了唄。”
看來這位姐還是屬鴿子的。
但是阮思嫻在這一刻確實猶豫了一下。
一方面,對鄭安的緒一直有些說不清道不明,探究總是不控制。
另一方面,真的好好奇傅明予到底怎麼把這位大小姐得罪這樣的。
不知道是不是和對一樣,不就“你不如做夢。”
走近卞璇的酒吧那一刻,阮思嫻還于無限迷茫中。
也是想破頭都沒有想到自己居然會和鄭安坐在一張桌子上喝酒,牽線人還是傅明予。
鄭安面前的酒已經下去一大半了,而阮思嫻的果還沒喝兩口。
“明明是你們世航的人打電話邀請我來拍攝,我什麼都準備好了,而且本來最近還有個參展我都推掉了,結果現在他說換掉我就換掉我,憑什麼嘛!”
“又不是我求著要來給他們拍的,我也很忙的!而且我們兩家什麼關系,他連這點面子都不給我,是打我的臉還是打我爸的臉呢?我從小到大就沒過這種委屈!”
聽到這邊的靜,卞璇借著送小吃的機會過來,朝阮思嫻眨了眨眼睛。
阮思嫻輕咳一聲,“我先去上個廁所啊。”
鄭安煩悶地揮揮手,“快去快回,我心里悶得慌。”
“哦。”
阮思嫻朝卞璇一使眼,兩人一起去了廁所。
“誰啊?你朋友?我怎麼沒見過?”
“鄭安。”
“聽著有點耳啊。”卞璇掏了掏耳朵,突然驚詫地說,“你怎麼和攪到一起了?”
這個理由實在難以啟齒,阮思嫻咬著后槽牙,半晌才說:“傅……”
后面兩個字還沒說出來就被卞璇截斷,“這也能跟傅明予有關?”
Advertisement
阮思嫻半白著眼睛看,“負責給我拍照片的是,認識了一下。”
“哦,這樣啊。”卞璇訕笑,“我還以為又是因為你們傅總呢。”
阮思嫻想走,卞璇又拉住。
“不過知道你是誰嗎?”
據這幾次的見面,阮思嫻斷定是不知道的。
“肯定不知道。”
這倒是讓卞璇心里擰了一下,“你一直沒去見過那邊啊?”
阮思嫻搖頭。
卞璇心想,看來媽媽也沒在那邊提過。
“你到現在也是跟你媽媽完全沒聯系啊?”
以為會得到肯定的回答,阮思嫻卻說:“也不是。”
靠著墻壁,仰頭呼了口氣,“一直在給我打錢。”
這次沒等卞璇問,阮思嫻主說,“這些年一直在給我打錢,兩三個月就會收到一次吧。”
“多?”
阮思嫻白一眼,掉錢眼里去了嗎?
“沒注意,零零總總,兩三百萬吧。”
“……?”
卞璇倒吸一口氮氣,“這就過分了啊你這個富婆,前年找你借錢周轉一下你還說沒有。”
“我那時候是真沒有。”阮思嫻說,“我媽給我打的錢我一直沒過。”
“不是,你為什麼啊?”
卞璇早就想問這個問題了,“多家庭父母離婚啊,這是很正常的,你爸媽好像也是和平分手吧?也沒撕破臉,而且離婚四年才再嫁,這也沒什麼吧?你怎麼就這麼介意?”
阮思嫻抬頭看天花板,眼睛霧蒙蒙的,看不清緒。
等了一會兒,只搖搖頭說:“不說這個了,我過去了。”
卞璇好奇,卻也無可奈何,關于這方面的事,阮思嫻不想說,誰也撬不開的。
坐下后,阮思嫻接著剛剛的話題問:“為什麼換掉你?”
Advertisement
“他說我風格不合適。”
阮思嫻嘀咕道:“他一個學管理的,他能懂這個嗎?”
“對對對!”鄭安手掌連續拍了幾下桌子,“我打電話問他,他說什麼太細膩不大氣,搞什麼呢?從來沒有人這麼說過我的。我去年去非洲拍的大遷徙還得獎了呢!不大氣嗎?他本就不懂攝影!”
阮思嫻了下,鄭安又繼續說道:“還有上次給你們拍照片,給的錢還不夠我買個包的,他卻說我拍得不好。”
正聽著,阮思嫻的手機響了一下,是傅明予發來的消息。
[傅明予]:你還沒回家?
阮思嫻一邊點頭說是,一邊飛速給傅明予回了個“?”
“還有還有,那次我搭他個順風飛機去西班牙,十幾個小時理都不理我一下,覺就像把我當做、當做……”
卡了半天說不出一個形容詞,阮思嫻補充道:“把你當做托運行李了?”
“對對對!”鄭安激起來又開始拍桌子,“現在回想起來我都不知道我怎麼忍的。”
同時,傅明予一個電話打來。
阮思嫻看到來電心里莫名一慌,有一種背后說人壞話即將被抓包的覺。
立刻掛了電話,回了條消息。
[阮思嫻]:什麼事?
[傅明予]:接電話。
[阮思嫻]:不方便,你打字不行嗎?
[傅明予]:不行。
[阮思嫻]:不行就算了。
“還有以前的事,那可太多了。”鄭安一張小叭叭叭地說個不停,“以前一見面吧,每次我還沒怎麼呢,他就離我八丈遠,那覺真的……就……”
“覺他好像覺得你很喜歡他一樣?”
鄭安猛點頭,五全都皺在一起,“對對對!好像我非要跟他怎麼樣似的。”
這一點阮思嫻深表同意,冷靜地點了點頭。
可是一個多小時過去,阮思嫻已經開始強行忍瞌睡,忍得眼淚都要出來了。
姐,你吐槽一個多小時了,來來去去就那麼幾件事,傅明予他不懂得欣賞你的作品,他沒眼,他沒眼力,他大豬蹄子。他對你答不理,你明天讓他高攀不起,而我連晚飯都還沒吃呢。
這就算了,鄭安重復這麼多遍后,竟然還趴著哭了起來。
“我從小到大就沒過這麼多委屈。”
阮思嫻一下子背都繃直了。
人吐槽男人不可怕,可怕地是還哭了起來,這樣沒個三四個小時別想收場。
清醒使得阮思嫻立刻拿出手機給傅明予發消息。
[阮思嫻]:不能算了,你現在就過來找我。
你弄哭的人你自己來收場,憑什麼要折磨我!
猜你喜歡
-
完結46 章

引我癡迷
十九歲那年,周琬盈第一次見到謝凜,和他目光一對視,她就感覺到心臟砰砰亂跳,臉紅得像蘋果。可那時候的周琬盈膽子小,喜歡也不敢追。何況謝凜在圈子里出了名的高冷,且不近女色。于是她就悄悄喜歡,每次在公開場合見到謝凜,也只是朝他笑一笑,別的一點也不…
7.7萬字8.18 6092 -
完結3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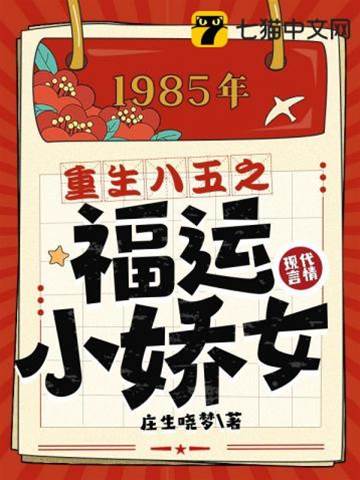
重生八五之福運小嬌女
前世,喬金靈臨死前才知道爸爸死在閨蜜王曉嬌之手! 玉石俱焚,她一朝重生在85年,那年她6歲,還來得及救爸爸...... 這一次,她不再輕信,該打的打,該懟的懟。 福星錦鯉體質,接觸她的人都幸運起來。 而且一個不留神,她就幫著全家走向人生巔峰,當富二代不香嘛? 只是小時候認識的小男孩,長大后老是纏著她。 清泠儒雅的外交官宋益善,指著額頭的疤,輕聲對她說道:“你小時候打的,毀容了,你得負責。 ”
70.5萬字8 21891 -
完結583 章
滿級大佬在線虐渣
她是天尊大佬,製藥、練丹、畫符樣樣精通,卻慘遭各路修真者圍剿令她三魂七魄只剩一縷。 再次醒來,魂穿現代。 校園欺淩? 大佬手一揮,欺她者全滅。 她是醜八怪? 臉上醜疤一揭,奪校花之位佔校園頭榜。 她很窮? 動動手指,將他們名下企業全收購。 她無人敢要? 某身份顯赫、位高權重的男人死纏爛打第九百九十次求婚:“阿初今天考慮嫁我了嗎? ”
103.9萬字8 28418 -
完結76 章

十九日
【溫柔理智女作家許惟vs傲嬌別扭大少爺鍾恒】【姐弟戀 微懸疑 破鏡重圓 校園 都市 愛情】鍾恒初見到許惟時,他還是個夢想“一統豐州六校”的扛把子。之後,酷跩、傲嬌、硬氣的鍾少爺,隻想“跟許惟考一個城市去”。她是難以企及的優等生,他就做拚盡熱血、力挽狂瀾的一匹黑馬。隻為著那一句“不分開”。一樁案件,撲朔迷離、險象環生,曆十九日,終是塵埃落定。這是許惟和鍾恒重逢的第十九日。
19.6萬字8 481 -
完結300 章

延時熱戀
林曦十七歲那年,傷了耳朵暫時失語。父母車禍離世,她和哥哥相依為命。 后來哥哥工作調動離開,她被接到臨市外婆家生活。 期間,哥哥囑托朋友來看她,來得最頻繁的,就是那個比她大了五歲的“三哥”——秦嶼。 京市距離臨市一百多公里,他堅持陪她看醫生,耐心教她講話,甚至每晚都會準時出現在她的校門口。 他將僅有的溫柔全都留給了她,但一切又在她鼓起勇氣表白前戛然而止。 暗戀未果,家里又突生變故,她遠走他鄉和他徹底斷了聯系。 再見面,是她七年后回國相親,被他堵在餐廳走廊,“樓下那個就是你的相親對象?怎麼在國外待了幾年眼光越來越差了。身邊有更好的選擇,你還能看上他?” “誰是更好的選擇?” 她下意識追問。 秦嶼:“我。”
43.3萬字8.18 86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