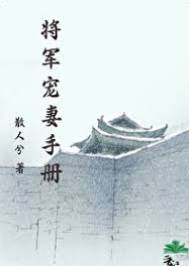《穿成反派的炮灰前妻》 第二章
一個滿臉橫的軍漢惡狠狠瞪著林初。
刀鋒的寒涼瞬間激起了林初脖子上一層皮疙瘩,濃郁的腥味讓胃裡一陣陣的噁心。
臥槽!
老娘這是招誰惹誰了!
還沒看到反派相公長啥樣呢!
林初心中萬馬奔騰而過。
「王虎,你這是做什麼,把刀放下!」另一個站在床邊的疤臉軍漢斥道。
想來那個疤臉軍漢在這群莽漢中還是有些威信的,王虎的軍漢聽了他的話,剜了林初一眼,才憤恨將刀收了回去。
林初用力在自己說手背上掐了一把,疼得眼淚花花直在眼眶裡打轉,「相公——」
這一嗓子得那個凄厲啊,林初自己自己手臂上都給激起了一層皮疙瘩。
所有人都愣愣看著。
只見林初撲倒在床前,噙在眼眶的淚也恰在這時候「啪嗒」砸在了床沿上,一副悲傷不能自已的樣子,「你若是出了什麼事,可我怎麼活啊……」
跟著就嗚嗚大哭起來。
軍漢們面面相覷,這還是前幾天要死要活跟他們大哥鬧悔婚的人嗎?
假哭的林初總算是看清了自己的反派相公燕明戈長什麼模樣。
儘管臉上大片大片的污,但五的廓還是清晰的。
這原著中的值擔當大反派燕明戈,的確是好看得當真令人髮指啊!
一道劍眉斜飛鬢,天生帶著幾分凌厲和銳氣。許是疼痛的原因,即使昏迷著,好看的眉峰也輕攏著。鼻樑很,林初覺得,就是這鼻樑,讓反派相公乍一看,不那麼氣,多了幾分男子才有的剛。他的偏薄,儘管被被封吹得乾裂,但還是能看出他的形是極好看。
角帶著,顯出幾分殘酷悍野的味道。
雖然有些憾看不見反派相公有著怎樣一雙眼,不過林初相信,只要劍眉下方那雙閉的眸子掀開,一定是狼一樣的目!
Advertisement
「燕娘子先別哭,給我打盆熱水來!」軍醫大喊。
燕明戈眼下的況似乎一點都不樂觀,軍醫丟在地上的紗布全是,床上的被褥也被鮮染一片深。
原著中沒有過多描述燕明戈傷的這一段,只作為回憶一筆帶過。
所以眼下哪怕林初知道燕明戈死不了,還是被這鮮嚇得手忙腳。
「灶上有熱水!我去提過來!」滿臉淚痕跌跌撞撞往外跑,看起來真跟躺在床上的燕明戈伉儷深似的。
兩個軍漢忙跟在後面去幫忙。
灶上的熱水是林初之前洗豬下水之後剩下的,兩個軍漢端了兩盆過去就沒有了。
林初也不知道水夠不夠,就又燒了一鍋。
恰好水缸空了,瞅著眼下免費勞力多,就讓一個軍漢幫忙去擔水。
林初坐在小木凳上看著灶里的火,心中沉思著,燕明戈傷了,這是刷好度的一個機會。不過原著中的燕明戈,格暴戾,喜怒無常,這麼貿然前去當狗子,被看不順眼一掌拍死了怎麼辦?
這煩著呢,就聽見一個婦人怪氣道,「這燕百戶還沒斷氣呢,有些人就開始給自己找下家了!」
這是在說讓人幫忙挑水的事嗎?
林初抬頭看了一眼,那婦人約莫三十齣頭,一張大餅臉,五扁平,許是生過孩子又常年勞作的原因,腰背骨架比男人還,此刻正一臉鄙夷的看著自己。
接二連三的被人挖苦諷刺,饒是林初再佛,也忍不住火了,「大娘你哪位?」
還跑家裡擺威風來了?
李氏平日里就喜歡打聽些東家長西家短的事,然後在婦人間添油加醋說道一番。原主之前的名聲能鬧的整個羌城人盡皆知,可以說李氏功不可沒。
這不,聽說燕百戶是被人抬回來的,一個下不得床了的丈夫,一個貌如花又不安分的新婚小媳婦,這怎麼都人浮想聯翩。李氏午飯都沒顧得上做,就跑這邊看熱鬧來了。
Advertisement
李氏見林初還敢懟人,哂笑一聲,「做了見不得人的事還怕被人說?」
林初心中的怒火蹭蹭蹭往上漲,見方才讓幫忙挑水的軍漢擔水回來了,便帶著哭腔大聲道,「我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了?我夫君如今躺在裡面生死未卜,大夫要用水,家中水缸空了,那位兄弟仗義,去幫忙擔水了,就被你這婦人說道,你到底安的什麼心?我夫君跟你有什麼仇什麼怨吶?你要在這時候來嚼舌子?」
又在自己手背上掐了一把,疼得瞬間飆淚,原主本就生得跟朵小白蓮似的,這麼一哭,瞬間那一個梨花帶雨,而且話里話外都是為了燕明戈好。
果然,那擔水的軍漢聽見林初的話,將裝滿清水的兩隻水桶重重往地上一放,怒道,「誰敢耽擱我燕大哥治傷,老子把腦袋擰下來!」
李氏的男人也是行伍出,不過現在上了年紀,一直在城門那邊當值。自己也生得虎背熊腰,瞅著這軍漢年紀頗輕,也當回事,繼續嗤笑,「瞧瞧,這姘夫都為你說話了!」
「死婆你胡說什麼!」軍漢年氣盛,被人污衊氣得臉都紅了,起地上一還沒劈柴禾的木頭就要跟李氏手。
屋外的靜讓屋裡的幾個軍漢也出來了。
那疤臉軍漢喝到,「六子,怎麼回事?」
李氏見人多了,更加唯恐天下不一般道,「看看,看看!我燕兄弟如今生死未卜,我不過教訓了這小賤蹄子兩句,這姘夫就要拿棒殺我了!」
「三哥,我沒有!」年輕的軍漢估計是第一次被人這般污衊,氣的臉紅脖子。
林初充分發揮原主小白蓮的優勢,繼續用力在自己手臂上一掐,那眼淚說來就來,收都收不住,「之前是我年輕不懂事,但現在我是一心一意想跟相公好好過日子的!我知道我名聲夠臭的了,大娘你再說我什麼,我都認了,可是這是跟我相公一起出生死的弟兄!你這麼污衊我們,你其心可誅啊!」
Advertisement
在這關外,家裡若是沒個男人,一個弱子是絕對撐不下去的。
林初突來的轉變,讓軍漢們以為是這幾日想通了,要安安分分跟著燕百戶過日子。
一朵花兒懺悔示弱,讓一群原本極度厭惡的軍漢心中都有了幾分憐憫。
他們之前就聽見林初刻意加大嗓音的話了,再一聯想,大抵也清楚是怎麼一回事。
這李氏平日里就喜歡添油加醋說閑話,可是眼下在人命攸關的時候作妖,還妄圖挑撥他們兄弟和燕大哥的關係,這蠢婦只怕是腦子被狗啃了!
疤臉軍漢惻惻盯了李氏一眼,「你這娘們天都是吃糞的嗎?一說話就滿噴屎!王虎,把人給我扔出去!」
那滿臉橫的軍漢當真就要扔人,李氏這下不敢撒潑耍混了,真被扔出去,腰估計都得摔折!
手忙腳跑出去好遠,才沖著林初和軍漢們啐了一口。
王虎做勢要追上去,嚇得李氏跌了一跤,連滾帶爬的跑了。
一場鬧劇就這樣結束。
軍醫還在給燕百戶理傷口,軍漢們繼續在屋子裡看著。
那個幫林初挑水的年輕軍漢許是為了避嫌,也待在屋子裡不肯出來。
林初也沒想再找人幫忙,這萬惡的古代,找人幫忙挑個水都能被人說長道短,也是夠糟心的了!
這弱,林初是拎不那滿滿一桶水的,只能裝進木盆里,再往水缸里倒。
等把兩桶水都倒進水缸里,水缸才滿了五分之一。
林初已經累得汗流浹背,的視線落在灶臺旁邊的漆桶上,桶里是洗乾淨的豬下水,還有蘭芝給的那塊豬。
本來打算煮吃的,誰知會突然出了這樣的意外。
肚子得咕咕,可是林初也知道自己現在不能煮吃的,那些軍漢看樣子都是燕明戈的兄弟,按理說,作為這個家裡的主人,是得煮飯款待一下的。
Advertisement
可是米缸空空,就算把這些豬下水和那塊豬全煮了,也不夠那些膀大腰圓的軍漢們塞牙啊。
思來想去,林初提著一壺燒得滾燙的開水走進了屋子,拿出六個陶碗,倒了開水端給那些軍漢。
軍漢們面面相覷,不知道該不該接。
林初覺得,自己要是想在這裡好好生活下去,不僅得刷燕明戈對的好度,還得先刷一下眾人對自己的好度,於是哽咽著說,「多謝眾位兄弟將我相公帶了回來,家中沒有茶葉,只能請大家喝碗白水了。」
還是那個疤臉軍漢接下了林初遞過來的水,說了句,「嫂嫂客氣,若不是燕大哥,只怕我們都不能站在這裡了。」
林初察覺他這話低沉,一群軍漢似乎也都沉默了,就猜到應該是戰場上出了什麼事,也不好多問。
不過既然這個軍漢都表了態一聲嫂嫂,餘下四個軍漢也不用林初親自倒水,自己就提起水壺倒了一碗水端著喝。
「不勞煩嫂嫂,我們自己來。」
除了最先用刀抵著林初脖子的王虎和那個挑水的年輕軍漢,神間似乎有些不自在,另外兩個軍漢對林初的態度都友好了很多。
「好了。」軍醫的這句話,讓一屋子的人瞬間都圍到了床前。
「胡軍醫,燕大哥怎麼樣?」軍漢們搶著問。
「先讓老夫喝口水。」軍醫道。
林初忙遞了一碗水過去。
軍醫喝了個乾淨,才舒了一口氣說,「命是保住了。」
這是林初意料之中的事,軍漢們卻都鬆了一口氣,顯然只是都是懸著一顆心的。
「燕明戈這小子!命大,閻王爺都不肯收他!」軍醫話語裡帶著笑意。「好好養一個月,估計就能下地了。」
「我就說燕大哥肯定會沒事的!」那個王虎的軍漢,竟然嗚嗚哭了起來。
「老五,你也就這點出息!」其餘軍漢打趣他,不過眼眶都是微紅的,顯然是真的擔心燕百戶的傷。
不多時又有軍漢上門來,帶著五升米和兩塊豬。
林初瞧著這次來的人應該是個當的,因為為首的那小鬍子穿的甲胄明顯不尋常士兵穿的,神也頗為倨傲。
「燕百戶在這一戰中傷了,將軍掛念著呢,燕百戶傷勢怎麼樣啊?」旗排雖是這麼問的,可是那語氣可一點也不親近,顯然沒把這麼一條人命放在眼裡。
「上刀傷斧傷好幾,最嚴重的還是口那一箭,若是再偏一點,人就救不回來了……」軍醫面對旗牌,說話似乎也疏離了許多。
「那讓燕百戶好好養著吧。」旗牌神倨傲,「這些東西都是給燕百戶補的。」他示意左右的小兵將米和放下。又掏出一個錢袋,看上去鼓鼓囊囊的,不過聽他晃錢袋的聲音,就知道裡面是銅錢居多。
「這些,也是賞給燕百戶的。」他的視線在屋掃了一圈,最終定格在林初上,瞇瞇的目將林初從頭到腳打量了好幾遍,才調笑道,「喲,聽說燕百戶前些日子才娶了個漂亮媳婦兒,今日一見,果真不假……」
那視線盯得林初頭皮發麻,心中草泥馬草罵了千萬遍,但現實里只能低頭看著自己的腳尖兒不說話。
。
猜你喜歡
-
完結72 章

終身妥協
“只有我不要的玩意兒,才會拿出來資源共享。” “安棠算個什麼東西?我會喜歡她?” “玩玩而已,當不得真。” 港城上流圈的人都知道,安棠深愛賀言郁,曾為他擋刀,差點丟了性命。 無論賀言郁怎麼對安棠,她看他的眼神永遠帶著愛意,熾熱而灼目。 * 賀言郁生日那晚。 圈內公子哥們起哄:“郁少,安小姐今年恐怕又費了不少心思給您準備禮物吧?真令人羨慕。” 他指尖夾著香煙,漫不經心:“都是些沒用的玩意兒,有什麼好羨慕的。” 賀言郁已經習慣踐踏安棠的真心,反正她愛他不可自拔,永遠都不會離開他。 然而—— 也就在這晚,安棠突然人間蒸發。 港城再無她的蹤跡。 * 安棠從小就有嚴重的心理疾病,溫淮之是她的解藥。 溫淮之重病昏迷后,她舊疾復發,絕望崩潰之際在港城遇到賀言郁。 那個男人有著一張跟溫淮之相同的臉。 從此,安棠飲鴆止渴,把賀言郁當做溫淮之的替身,借此來治療自己的心理疾病。 相戀三年,安棠的病得到控制。 某天,她接到溫淮之的電話。 “棠棠,哥哥想你了。” 安棠喜極而泣,連夜乘坐飛機回到英國。 * 安棠消失后,賀言郁徹底慌了,發瘋似的找她。 結果,兩人相逢卻是在葬禮上。 身穿黑裙,胸前戴著白花的安棠,雙眼空洞,仿佛丟了魂。 那時賀言郁才知道,他們是青梅竹馬,彼此深愛。 而他,只不過是溫淮之的替身。 * 那天晚上大雨滂沱,賀言郁滿懷不甘和嫉妒,求著安棠不要離開他。 安棠用冰涼的指腹撫上他的臉。 “你不是淮之。”她笑,“但你可以一步步變成他。” “安棠會離開賀言郁,但絕不會離開溫淮之。” 那一刻,賀言郁從她眼里看到溫柔的殘忍。 后來,賀言郁活成了溫淮之。 他愛她,愛到甘愿變成情敵的模樣。 * 【排雷】 雷點都在文案里,追妻火葬場地獄級 男主前期又渣又狗,后期top舔狗 女主有嚴重心理疾病,但是會就醫治療,看立意
22.1萬字8 26921 -
完結179 章

掌中春色
陸執光風霽月,是天子近臣,寧國公獨子。 寧國公摯友戰死沙場,愛女無依無靠,被國公爺收留。 國公爺痛哭流涕,對外揚言定會視如己出,好生照顧。 小姑娘剛來那年乳臭未乾,傻乎乎的,還帶着稚氣,陸執看不上,沒瞧她第二眼。 不想到幾年後再見,人出落得清婉脫俗,便好似那天上的仙女一般,柳夭桃豔,魅惑人心。 陸執,越瞧心越癢癢...
25.7萬字8 14436 -
完結179 章

近我者甜
裴家小小姐裴恬週歲宴抓週時,承載着家族的殷切希望,周身圍了一圈的筆墨紙硯。 頂着衆人的期待目光,小小姐不動如山,兩隻眼睛笑如彎月,咿咿呀呀地看向前方的小少年,“要,要他。” 不遠處,年僅五歲的陸家小少爺咬碎口中的水果糖,怔在原地。 從此,陸池舟的整個青蔥時代,都背上了個小拖油瓶。 可後來,沒人再提這樁津津樂道了許多年的笑談。 原因無他,不合適。 二十五歲的陸池舟心思深沉,手段狠戾,乾脆利落地剷除異己,順利執掌整個陸氏。 而彼時的裴恬,依舊是裴家泡在蜜罐里長大的寶貝,最大的煩惱不過在於嗑的cp是假的。 所有人都極有默契地認定這倆be了,連裴恬也這麼認爲。 直到一次宴會,衆人看到,醉了酒的裴恬把陸池舟按在沙發上親。 而一向禁慾冷淡,等閒不能近身的陸池舟笑得像個妖孽,他指着自己的脣,緩聲誘哄:“親這兒。” 酒醒後的裴恬得知自己的罪行後,數了數身家,連夜逃跑,卻被陸池舟逮住。 男人笑容斯文,金絲邊眼鏡反射出薄涼的弧度:“想跑?不負責?”“怎麼負責?” 陸池舟指着被咬破的脣,低聲暗示:“白被你佔了這麼多年名分了?” 裴恬委屈地抽了抽鼻子,“你現在太貴了,我招不起。” 男人吻下來,嗓音低啞:“我可以倒貼。”
30.9萬字8 19040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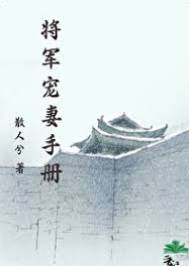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
完結176 章

天鵝與荊棘
苦練四年的芭蕾舞劇即將演出,許嘉卻在登臺前被通知換角。 表演結束,她去找對方質問,沒想到撞進分手現場。 女演員哭花了妝,從許嘉身邊跑過。 她投以冷漠的一瞥,看向站在平臺中的男人。 邵宴清,豪門繼承人,手握大半的演藝資源,是圈內最堅固的靠山。 他與她像是雲和泥,一個如天邊月,一個如地上塵。 若錯過這個機會,她再無輕易翻身的可能。 “邵先生。” 許嘉走向他,從他手裏接過點燃的煙,將溼潤的菸嘴放入自己脣間,“要和我試一試嗎。” 邵宴清漠然地看向她,一言不發地提步離開。 許嘉以爲計劃失敗,三天後卻收到請函。 上面竟寫着:邀請您參加許嘉與邵宴清的婚禮。 — 許嘉非常明白,這場婚姻只是交易。 即使在感情最融洽時,她也沒有任何猶豫地選擇離開。 很快鬧出傳聞,說邵宴清爲一個女人着魔,新建公司,投資舞團,費勁心力只爲挽回她的芳心。 許嘉對此不以爲意,回到家門口卻是愣住。 一道高挑的身影守在門前,腦袋低垂,肩膀處覆有寒霜。 邵宴清的眼睛佈滿血絲,顫抖地攥住她的手,咬牙質問:“許嘉,你都沒有心嗎?” 許嘉尚未回答,已被他抵至牆邊。 邵宴清摟住她的腰,冰冷的脣覆在她的耳畔,似警告又似祈求:“許嘉,說你愛我。”
25.8萬字8 195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