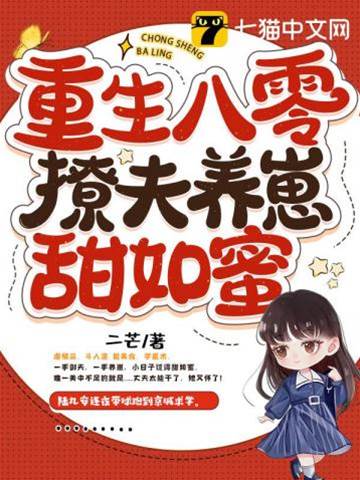《第一寵婚:顧少,不可以!》 第26章 是不是,該給她一個驚喜?
顧凌謙的話,就像是七月里的冰霜,在大熱天里,凍骨髓!
夏一念費了好長一段時間,才將他的話徹底消化掉!
心頭,蒙上了一片影,涼颼颼的。
讓永安孤兒院所有人陪葬,以他顧家凌爺的份地位,要做到這一點,並不難。
夏一念心裡真的很慌,很不安。
顧凌謙眼底那一瞬間的寒氣,已經消失在他習慣淺淡的笑意中。
「夏小姐只要做好自己本分的事,就不用顧慮這些。」
「什、什麼本分的事?」夏一念的聲音,有那麼點生,和木訥。
「一年之不要談,不要在我家人面前說出什麼自己不是我朋友的話。」
「就……這麼簡單?」有點不敢相信。
「難道,你覺得這種事還能有多複雜?」
顧凌謙這次的笑意,是真的,這丫頭……心思有點太單純,想什麼,全都寫在這張臉上了。
Advertisement
「放心,我不是十惡不赦的壞人,我也不會主去害孤兒院的人,沒那麼工夫,明白嗎?」
「可是,如果……是你自己在外頭有人……」
「那麼,協議終止,算我毀約,給小蓮和孤兒院的錢,一分不會。」
「真的嗎?」夏一念眼底重新弄燃起了希,忽然,好想把夏初雪推給他怎麼破?
只要他在外頭有人了,自己就可以功退了,是不是?
那點小心思,顧凌謙看得清楚,莫名的,心頭有那麼點不是滋味。
「我對人很挑,別想著隨便給我塞一個。」他哼了哼,語氣有點不善。
被人看,夏一念一張臉又紅了紅。
深吸一口氣,終於咬了下,認真說:「好,我答應你。」
……
……那丫頭又跑了。
這次,不是從他的地方逃跑那麼簡單,而是,跑到了另一個男人的懷裡!
Advertisement
好,很好!事不過三,這是第三次了是不是?
看來,對真是太仁慈了!
冷颼颼的氣息,得池赫頭皮一陣陣發麻,連話都不敢說。
夏一念又跑了,這次,竟然跟著凌爺回了顧家。
對於夏一念找了顧凌謙這麼一個靠山的行為,池赫不知道該贊聰明,還是該笑愚蠢。
但現在,他是絕對笑不出來,因為,眼前這座火山快要迸發了!
「七、七爺。」雖然明知道自己的話會惹七爺不高興,但,有況,總是要彙報的。
池赫深吸一口氣,才小心翼翼地說:「七爺,那個……夏小姐跟著凌爺回顧家,是……是因為兩人有婚約……」
「很好。」啪的一聲,杯子落在茶幾上,頓時了碎片。
顧北城臉上沒有半點波瀾,看起來還是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
但,茶幾上破碎的酒杯,足見他這一刻的怒火有多大。
Advertisement
池赫嚇得大氣不敢一口,戰戰兢兢地:「七爺,要、要不……我去把帶、帶回來?」
不過這會,顧凌謙應該已經將夏一念帶到顧家,再去帶回來,除非去顧家搶人了。
顧北城不說話,深邃如星辰的眼眸里,一冷笑掠過。
想逃?
很好。
小東西,以為這樣就可以逃出他的掌心,簡直,太天真!
他是不是該給一個驚喜,來獎勵幾次三番從他邊逃跑的勇氣?
猜你喜歡
-
完結1722 章

快穿之女配功德無量
從混沌中醒來的蘇離沒有記憶,身上也沒有系統,只是按照冥冥之中的指引,淡然的過好每一次的輪迴的生活 慢慢的她發現,她每一世的身份均是下場不太好的砲灰..... 百世輪迴,積累了無量的功德金光的蘇離才發現,事情遠不是她認為的那樣簡單
292.3萬字8 27087 -
完結719 章
穿書後我成了娛樂圈天花板
一覺醒來,秦暖穿成了虐文小說里最慘的女主角。面對要被惡毒女二和絕情男主欺負的命運,秦暖冷冷一笑,她現在可是手握整個劇本的女主角。什麼?說她戀愛腦、傻白甜、演技差?拜拜男主,虐虐女二,影后獎盃拿到手!當紅小花:「暖姐是我姐妹!」頂流歌神:「暖姐是我爸爸!」秦家父子+八千萬暖陽:「暖姐是我寶貝!」這時,某個小號暗戳戳發了一條:「暖姐是我小祖宗!」娛樂記者嗅到一絲不尋常,當天#秦暖疑似戀愛##秦暖男友#上了圍脖熱搜。秦暖剛拿完新獎,走下舞臺,被記者圍住。「秦小姐,請問你的男朋友是厲氏總裁嗎?」「秦小姐,請問你是不是和歌神在一起了?」面對記者的採訪,秦暖朝著鏡頭嫵媚一笑,一句話解決了所有緋聞。「要男人有什麼用?只會影響我出劍的速度。」當晚,秦暖就被圈內三獎大滿貫的影帝按進了被子里,咬著耳朵命令:「官宣,現在,立刻,馬上。」第二天,秦暖揉著小腰委屈巴巴地發了一條圍脖:「男人只會影響我出劍的速度,所以……我把劍扔了。」
69.3萬字8 47376 -
完結94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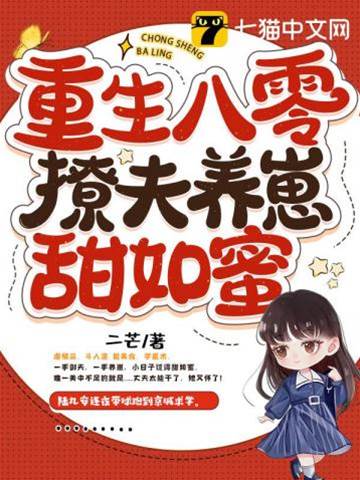
重生八零撩夫養崽甜如蜜
一場綁架,陸九安重回八零年的新婚夜,她果斷選擇收拾包袱跟著新婚丈夫謝蘊寧到林場。虐極品、斗人渣。做美食、學醫術。一手御夫,一手養崽,小日子過得甜如蜜。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丈夫太能干了,她又懷了!怕了怕了!陸九安連夜帶球跑到京城求學。卻發現自己的丈夫站在三尺講臺上,成了她的老師!救命!她真的不想再生崽了!!
174.3萬字8.18 74899 -
完結711 章

高考首富身份曝光,攻略高冷學姐
[都市日常](偏日常+1V1+無系統+學姐+校園戀愛)(女主十章內出現) “兒子,你爸其實是龍國首富!” 老媽的一句話直接給林尋干懵了。 在工地搬磚的老爸
123.7萬字8.33 18213 -
完結242 章

圓橙
直到離開學校許多年後。 在得到那句遲來的抱歉之前。舒沅記憶裏揮之不去的,仍是少年時代那間黑漆漆的器材室倉庫、永遠“不經意”被反鎖的大門、得不到回應的拍打——以及所謂同學們看向她,那些自以為並不傷人的眼神與玩笑話。她記了很多年。 而老天爺對她的眷顧,算起來,卻大概只有一件。 那就是後來,她如願嫁給了那個為她拍案而起、為她打開倉庫大門、為她遮風避雨的人。 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從來屢見不鮮。 連她自己也一直以為,和蔣成的婚姻,不過源於後者的憐憫與成全。 只有蔣成知道。 由始至終真正握住風箏線的人,其實一直都是舒沅。 * 少年時,她是圓滾滾一粒橙,時而微甘時而泛苦。他常把玩著,拿捏著,覺得逗趣,意味盎然。從沒想過,多年後他栽在她手裏,才嘗到真正酸澀滋味。 他愛她到幾近落淚。 庸俗且愚昧。如她當年。
36.8萬字8 103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