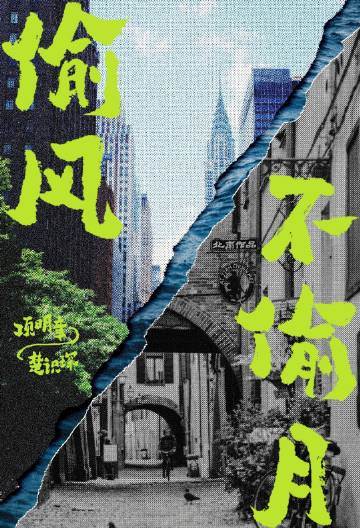《紙婚》 第12頁
江聽白從樓下藥箱里拿了口服,扶靠在床頭,鎖著眉頭看喝完了,又閉了會兒眼,他知道于祗的打小兒就不好,但沒想差到這地步。
這又是哪一年作下的病?
于祗緩了好一陣,在江聽白以為快要睡過去,正要給蓋被子再請醫生,又睜開了眼睛。
江聽白語氣有點張,“我們去檢查一下好嗎?”
是連于祗這種對周邊不大關心的人,都能一耳朵就聽出來的擔憂和不安。
不解地看了他一小眼,但很快收回目,大概因結婚后關系不同了,平時他可不這樣。
于祗擺手道,“在國念書的時候長年不吃早飯引發的,都老病了。”
江聽白不經思索的,問出了個盤桓在心頭很久的疑,“所以你為什麼非要去國讀書?”
明明于家在倫敦的大公寓里,有傭人有司機,于祲過得跟個歐洲貴族似的。可到了于祗,就偏偏在紐黑文這麼個小城市里,什麼都自己來。
于祗剛要抬頭,找個借口答他。
但江聽白一看見的表,他就笑了,站起來道,“我不該在新婚早上問這些。”
Advertisement
于祗自己可能沒發現,一準備開始糊弄他之前,總會先進他的眼睛。
就像那一年高三從上海回了北京上學,江聽白幾次開車去接,吃飯看電影,看差不多了,包了喜歡的餐廳正要表白的那一天下午。
于祗才意識到有點不對,坐在副駕駛上,自以為很給人留面子的,讓他不要來了。
當時就是這副表,江聽白記了將近八年。
而所謂的進展狀況差不多了,也不過是他的一廂愿而已。
于祗從來都沒有,把他們的關系往男朋友這上頭想,還以為江聽白是哥囑托,怕高三剛開課學業力大,特地等放了學來帶出去散散心的。
可即便是這樣,也不喜歡陪著解悶的人是江聽白,所以讓他別再來。
那烏溜溜的眼珠子一轉,不是要騙他,就是要傷他,所以他懶得聽的托辭。
于祗坐在床上,看著江聽白已經下了樓,也沒回過神。
他剛才那笑容怎麼形容呢?
說是真笑吧,他又著些不正經,顯得特別不誠心。說他是怒笑,又有那麼幾分嘲弄,也不知在諷刺什麼。
最讓人疑的是還有點心酸。
Advertisement
今天要去江家過門兒,于祗換上件提前備下的蘇繡旗袍,巧的剪裁勾勒出纖細的腰。金線制的盤扣一系,有種瑞氣灼灼的華。
下樓時,江聽白剛端了碗小餛飩上桌,冒著騰騰的熱氣,于祗聞著香味就往桌邊跑去,“這是你做的?”
江聽白給擺上一把勺子,“怎麼,是我做的你還不吃了?”
于祗嘆了聲氣,“我覺得,你對我有誤會。”
江聽白“哦”了一聲,“你是指哪方面的誤會?”
“我并沒有那麼討厭你。”于祗手里轉著勺柄道。
畢竟以后是一家人,也不想搞得劍拔弩張,面子上能過得去最好了。
他倒鮮的手頓了一下,心知肚明的,“嗯,你沒那麼討厭就好。”
聽出來了,這番說辭他本不信。他們之間的隔閡遠不是一兩句話就可以消弭的。
于祗往里送了個小餛飩,味兒正。
本來還想問他怎麼會做這些,但咬著餛飩的間隙瞄見江聽白冷漠眾生的臉,生生地把話給憋了下去。
不管喝沒喝多,他都不像個人。喝多了是在床上不做人,沒喝多在飯桌上扮佛像。
Advertisement
也不理不得住,只管將抱在懷里狠狠地撞過來,風雨飄搖之際他倒像說了句話,但于祗沒能聽得清。
到了江家以后,江聽白陪著江盛去園子里散步,留下一屋子眷聊些家常話。
陳雁西領了于祗坐在上頭,聽各路親戚們一車又一車的奉承話說出來,拉過兒媳婦的手笑了又笑。
這種場合,于祗雖然是主角,但有個厲害的婆婆在,需要開口的地方很,也樂得清閑。
待江聽白回來時,就看見于祗溫婉安靜地坐在沙發上,不時撥一下鬢邊散下的碎發,面上也沒著意點什麼妝,但那份兒容已是無可比擬的了。在場的另有那麼多jsg別家的年輕小姑娘們,各有各的漂亮法兒,可同他太太堆還是差了好遠一程子。
他又想起昨天晚上來。
于祗地靠在他肩頭上,糯著嗓音讓他輕點,可他迷迷滂滂的哪里肯?說起來也是邪的厲害,那頭兒越是這樣不住,他就越發克制不住自己。
真要細論的話,約莫就是長久以來,他面對著于二時,吞聲踟躕不敢言而壘起來的憾恨在心里作祟吧,好容易等到結婚,才會一腦發泄出來。
Advertisement
仿佛最后那一繃,他眼前白茫茫一片看不清任何,瞧著那口氣也快要續不上來了,他摟著于祗說了句,“織織,我好你。”
但早已昏而無力的于祗本沒聽見。
江聽白著長進了客廳。他坐在了挨著于祗的沙發扶手上,而于祗手里剝著一個橘子,正笑地認真聽江家二伯母說話,連江聽白坐下也沒察覺。
江聽白手緩緩地上的發頂,另一只手搭在點著地的膝蓋上方,臉上流出極見的溺之。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664 章

重生暖婚甜入骨
《重生暖婚甜入骨》【憶瑾年甜寵新作】讓我看看是哪個小倒黴蛋被墨閻王盯上了?哦,原來是我自己……
112.9萬字8.09 43240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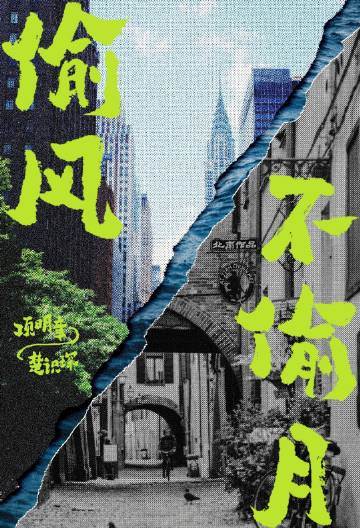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359 -
完結129 章

別哄
沂城傅家丟了個女兒,千辛萬苦尋回后,沂城就傳出了江傅兩家聯姻的消息眾人都以為是豪門里慣有的手段,兩人肯定沒什麼真感情果然,很快就聽說周以尋跟江少斷了聯系,眾人紛紛押注這婚約啥時候能取消江夫人只是去旅了個游,回來后就聽說了這事,她大怒特怒地沖到江京峋的私人住宅,開門進去——卻看到小姑娘穿著件寬大的男士襯衣,瓷白的小腿踢著江京峋,聲音微啞:“滾開啊……”江京峋單膝跪地,把小姑娘攔腰抱起,聲音低啞地哄著她:“老婆,我錯了。”
29.1萬字5 18994 -
連載195 章

軟誘
她是徐家的養女,是周越添的小尾巴,她從小到大都跟著他,直到二十四歲這年,她聽到他說——“徐家的養女而已,我怎麼會真的把她放在心上,咱們這種人家,還是要門當戶對。” 樓阮徹底消失後,周越添到處找她,可卻再也找不到她了。 再次相見,他看到她拉著一身黑的少年走進徐家家門,臉上帶著明亮的笑。 周越添一把拉住她,紅著眼眶問道,“軟軟,你還要不要我……” 白軟乖巧的小姑娘還沒說話,她身旁的人便斜睨過來,雪白的喉結輕滾,笑得懶散,“這位先生,如果你不想今天在警局過夜,就先鬆開我太太的手腕。”
33.8萬字8.18 4282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