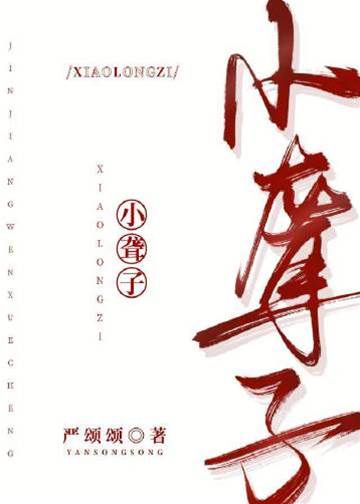《懸日》 第9章 P.螞蟻逃亡
校門口人來人往,寧一宵著煙盒,盯著蘇洄笑著說再見,然后像鳥一樣離開他邊,奔向路邊停靠的一輛車。
駕駛座的司機特意出來,為他拉開車門。養尊優的小爺鉆進車里,降下窗,遙遙著他,一直著他,最后消失在車流中。
寧一宵安靜將煙盒收好,坐上了去往補課學生家的公。
車子里,蘇洄回了頭,不再去看窗外。他開始盯著后視鏡里新司機的臉。這個人看上去四十歲左右,偏壯,額頭上有一塊拇指大小的青胎記。
司機似乎也察覺到蘇洄的目,先是瞥了一眼,然后很殷勤地出笑容,“爺,要不要喝水?我還帶了果,你……”
“您就我小蘇吧。”蘇洄禮貌地笑笑,隨即詢問,“之前沒見過您,張叔呢?”
“他家里出了點事兒,好像是家里老人中風了,得請個長假回去照顧老人。我是徐先生介紹過來的。”他說著,想起來什麼,“哎呀您看我這一著急,都忘了給你自我介紹,我姓馮,馮志國。您就我老馮就行。”
“我您馮叔吧,麻煩您來接我了。”蘇洄聽到他說徐先生,心開始變差。
過了不多時,蘇洄又問,“您是怎麼認識徐叔叔的?”
馮志國聽了一笑,“這說起來都二十年的事兒了吧,他和我是老鄉,從小一塊兒長大的。不過小徐……哦不,徐先生人聰明,書讀得好,當時我就說他能混出頭,你看這不,一步步走到現在,也當了大,來了首都。”
和很多中年男人一樣,馮志國一侃起大山來滔滔不絕。
蘇洄陪聊,不聲地問出他想知道的問題,包括徐治長大的地方,還有他曾經讀過的中學。
Advertisement
蘇洄的父親在他十三歲時就因車禍去世,三年前,徐治和他母親開始往,結婚也有一年。這幾年里蘇洄從未聽過母親說過徐治的過往。
他很想知道這些。因為從徐治出現的那一刻開始,從他侵到自己的家庭起,蘇洄就到不安。
原來徐治的出比自己想象中還要低,可即便如此,依舊得到了外公的認可。
“我們那個小漁村雖然小,也落后,但是出過不人才的。說起來巧,我家那個兒子也還算爭氣,和小蘇爺你一個學校呢。”
馮志國臉上堆了笑,帶著些許驕傲,說起自家的兒子,他便絮絮叨叨了許多,說自家孩子學的是計算機,是特別熱門的專業,報志愿的時候很心虛,好在錄上了。
計算機。
蘇洄想到了寧一宵。
“您兒子……”蘇洄問。
馮志國一聽,覺得蘇洄這麼好奇,一定是想和他的兒子個朋友,格外開心,“啊,他馮程,馮程程那個程。我以前可看《上海灘》了,就喜歡那個主角,所以給他起了這個名字。”
蘇洄點了點頭。
不是一個人。
不知為何,他松了一口氣。
“等哪天我把我兒子也帶過來讓您瞧瞧,打個招呼。”
蘇洄笑笑,沒再接話。
快抵達蘇家大宅,馮志國減緩了速度,“快到了,小蘇爺,您看這個車速可以吧?有沒有哪里不舒服?”
每一任司機都會在他下車前問這樣的問題,前提是他還能自己獨立下車。
“好的。”蘇洄臉上始終帶著笑意,下了車,腳步輕快,“辛苦你了馮叔。”
不同于之前的死氣沉沉,開門的時候蘇洄就覺家里有人,朝里走去,他看到了正抱著一瓶紅酒從地下酒窖上來的陳媽。
Advertisement
蘇洄語氣里帶了些撒的意味,“陳媽,拿的什麼酒呀?”
“小洄回來了?”陳媽笑著,給他看了看酒瓶,“小姐要喝呢,讓我拿出來醒著,今天這麼早就回家呀,累不累啊?”
蘇洄搖頭,“陳媽,我有點想吃剪刀面,想吃菠菜味的。”
“好,一會兒單獨給你做一碗,番茄菠菜面。”陳媽笑盈盈地拿了醒酒壺,和蘇洄一同朝里去。
會客廳里,蘇洄一眼就看到季亞楠,散著一頭長卷發靠在沙發上,手里拿著什麼,很仔細地看著。
或許是病理的“雀躍”,又或許是他真的很久沒有見到媽媽,一時間有些興,腳步都快了些,想和母親說話,想分在學習發生的事,關于他遇到的人,比如寧一宵。
“媽,我回來了。”
季亞楠沒抬眼,“嗯,今天還早的。沒在外面吃東西吧?”
“沒有,在食堂隨便吃了一些飯。”蘇洄沒打算說飲料的事,臉上帶著笑走過去,“你今天怎麼這麼早回家?公司最近不忙嗎,還是要休假?”
“半個月之后你外公七十大壽,我得準備準備呀。這幾天把工作都往后排了排,客戶也沒見了,專門給你外公弄這些。”
將手里的名單往茶幾上一放,食指抵著太,“是這賓客名單就看得我頭疼,都是些有頭有臉的大人,座位啊喜好啊,都得好好弄。”
這哪里像是祝壽,簡直就是組織要員會議。
蘇洄本想和說自己被王教授選中寫論文的事,對他這樣一個頻繁休學的人來說,這很值得分。
但季亞楠這時候大概沒心思聽。
而且蘇洄很怕聚會,尤其是和那些大人的聚會,好幾次失誤令他下意識回避這些事。
Advertisement
“那媽媽你注意休息,我先回房間把包放下。”
“哎,等一下。”季亞楠住他,上下打量了一遍,“優優,最近都按時吃藥了吧?”
優優是他的小名,但蘇洄聽了并沒有覺得親昵。
“嗯。”蘇洄看向,語氣和,甚至帶著一點笑容,“媽媽,我現在的樣子應該還像個正常人吧。”
季亞楠臉上的表松弛些,“還行。我可先說好,從今天開始的每一天,你都必須給我好好吃藥,一頓不能。
你外公的生日聚會是大事,去的客人個個都是一把手二把手,要是出了問題,你這學期的課也不用上了,我給你請老師,就在家學,反正你高中也是這麼過的,也沒怎麼樣。”
蘇洄平靜地聽著,一點也不像個有神疾病的人,甚至很順從地點頭,沒有多說什麼。
“好。”
他膨脹的表達一點點消下去,就像放久了的汽水,氣泡一點點滅掉,沒了滋味。
“你別多想,媽媽是希你能正常去參加生日宴才這麼囑咐你的。”
季亞楠看到他沉默的樣子,又覺得有些可憐,于是走過去,將蘇洄攬在懷里,“媽媽就只有你一個孩子,外公也就你一個孫子,我還指你給外公切蛋糕呢,表現好一點,讓大家放心嘛。”
大家?
蘇洄很想知道,他們究竟什麼時候才愿意把他的病告訴其他人。
大概是不可能的,有哪個一把手二把手,愿意在老領導的生日宴上聽他宣布自己唯一的孫子是個神病患者呢。
“我會好好吃藥的。”蘇洄到悶,從季亞楠的懷里退出些許,“如果我狀態實在不好,你們就說我生病了,得了流,去不了。”
他不是第一次謊稱抱病逃離這種場合,多數時候都是他媽主說謊,為了不讓他給全家丟臉。
Advertisement
“那不行,這是重要場合,你可不能狀態不好。”季亞楠有些自顧自地說,“哦對了,你徐叔叔還幫你找了一位特別知名的心理學專家,他也是臨床醫生,專門研究雙相的。徐叔叔打過招呼了,明天就可以帶你去專家那兒咨詢,都說很有幫助的,說不定這次能治愈呢。”
蘇洄點了點頭,穿過沉悶而空曠的客廳,一言不發。
從十四歲開始,到現在也有五年了。
一次次地接近希,一次次復發,他已經對治愈不抱希。
推開客廳一角的玻璃門,蘇洄走進后花園,繞過一條草木環繞的鵝卵石路,來到自己的房間。
他站在外面了鞋,移開玻璃門,赤腳走進去。房間里被收拾得很干凈,沒有任何危險品,被認定“對他有害”的東西也全部被擅自清除出去,包括他新買的一些書,蘇洄甚至連翻一翻也來不及。
玻璃門外,花園里的無盡夏開了,大片大片的藍在綠意里起伏。蟬鳴四溢,充沛。但蘇洄到不過氣。
他試圖將上的負擔全部卸下,重重的書包,皮的上,都扔在地板。面對鏡子,蘇洄盯了一會兒自己凸起的肋骨,抬手,肋骨下方淺的疤痕。
約可以看見,心臟正抵著那層薄薄的皮和,小幅度跳著。
這是他活著的證明。
愣神間,手機震的聲音傳來,打破蟬鳴,但很短促,很快就消失了。
蘇洄到奇怪,蹲下來,從包里翻找出手機,打開一看,的確有一個未接來電,是陌生號碼。
眼前沒來由地浮現出寧一宵坐在長椅上的樣子,他上下浮的結。
蘇洄握著手機走了兩步,重重倒在床上,又滾了半圈,把臉埋在的被子里,撥回了電話。
電流聲刺激著他的心,一聲一聲響著,大約過了十幾秒那頭才接通,一個聲音出現。
“蘇洄?”電話里,寧一宵的聲音比面對面時更低沉些,那頭還有一個小男生的聲音,正說著“寧老師這一題我不太懂”。
聲音移遠了,蘇洄聽到寧一宵說等一下,讓小男生先做題,最后才對他開口,又一次了他的名字。
“嗯。”蘇洄的聲音隔著電波信號與棉被,用有些黏糊的語氣了他的名字,“寧一宵。”
電話那頭的人靜了一會兒。
似乎找到了一個較為安靜的地方,寧一宵的聲音比之前大了一些,也清晰許多,“我打電話給你,是想找你要今天王老師說的那篇文獻,他說你有,不過撥過去之后我發現可以下載到,所以就掛……”
“寧一宵。”
蘇洄又一次了他的名字,打斷了這些解釋。
“嗯?”
蘇洄趴在棉被里,同時到窒息和安全。
“你有沒有很想逃走的時候?”
這句話令寧一宵有一瞬間的恍惚,想起些不太好的回憶。
有想逃走的時候嗎?很多。
明明補課學生家的臺,可他卻突然嗅到海水淡淡的腥味。
在某個瞬間,寧一宵仿佛又變了那個無助的孩子,困在小漁村的日與夜里,走在路上都會被幾個年長幾歲的男孩兒圍堵起來,推搡他,用“野種”或是更難聽的稱呼辱他。
當時的他別無選擇,一個人的拳頭打不過一群人,逃不出那個地方,只能帶著一臉的傷回到家,看著母親抱著自己哭。
蘇洄很有耐心,沒催促他,是寧一宵自己從回憶里走出來的。
“有。”他難得誠實,而不是偽裝一個的、沒有傷口的人。
電話那頭的蘇洄像是深吸了一口氣,停頓了幾秒,聲音還是悶在被子里,聽上去又虛無縹緲,也沒有邏輯。
“我們能逃到哪里去呢?”
蘇洄隨時會說出一些奇怪的話,對于這一點,寧一宵以為自己已經習慣了,可聽到他嘆著氣說“我們”,心還是了。
“我覺得我像一只螞蟻。”
在寧一宵還愣神的時候,蘇洄又跳轉了下一句話,“被關在玻璃罩里的螞蟻。只要我好好地待在里面,就很安全,可一旦我想要出去,爬到玻璃罩的邊緣,人類的手指就會摁在我的上,我不了。”
像是一種很奇異的心靈應,寧一宵過這通電話,竟然到他的苦悶與沮喪。
他是個完全不會安他人的人,缺乏共力,只是很會藏,但這一刻,寧一宵竟然產生了想要安蘇洄的念頭。
蘇洄的聲音很輕,“我不想做一只被飼養的螞蟻。”
哪怕他知道自己的人生不會有太幸福的過程,也不會有多麼完滿的結果。但至要自由,哪怕是痛苦的自由。
“你不是。”掙扎過后,寧一宵還是開了口,“你不是螞蟻。”
他是個完全不懂得如何安人的人,也認為安是世界上最無用的事。寧一宵只做有價值的事,只做對自己的未來和前途有幫助的事。除非有益于他的前進,否則,他不會被任何人的所影響。
可是,現在的自己在做什麼。寧一宵也不懂。
似乎也覺得這樣有些荒唐,僅僅一句否定也顯得很沒道理。所以他又加以解釋,“我是說,雖然我不太清楚你發生了什麼,但總有一天,你會擺這些。”
電話那頭靜了好一會兒。
他不由得想,自己說的話是不是聽上去很無力,沒有任何幫助。
但這些也是他賴以生存的東西。
電話那頭忽然傳來笑聲,接著,是蘇洄很輕、又帶著笑意的聲音。
“寧一宵,你是玻璃罩外面的螞蟻。”
猜你喜歡
-
完結205 章
沖喜[重生]
[CP:溫柔大美人受x鐵血狠辣戰神攻] 國公府不受寵的嫡子葉云亭,被一道圣旨賜婚給了永安王李鳳岐當王妃。 永安王鎮守北疆,殺敵無數,是當之無愧的北昭戰神。 然而葉云亭嫁過去的時候,戰神已經身中劇毒,經脈寸斷,只能躺在床上茍延殘喘。 葉云亭心如死灰嫁過去,因懼怕戰神兇名,躲在自己的院子里得過且過。沒過多久,他因誤喝了給永安王的毒湯,就此命喪黃泉。 臨死前,那個據說快死了的永安王半跪在他床前,握著他的手鄭重承諾:“你因我而喪命,從今往后,我會竭我所能庇護你的親人,你安心去吧。” 后來他登基為帝,果然踐諾,庇護了他唯一的親人。 重來一世,葉云亭還是躲不過給永安王沖喜的命運。但這一次,他決定好好照顧這個奄奄一息的男人,報他前世恩情。 卻不料男人解毒后急不可耐拉著他要圓房。 他被男人緊緊摟在懷里,溫熱呼吸打在耳畔:“安心跟著我,從今往后,我護著你。” ★食用指南★ 1.1v1小甜餅,兩輩子攻受都只有彼此。 2..依舊老梗開局,雷的別看,作者就好這口,不喜歡請及時止損,不要互相折磨了真的。 3.朝代背景雜糅,私設如山,請勿考據哦。 4.完結甜餅,專欄可看:《暴君的寵后》《你不許兇我》《我們妖怪不許單身》 內容標簽:宮廷侯爵 重生 甜文 爽文 搜索關鍵字:主角:葉云亭,李鳳歧┃配角:韓蟬,李蹤,季廉……┃其它: 一句話簡介:從今往后,我護著你。 立意:身處逆境亦不忘堅守本心。
47.4萬字8 30029 -
完結170 章

殘疾戰神嫁我為妾后
野史記,大樑戰神霍無咎曾為敵國所俘,被斷經脈,廢雙腿,囚於大獄。那昏君為了羞辱他,還將他賞給了自己的斷袖皇弟為妾。 霍將軍受盡屈辱,臥薪嘗膽三載,後金蟬脫殼,潛回大樑。治愈腿疾後,他率軍三個月攻入敵國都城,殺其君王,焚其國都,最終將那廢物斷袖的頭顱斬下,在城牆上懸了整整三年。 自此,天下一統。 —— 某高校歷史系導師江隨舟,收到了一篇以霍無咎的野史為根據寫的畢業論文,將學生批評了一番。 再睜眼,他穿成了野史中的那個斷袖王爺。 四下里張燈結彩,下人來報,說敵國那個殘廢將軍已由花轎抬進王府了。 面對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穿著大紅嫁衣,目光陰鷙的霍將軍,江隨舟這才知道,野史也會成真的。 還會讓他被梟首示眾,腦袋在城牆上頭掛上三年。 江隨舟只好將霍將軍好生供著。 朝中明槍暗箭,昏君百般羞辱,他都咬牙替他擋下,只求三年之後,他能留自己一顆腦袋。 更不敢真讓這位身長九尺的“侍妾”伺候他。 可是未滿三年,霍將軍的腿竟然自己好了。 不光殺了昏君,統一了天下,還強行將他堵在房中,硬要儘自己“侍妾”的本分。
39.3萬字8 21049 -
完結148 章

我死后,成了渣A前夫的白月光
“杭景,離婚吧!”“我們的婚姻從一開始就是個錯誤!”杭景唯一一次主動去爭取的,就是他和宗應的婚姻。可宗應不愛他,所謂的夫夫恩愛全是假象,三年來只有冷漠、無視、各種言語的侮辱和粗暴的對待。只因為宗應不喜歡omega,他從一開始想娶的人就不是杭景,而是beta林語抒。從結婚證被換成離婚證,杭景從眾人艷羨的omega淪為下堂夫,最后成為墓碑上的一張照片,還不到五年。杭景死了,死于難產。臨死前他想,如果他不是一個omega而是beta,宗應會不會對他稍微好一點。后來,杭景重生了,他成了一個alpha…..更離奇的是,改頭換面的杭景意外得知,宗應心里有個念念不忘的白月光,是他一年前英年早逝的前夫。因為那個前夫,宗應決意終生不再娶。杭景:???宗先生,說好的非林語抒不娶呢?我人都死了,亂加什麼戲! 下跪姿勢很標準的追妻火葬場,前期虐受,后期虐攻,酸甜爽文。 完結文:《我養的渣攻人設崩了》同系列完結文:《[ABO]大佬學霸拒婚軟心校草之后》
40.6萬字8 13391 -
完結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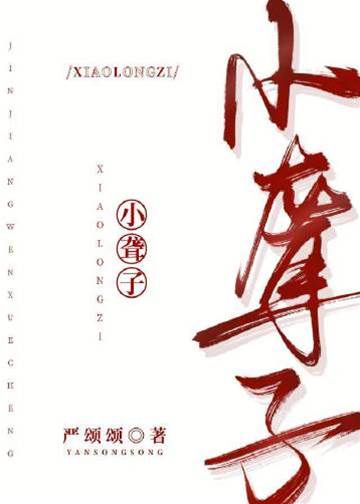
小聾子受決定擺爛任寵
憑一己之力把狗血虐文走成瑪麗蘇甜寵的霸總攻X聽不見就當沒發生活一天算一天小聾子受紀阮穿進一本古早狗血虐文里,成了和攻協議結婚被虐身虐心八百遍的小可憐受。他檢查了下自己——聽障,體弱多病,還無家可歸。很好,紀阮靠回病床,不舒服,躺會兒再說。一…
30萬字8.18 182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