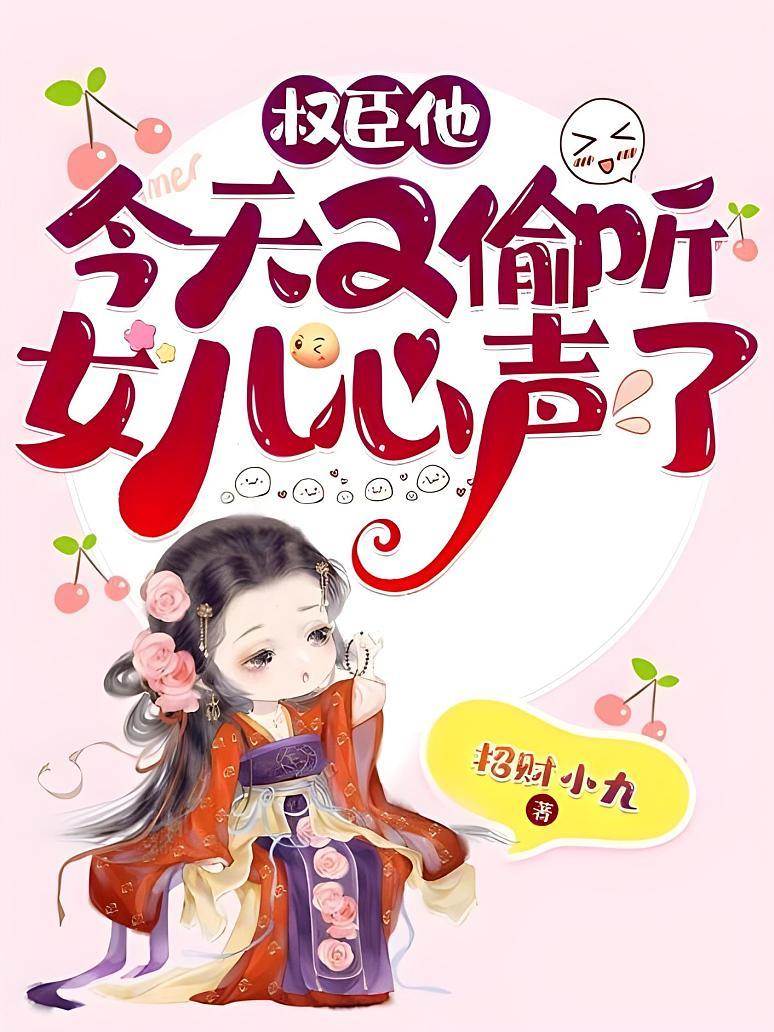《霸王與嬌花》 22
沈令蓁疑地拿著那幅字去了霍留行的院子,還沒進門,恰見他搖著椅出來。
兩人這幾日談不多,乍一當面還有些不適應。
沈令蓁是因到霍留行近來的疏遠,心底揪著小疙瘩;而霍留行呢,是因此前好一陣子,兩人都在椅上平起平坐,如今沈令蓁腳好了,居高臨下之中似著一興師問罪的味道,他心中生出了不好的預。
如此一來,兩人竟是隔著一道月門齊齊頓住,相對無言了。
霍留行微瞇起眼,打量一眼手中的件,當先開口:“這是?”
“哦,”沈令蓁回過神,將手中宣紙展開,“這是郎君題的詩吧?”
霍留行目一凝,轉瞬又恢復泰然,不答反問:“哪來的?”
“妙靈從大姑娘房里拿來的。”
霍留行后,空青和京墨呼吸一窒。
這幅字應當是郎君幾年前的手筆了,因本是隨而書,并非見不得的件,他們從前未曾太過留意它的去向,究竟是何時被大姑娘拿走收藏起來的,倒真沒了印象。
只是看眼下的形勢,郎君恐怕不得不認下這手字了。
霍留行的手指在椅的木扶手上挲幾下,默了默道:“是我的不錯。”
沈令蓁眉頭蹙起:“這就怪了,雖都是行楷,可我分明記得當初那塊帕子上的字跡跟郎君這手筆一點也不一樣。郎君上回不是與我說,那是你的字跡嗎?”
霍留行維持到此刻的坦然之微微現出了松,輕輕咬了咬牙。
佩劍與他一樣,疤痕與他一樣,連武功招式也與他一樣,這不該一樣的全一樣了,怎麼該一樣的卻不按路數來?
空青與京墨也膽戰地眼觀鼻鼻觀心。
然后,他們聽見霍留行大不解地“嘶”了一聲:“怎麼不一樣?那塊帕子上就是我這字跡。”
Advertisement
“不是。”沈令蓁肯定道,“郎君,我從小記憶力過人,絕不會記錯。”
“哦,”霍留行面遲疑之,“難道我們所見并非同一塊帕子?要不這樣,你把你記得的字跡描給我看看。”
空青對自家郎君不撞南墻不回頭的無賴神到由衷欽佩。只是夫人平常看著沒什麼脾氣,認起死理來卻也犟得很,這事即便遮掩得了一時,怕也遮掩不了一世。
沈令蓁為難道:“我所見那手行楷筆勢剛健,飄若游云,矯如驚龍,以我之能實難寫。”
霍留行嘆了口氣,向后叱責:“這麼件小事,給了你們多期日,到現在也沒查出究竟,還夫人在這兒勞神?”
京墨配合地埋下頭去:“小人無能,請郎君責罰。”
沈令蓁一聽“責罰”二字就記起好端端挨了十鞭子的霍舒儀,想霍家人起手來當真要命,趕勸道:“我不勞神,不勞神的,只是巧發現不對勁,才順來問一問郎君。”
霍留行皺著眉頭思索片刻,推測道:“按你如今提供的線索,這帕子從我手里到你手里,中途興許曾被人調換也未可知。此事從頭到尾著古怪,我暫時也理不出頭緒,不如讓京墨按新思路再去查查。”
沈令蓁心中有些狐疑,可見他這模樣又不像說謊,思忖半晌點點頭,想也只能這樣了。
說:“如此,郎君若是有可靠的人手,不妨去國公府取一趟帕子,有了實,這其中的困興許便可迎刃而解了。”
霍留行笑了笑:“我倒是有人手,只怕長公主不愿將它給我。”
“這個簡單。到時郎君的人替我捎一句口信,阿娘聽了,自然會明白。”
此事正中霍留行下懷。
Advertisement
他點頭應下,見還未打消疑慮,一副有話要問的樣子,突然回頭道:“前些天你去辦的事,辦好了嗎?”
空青一愣之下恍然大悟,連連點頭,對沈令蓁說:“郎君說,夫人這些天吃了不苦,他歉疚非常,無面對您,小人去置辦些您喜歡的吃食來討好討好您!今早這吃食已經送到了!”
“……”霍留行冷冷瞥了眼空青。他當時好像不是這麼說的吧,這可不止是添油加醋,而是顛倒黑白了。
空青眨眨眼睛,自覺用心良苦,一則轉移夫人當下的注意力,二則也給分房好幾日的兩人當了一回和事老。
沈令蓁細細回味了一下空青的話,再看霍留行這個“你多什麼”的表,明白過來,笑道:“原來郎君這幾天對我不理不睬,是因為那日嚇著了我,自覺歉疚無呀?”
霍留行看著這喜笑開,霾盡散的模樣,皺了皺眉頭,沒有說話。
空青急了,替他解釋:“夫人,您就別為難郎君了,郎君這是不好意思承認呢。”
沈令蓁連“哦”兩聲:“那我不為難郎君。”又問空青,“你方才說,今早送到了什麼?”
“荔枝,新鮮的荔枝,從南邊快馬加鞭運來的!還有一些荔枝做的吃食——荔枝糕,荔枝酒!小人一會兒就給您送過去!”
沈令蓁點點頭,眼看霍留行似乎因為被人揭了心事不自在著,便十分善人意地告了辭,笑著看他一眼:“那我就回去等著吃荔枝啦。”
霍留行目送離開,一聲不吭地轉頭回了院子。
等四下沒了人,空青惆悵天:“京墨,你說郎君和夫人可怎生是好啊?”
京墨瞥瞥他:“杞人憂天什麼?總歸眼下蒙在鼓里的是夫人,主權還在郎君手里。”
Advertisement
“你說你,分析起謀謀來頭頭是道的,上這種事就不如我看得清楚了。”空青長嘆一口氣,“我問你,假如我現在告訴你,不要去想荔枝長什麼樣,你腦袋里在想什麼?”
“……”京墨低咳一聲,“荔枝的樣子。”
“是吧?那同理,假如郎君不停告訴自己,別把夫人當回事,結果會怎麼樣呢?”
京墨無言以對了。
“你看方才,我給郎君搭了個臺階,換作以前他必然順勢下了,如今卻不肯拿那些甜言語去哄騙夫人,這是為何?你再看,郎君這幾天不須應付夫人,本該樂得輕松,但看著卻反倒心事重重,這又是為何?”
不等京墨答,空青已一錘定音:“但凡需要有意疏遠,有意放狠話,才能不當回事,就說明這事啊,懸了。”
——
當夜,霍留行照舊睡在自己的院子。
空青有心勸他,可眼看他那風雨來的臉,又不敢開口,只好默默伺候他歇下。
卻不料到了熄燭的時辰,京墨匆匆來了,說院鬧出了古怪的靜,他打聽了下,聽說是夫人吃醉了酒。
霍留行皺了皺眉,從床榻上起來:“誰給吃的酒?”
空青撓撓頭:“難道是今早的荔枝酒?”
“不是說新鮮荔枝嗎?怎麼又了荔枝酒?”
“是有新鮮荔枝,也有荔枝糕和荔枝酒。”
霍留行搖搖頭,拿手虛虛點點他:“喝不了酒。”
空青一噎,心道他也不知道啊,而且今早他說這話時,郎君分明就在一旁,也不知魂游到哪兒去了。
霍留行披下榻,去了沈令蓁的院子,一進臥房就見蒹葭與白圍著,披散著一頭烏發坐在床榻邊,一雙腳丫子踢踏踢踏晃著,里咕噥:“我不睡,我不睡……”
Advertisement
蒹葭和白聽見后靜,向他行了個禮,解釋道:“姑爺,是婢子們失職,夫人一時貪,吃多了荔枝酒。”說著又回頭去攙沈令蓁,讓躺下。
沈令蓁揮揮手,不要們照料:“你們摁疼我了……”
兩人不好對真格,慌忙收手,一時有些難辦。
霍留行看看酡紅的臉,搖著椅上前:“下去吧,我來。”
蒹葭與白猶豫了下,頷首退了出去。
沈令蓁沒了鉗制,舒坦了,又要跳下床榻。
霍留行站起來,一把架住了的咯吱窩:“大半夜不睡覺,做什麼去?”
像是這時候才發現屋里來了人,歪著腦袋,迷迷瞪瞪地瞅了他半天:“阿爹……你胡子呢?”
“……”這是一醉回到出嫁前,還以為自己在國公府呢?
霍留行好笑道:“我不是你阿爹。”
“阿爹胡說什麼呢?”沈令蓁奇怪地看著他,抬手去挲他的下,“不過阿爹的胡子去哪兒了?”
他兩只手都用來架胳膊了,騰不出空攔,只得偏頭去躲。沈令蓁不依不饒地追著又又。
“鬧什麼!”霍留行恨恨道,“我不是你阿爹,這兒也不是國公府,你已經嫁人了。”
沈令蓁被他吼得一駭,垂下手來,轉眼就來了哭腔:“阿爹不要我了,阿爹要把我嫁出去……”
霍留行一滯,松開了的胳膊:“我……”
沈令蓁吸吸鼻子,自己爬回了床榻,趴在枕上搭搭:“阿爹走吧,我要睡覺了,我會聽話嫁給那個大老的……”
“……”
霍留行掉頭想走,邁出去一步又停住,回頭把拎起來,咬著牙質問道:“你說誰是大老?”
沈令蓁一愣:“當然是霍……咦,霍什麼來著?”
連他名字都忘了是吧。
霍留行吸了口氣:“他霍留行。”
“哦,對!”沈令蓁咯咯笑起來,笑完又哭喪著臉道,“阿爹,我一定要嫁給他嗎?”
霍留行似乎也沒意識到自己默認了這當爹的份,問道:“你不想嫁?”
“我當然不想嫁。”耷拉著角,“我跟阿爹說,我愿意嫁,都是騙阿爹的,我怕阿爹為我去找皇舅舅出頭……”
霍留行拎著的那只手松了松,閉上眼嘆出一口氣。
再睜開時,他的眼底多了幾分確定。
他問:“你喜不喜歡你皇舅舅?”
“皇舅舅以前對我還是好的……可是這次,我不喜歡他……”
“那要是以后,我去幫你出頭,你會站在我這邊,還是站在你皇舅舅那邊?”
沈令蓁一把捂住他的:“阿爹別犯傻,阿爹怎麼敢跟皇舅舅作對?”
他笑著垂眼看:“這天底下,沒有我不敢做的事。”
擱下手,拼命搖頭:“不行,不行的……我還是嫁人好了,萬一那個霍……霍留行長得還不錯呢?”
霍留行揚揚眉:“他就長我這樣,你看這算不算不錯?”
沈令蓁瞇起眼來瞅他,點點頭:“跟阿爹長得一樣,那當然是很不錯了!”說著又愁眉苦臉起來,“不過他會不會中看不中用呀?”
霍留行一個板栗輕輕敲下去:“你說誰不中用?”
沈令蓁“嗷”地抱住了腦袋,躲去床角,警惕地看著他:“不對,不對,阿爹從來不打我的,你不是我阿爹!”
霍留行跟著上榻,把堵在了床角:“現在才發現引狼室,是不是晚了些?”
眼看他越越近,沈令蓁拿手擋在前,使勁往后:“……你是誰?”
“我是你夫君。”
“芙菌是什麼?吃的嗎?”
“想吃我?你膽子不小。”
沈令蓁搖搖頭:“我膽子很小,我要睡覺了……”一個激靈從霍留行咯吱窩底下鉆出去,正要拿被衾將自己兜頭護住,卻被一把拽了回去。
霍留行拽著胳膊,忽然問:“這世間的法則——螳螂吃蟬,黃雀吃螳螂,鷹吃黃雀,那你知道誰可以吃鷹嗎?”
沈令蓁呆滯地搖搖頭。
“沒有誰可以吃鷹。鷹是沒有天敵的。”他著窗外霧沉沉的夜,似將目投放到了很遠的地方,“他們當我是蟬,我卻要做鷹。”
沈令蓁愣了愣:“……那是什麼意思?”
霍留行垂眼看著,大約十個數,或者二十個數。然后他終于在數日的思慮考量后,得出了一個決定。
“意思是,這場仗,我有把握打贏。從今往后,誰欠的債,我找誰去討,只要你乖乖跟著我,不背叛我,我就護你周全。”
沈令蓁懵懵懂懂地看著他,眨眨困倦的眼,打出個酒嗝來:“啊?”
霍留行一把住的下,黑著臉問:“啊什麼啊,我在問你,以后要不要跟著我?”
猜你喜歡
-
完結1669 章
溺宠神医狂后
她,秦家嫡女,生母遭人暗算而亡,被迫離家十數載。一朝歸來,她發誓,定要查明母親死因,讓害死母親之人付出泣血代價爹爹不親,祖母不愛,繼母狠毒,姐妹兄弟各個不是省油的燈。而她,絕不像娘親那般懦弱她手握上古單方,身懷絕世武功。正麵剛一招送你上西天玩下藥千萬毒藥任你選隻是,回家路上不小心撿的這個男人竟是當今聖上可他為什麼有事沒事總大半夜往她的閨房跑夜幕之中,他的眸閃閃發亮,“你我早已共浴,你也看過我的身子,自然要對我負責”秦若曦無力扶額,撿個皇上做夫君好像也不錯。皇上說“我家皇後身纖體弱,心思單純,誰都不許欺負她。”那被打到滿地找牙的京中小姐滿臉淚痕,到底是誰欺負誰皇上又說“我家皇後淡泊名利,心性善良,大家都該學習。”皇後孃孃的專用“會計”嘴角抽搐,“皇上,您家皇後的錢比國庫都要多了。”皇上臉色瞬變,“胡說國庫的錢也是皇後的”
317萬字8 16827 -
完結1256 章

絕世醫妃
現代超級學霸風雲菱,醫毒雙絕。一朝穿越,感受很強烈。一針就讓渣男王爺軟弱無力,耳刮子唰唰響,告禦狀,陰謀陽謀齊下,光明正大休夫!休夫後,大小姐風華萬千,亮瞎眾人狗眼!溫潤皇子表好感,渣男警告:“風雲菱是我的女人!”謫仙美男表愛慕,渣男:“她,我睡過了!”某女:“睡,睡你妹,再說讓你做不成男人。”某男:“那,做不成男人你還要嗎?”“滾……”
223.4萬字8.18 156267 -
連載689 章

萌妃駕到:王爺別亂來
聽說嗜血殺伐的冷酷王爺不近女色?非也,自從娶了將軍府的六小姐后就大變樣了。“妖妖她嬌小柔弱,不愛說話,一個人出門本王不放心。”發小汗顏!王妃棒打太子,手撕白蓮,毒舌起來能把死人氣活,還不放心?“妖妖她不懂兵法,醫術尚淺,你們不要欺負她。”敵…
129.2萬字8 20002 -
完結666 章
嫁權宦
元衡郡主的嫡女李清懿在魏府受盡欺辱,之后被魏府送給了當朝權勢滔天的宦官秦增當玩物。洞房花燭夜,她沒能等來權宦夫君就莫名其妙的死了,睜眼回到母親元衡郡主接她到魏府的那一日。面對魏府一干吃人的蛇蝎,李清懿恨的咬牙切齒!魏府二夫人想害她二叔入獄,她就把二夫人做的惡事一樣樣揭出來,看她惶惶不可終日,到死都不能解脫!魏府二姑娘誣她二嬸清白,她就讓對方嘗嘗身敗名裂,無路可退是什麼滋味!魏府老夫人圖謀李家家財,她就讓對方感受一下失去一切的痛苦!還有她那個城府極深的繼父魏世成,想做首輔?沒門!李清懿在魏府興風作浪,卻也沒忘記她的權宦夫君秦增,這一世,她必得先下手為強,免得將來他恢復身份,被人瘋搶!不過,為啥春風一度之后,這個宦官夫君好像沒有那麼冷了?
138.7萬字8.18 24140 -
完結3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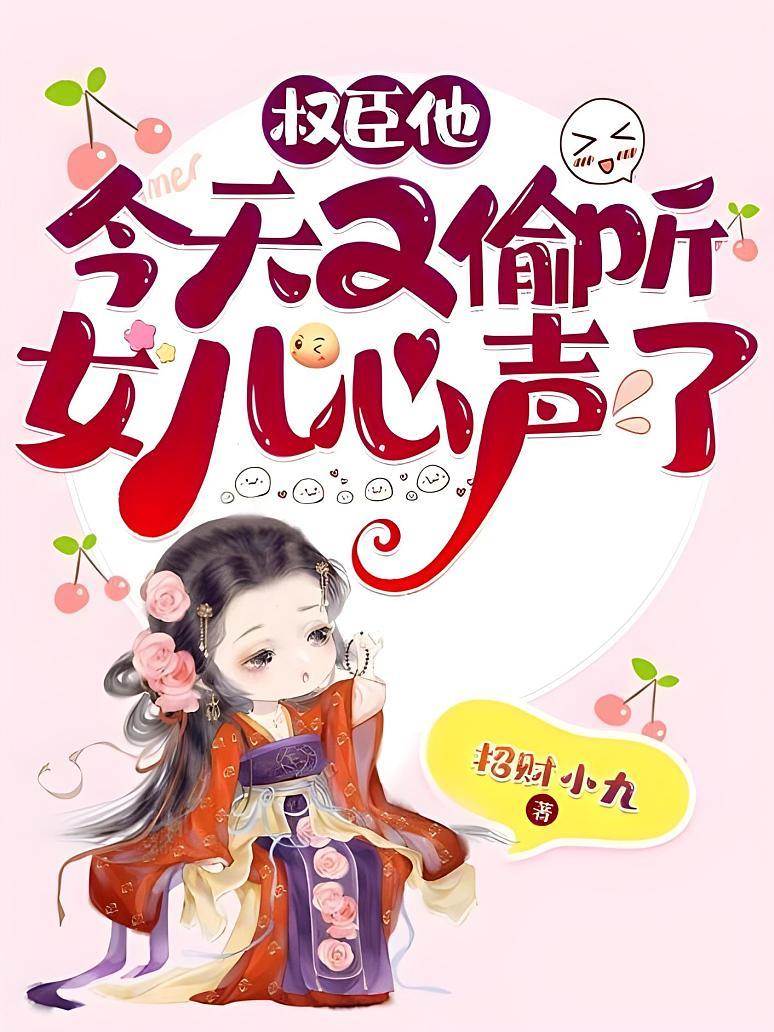
權臣他今天又偷聽女兒心聲了
樓茵茵本是一個天賦異稟的玄學大佬,誰知道倒霉催的被雷給劈了,再睜開眼,發現自己不僅穿書了,還特喵的穿成了一個剛出生的古代嬰兒! 還拿了給女主當墊腳石的炮灰劇本! 媽的!好想再死一死! 等等, 軟包子的美人娘親怎麼突然站起來了? 大奸臣爹爹你沒必要帶我去上班吧?真的沒必要! 還有我那幾位哥哥? 說好的調皮搗蛋做炮灰呢? 怎麼一個兩個的都開始發瘋圖強了? 樓茵茵心里犯嘀咕:不對勁,真的不對勁!我全家不會是重生的吧? 樓茵茵全家:重生是啥?茵茵寶貝又爆新詞兒了,快拿小本本記下來!
69.1萬字8 1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