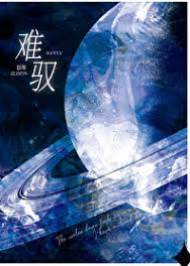《金牌律師Alpha和她的江醫生》 第 23 章 兩O相遇
撲面而來的百合香濃郁得散不開,江知意剛剛打完架還爬了樓梯,力氣消耗不,推了兩次愣是沒推開,看似纖瘦的秦蓁此刻因為發熱期發出不同尋常的能。
今天幸好是江知意在岑清伊家里,換了alpha,十個有九個必定扛不住。
現在是兩O相遇,都是坐其的躺贏類型,江知意作為頂級omega,雖然備一般omega不備反向標記的能力,但能讓有興趣反向標記的對象僅僅是針對alpha,而且這個alpha也只能限定為岑清伊。
江知意剛才歇了會力氣恢復些力氣,將人從上拽下來,順手將人推搡摁倒在沙發上起發檢查后頸的腺,接近完全蘇醒,正在接近被標記的巔峰時刻。
江知意不得不懷疑秦蓁的用心,明知發熱期來臨,不僅不采取措施,還跑來岑清伊家里。
秦蓁心本能的使得極力掙扎,江知意按著不放,高聲道:“秦蓁,你看清楚我是誰。”
秦蓁心思混但還能分清眼前的人不是岑清伊,因為沒有著迷的麝香味,之前迷離的眼神沒看清是誰,被提醒才瞪大眼睛,“你!”
發熱期的人本就狀態不穩,眼下氣急的秦蓁更是肝火大旺,明明人阮得不行,卻還是兇地嚷:“你怎麼那麼不要臉,誰讓你來的!”
眼下難的秦蓁其實無心聽江知意說什麼,是看到這個人就生氣,心里仿佛被誰支起一個火爐,燒得口難忍。
江知意無奈之下只能先去自己包里翻抑制劑,秦蓁太熱扯著自己的領,想要拽掉扣子。
江知意按著人抑制劑,作一點都不溫,秦蓁嗚嗚咽咽哭得好不可憐。
Advertisement
最無奈的是抑制劑發揮效果需要時間,而發熱期已經來臨的秦蓁大概等不到起效就會耐不住想盡辦法解決的難了。
江知意作為一名醫生,不得不采取極端的措施將人控制住,怕秦蓁在岑清伊做出有失統的事,拽下秦蓁服裝飾的腰帶,將人直接捆上了。
秦蓁正難,哪里得了這份委屈,剛要張抱怨,江知意直接塞里一條巾。
秦蓁淚眼汪汪地瞪著江知意,大有將卸八塊的敵意。
江知意忙活一汗,洗手出來,站在秦蓁面前,淡聲道:“過了這個勁兒,你會謝我。”
江知意抬手看看時間,一般Omega發熱期的巔峰在抑制劑的控制下,怎麼也得一個小時才能過了那個勁兒。
“等會給你助理打電話,讓過來接你。”江知意角的,轉去廚房準備洗菜,客廳里唔唔聲抗議,聽著聒噪將門關上。
江知意打開音樂放在廚臺上,世界果然妙了。
**
市中心堵了會車,岑清伊翻翻和江知意的聊天記錄,上上下下了幾個來回。
有的句子反反復復看幾遍,看到江知意說小嘮叨,角扯出一笑,笑完又覺得自己很傻。
紅燈倒計時,岑清伊忙放下手機,頭一次覺得等綠燈的時間好像變短了。
江城市興臺區,屬于老街區,從市中心開過去明顯能覺到周邊的建筑越來越老舊,樓層也越來越矮。
何家所在的位置是江城市原來的老汽貿城區,冬天黑得早,店鋪幾乎全關。
昏暗的老路燈一閃一閃,岑清伊深一腳淺一腳往狹窄的巷口走。
一陣寒風穿過,吹得岑清伊打冷戰,裹服呼口氣,白霧繚繞更顯冷。
Advertisement
地面凹凸不平,垃圾隨可見,岑清伊一不小心踢了個空易拉罐,刺耳的聲音傳出很遠。
這里安靜的過分啊,岑清伊四張,過窄窄的巷口終于看見何母口中所說的“何家小館”的小牌子,夜里瑩綠大字歪歪扭扭瞅著有點滲人。
臨出巷口,又是一陣寒風,裹挾著地面的垃圾吹過來,幾張方外圓的紙錢被風吹得著地面翻滾,其中一張到岑清伊的上了。
岑清伊抖了抖,紙錢向后飛去,這邊是死人了?
岑清伊想著,聽見前面突然傳來沙啞的嗓音,“岑律師嗎?”
“啊!”岑清伊應了聲,“是我。”
“快進來暖和下。”何母連忙迎過來,岑清伊跺跺腳上的雪,呼了口氣跟著何母往屋里走。
咣!岑清伊捂著腦袋倒退一步。
何母哎喲哎喲兩聲,“瞅瞅我,忘記提醒你了,我家這門有點矮。”邊說邊打量岑清伊,笑道:“你這孩子長得又俊又高。”
岑清伊嗡嗡的腦袋,何母倒杯熱水,“磕疼了吧?”
“沒事。”岑清伊笑了笑,接過水杯放到桌上,“阿姨,咱們先說正事吧。”
“噢噢。”剛坐下的何母立刻起,岑清伊擺擺手,“阿姨您坐,不用張。”
何母捋順耳邊的碎發,長嘆口氣,還未開口淚花已在眼底翻滾。
**
何母好幾天沒見到兒子了,之前秦川和安歌帶著去了解況也不讓見。
何母抹抹眼淚,從屜里翻出一個黑的手機,“這是我兒子的手機,現在沒電關機了,之前還沒關機,我翻了一下,無意中聽見我兒子和別人打電話的聲音。”
何母想說的其實是錄音,岑清伊查看手機充電口,安卓手機幾乎都通用的端口,“阿姨,您和叔叔的手機都是什麼樣的?”
Advertisement
阿姨知道岑清伊問的什麼,搖搖頭,“我和老伴的手機都是老式的。”
“那您的鄰居……”
“基本沒什麼鄰居了,”何母再度哽咽,抬手指指隔壁,“就隔壁樓一戶人家,還不太方便。”
“恩,那您說說,您都聽到什麼了?”岑清伊開著錄音,邊問邊記錄。
兩人聊了不到二十分鐘,岑清伊基本了解清楚,點點頭道:“行,那您兒子的手機,您是想暫時放在我這里保管?”
“恩,岑律師,您拿著,萬一有幫助。”何母站起,“您還沒吃飯吧,我還差個青菜沒炒。”
岑清伊哪能留下來吃飯,起告辭,何母留不住,只能送出去。
岑清伊站在門口才意識到一件事,何家離云盛集團要收購的那塊地僅僅隔著一條街。
何家左邊是何家小館,右邊是何家超市,眼下冷清得不見人。
“阿姨,這邊怎麼冷清啊?”岑清伊心中有所猜測,果不其然,何母抬手從左到右劃了條線,“這一片都要拆了,我們這邊基本也都搬走了,現在就剩下我家,還有旁邊這家,”何母揚了揚下,隔壁樓里傳來嗚咽哭聲,岑清伊聽著瘆得慌,“這家怎麼回事?”
何母又是長嘆一聲,低頭抹眼淚,哽咽道:“死人了。”
岑清伊回想起寒風吹起的紙錢,記憶倒流又想起前些天的,以為得了絕癥不久于人世……心中也不免生出悲戚,也跟著輕輕一嘆,“阿姨,您也別難過了,天怪冷的,您趕回去吧。”
“岑律師,我兒子就拜托你了。”何母雙手抖地抓著岑清伊,冰涼凍人,讓想起江知意寒涼的手,岑清伊點點頭,“恩,我會盡力的。”
**
岑清伊沿著巷口往回走,走出幾步回,何母還在著。
Advertisement
岑清伊揮揮手,“阿姨,快回去吧。”何母誒了一聲,這才轉走了。
岑清伊抬頭天,窄巷里的天似乎都是狹窄的,破舊歪扭的電線纏在一起。
昏黃的路燈映照在殷紅的磚墻上,一個白的大圈里寫了個拆字。
這一片也在拆遷范圍,現在不拆也只是時間問題,何家和隔壁的鄰居也是一樣,現在拖不搬走,拖到最后早晚都要搬走。
說到底,還是錢上出了問題。
拆遷款給的不滿意,加之對長久居住的地方有,何家不愿搬走。
一家小超市和小飯館,靠的是周邊的居民養活,現在大多人都搬走,兩個店面也快黃了。
岑清伊心口沉甸甸,新聞里每天都在說人均收提高了,但是窮人永遠都是大多數。
岑清伊預料到今天的面談會很快結束,但沒想到會這麼快結束戰斗,咕咕的肚子,想起還有一個人等回家吃熱氣騰騰的火鍋,心輕快不。
**
回家路上,岑清伊收到助理秦川的微信,他發了一張飯店牌子照片,寫了句:老大,我今晚要和大老板吃飯,有沒有需要特別注意的啊?
岑清伊正好等紅燈,語音回復:“也沒什麼特別的,就是點菜前提前問對方有沒有忌口,吃飯時別給人夾菜,可以敬酒但不要勸酒,敬酒杯沿要低于對方,不過我不建議你喝酒,作為律師,說話尤其注意,不要授人以柄……”
岑清伊發了一條接近60秒的語音,秦川:老大,你搞得我好張。
岑清伊又回了一句,“你這才剛開了解況就吃飯,誰提議的?”
秦川:我,嘿嘿,想著悉好辦事。
飯局已定,岑清伊也沒再多說。
臨近家門,岑清伊接到小紀的電話,掩不住的焦急,“岑律師,蓁姐在你那嗎?”
“沒啊,怎麼了?”
“沒、沒事。”小紀匆匆掛了電話,岑清伊察覺不對,發信息又問小紀:到底怎麼了?
小紀發來哭泣的表包:蓁姐的電話打不通,人也不見了,今天發熱期,我以為去找你了。
岑清伊打秦蓁電話,也是無法接通,安小紀:不是小孩子,應該沒事。
岑清伊發信息給秦蓁提醒看見信息回電話,上電梯后下意識兜,啊……鑰匙給江知意了。
岑清伊來回除去路上的時間,談事的時間不到20分鐘,回來那會不堵車,也就半個小時的車程。
岑清伊估計江知意正在吃火鍋,一想到火鍋的香氣,胃里的饞蟲都醒了,事實證明,江知意多買菜是正確的。
秦蓁會去哪?岑清伊出電梯,這個問題迎刃而解。
百合香依舊沒散開,岑清伊的饞蟲全部嚇跑,難以想象發熱期的秦蓁和暴脾氣的江知意在一起會怎麼樣。鄰居的門突然被推開,胖胖的眼鏡正從房里往外搬椅子,“岑律師,你家缺椅子不?送你了。”
“啊,不用。”岑清伊道謝,一眼瞟見門鎖著的鑰匙正是岑清伊曾經給秦蓁的那把,人果然是來了。
**
岑清伊無心和鄰居寒暄,開門后大吃一驚,一瞬以為是到了兇殺現場。
地上的跡猶如染料似的涂抹的到都是,茶幾被踹歪,茶幾上的果盤和杯子掉地,杯子碎了一地,水果滾得到都是。
秦蓁像是瀕死之人,阮著攤在跡里,岑清伊驚慌地抱起人,“秦蓁?”
秦蓁奄奄一息,“嗚~”
岑清伊拽掉秦蓁里的巾,秦蓁嗚嗚地哭,發熱期最難的那個勁兒剛過去,疲力盡,渾被撕裂得疼。
“救我~”秦蓁說完就止不住地哭,覺自己像是岸上的魚,因為缺水幾度產生死去的幻覺。
廚房的門這時開了,歡快的音樂傳來,江知意手里拎著菜刀,逆而站,表郁。
“你回來了。”江知意走近,秦蓁抖糠,似乎很怕江知意,無力地埋頭在岑清伊的懷里,呢喃道:“你、你別過來~”小音要多可憐有多可憐。
岑清伊一時怒火騰地上來,“是你把捆起來的?”
“是。”
“你怎麼能這樣?”岑清伊擰眉不悅,抑道:“你看看傷什麼樣子了?”
“那是自己弄傷的。”
“你不捆,怎麼會傷到?”岑清伊抱起渾哆嗦的秦蓁,江知意哼笑了一聲,“秦蓁,這是你的計劃嗎?”
秦蓁低聲嗚咽,沙啞地說:“我怕~伊伊~我怕~”
江知意拎著菜刀更近一步,問道:“我在問你話,秦蓁。”
“嗚~”秦蓁低聲啜泣,人幾近虛。
面對面而站,岑清伊看見江知意角破了,第一反應是兩個人或許之前手了。
江知意的手勁兒岑清伊很清楚,秦蓁一個普通的omega本抵擋不了。
岑清伊無奈地嘆口氣,低頭哄秦蓁,“你先別哭,我給你理傷口。”
岑清伊要繞過去卻被江知意攔住,蹙眉道:“讓開。”
江知意臉也徹底冷了,“你是醫生,我是醫生?”
岑清伊愣了下,江知意冷聲道:“把放下。”
“我不要~”不等岑清伊回答,秦蓁先拒絕了,“死也不要我~”
“放下。”江知意重申。
“不要。”秦蓁拒絕。
岑清伊:……
的人生可能TM就是一道送命選擇題。
猜你喜歡
-
完結49 章
黑白
他是至純的黑色,她是純淨清透的白。 從遇到她起,他就不曾打算放走她,這是一種執念。 哲學上這樣定義它,一個人過分專注於某事某物,長時間淪陷於某種情緒,這一情結就會成為有形,將之束縛住。而他,有執念,亦有將之執行的資本。 於是他終於出手,親手折斷了她的翅,從此把她禁在身邊。
13.8萬字8 8139 -
連載994 章
一夜驚婚夫人超有錢
五年前,蘇晚心識人不清,被最親近的人陷害出軌神秘陌生人,父親身死,送進精神病院,流言加身萬劫不複。五年後,她從國外攜萌寶歸來華麗變身,卻被孩子的便宜爹纏上,聽說本以為便宜爹身無分文,還要賣身接客賺錢?為了寶寶有個爹,蘇晚心豪擲三百萬,“彆工作了,你帶孩子,我養你,每個月三百萬。”突然被養的男人:???助理:“老闆,太太買房看上那棟三千萬的彆墅是我們開發的。”費總:打一折,送她!助理:太太說太便宜了,要再買十套!費總表示,十套彆墅,難道我送不起?房子隨便送,錢隨便花,都是他家的,肥水不流外人田!一夜驚婚夫人超有錢
96.6萬字8 178121 -
完結953 章

結婚後,殘疾大佬站起來了
被人陷害,她與他一夜荒唐,事後,她代替妹妹嫁給輪椅上的他。 都說傅家三爺是個殘廢,嫁過去就等於守活寡。 誰知她嫁過去不到三個月,竟當眾孕吐不止。 眾人:唐家這個大小姐不學無術,這孩子一定是她揹著三爺偷生的野種! 就在她被推向風口浪尖的時候,傅景梟突然從輪椅上站了起來,怒斥四方,“本人身體健康,以後誰再敢說我老婆一個不字,我就讓人割了他的舌頭!” 感動於他的鼎力相助,她主動提出離婚,“謝謝你幫我,但孩子不是你的,我把傅太太的位置還給你。” 他卻笑著將她摟進懷中,滿心滿眼都是寵溺,“老婆,你在說什麼傻話,我就是你孩子的親爸爸啊。”
96.6萬字8.18 118489 -
完結1725 章

夫人她是個小作精
醫院裏一場驚心設計的陰謀,季溫暖從豪門真千金,淪為了親爹不疼,親媽不愛的鄉下野丫頭。十九歲,親媽終於接她回家,隻為逼她把婚事讓給假千金妹妹。腦子一熱,季溫暖盯上了前未婚夫的小叔叔。眾人皆知,有權有錢又有顏的秦家四爺小的時候被綁架,受了傷,從此吃齋念佛,生人勿近。家財萬貫隨便花,還不用伺候,完美!“四爺,我看您麵若桃李,命犯爛桃花,隻有做我的男人,方能逢兇化吉。”某人眸色沉沉,“叫大叔,就答應你。”“大叔。”某天,季溫暖發現實際情況根本不是傳聞的那樣,她要分手!“不分手,我把錢都給你。”
162.5萬字8 98972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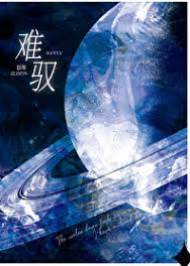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18 11698 -
完結202 章

暮夏婚約
顧念一在24歲這年同一個陌生人結婚,平靜的生活被打破。 彼時,她只知道陸今安是南城首屈一指的陸家長子,前途無量的外科醫生。 顧念一與陸今安的第一次見面是在民政局,他遲到了2個小時,矜貴清雋、棱角分明的面容中,盡顯疏冷。 婚後的兩人井水不犯河水,結婚證被陸今安隨意扔在抽屜裏。 某天,顧念一去醫院,無意間撞見矜貴落拓的男人與朋友在辦公室閒聊,被問及這樁突如其來的婚事時,陸今安淡漠開口:“不過是完成老人的囑託罷了。” 不繼承家族企業、不爲情所動的人,怎會上心婚姻。 — 婚後某日,顧念一在次臥獨自落淚,陸今安猶豫之後將她擁在懷裏,任由淚水打溼他的襯衫。 翌日,陸今安笨拙搜索如何安慰女生,奔波在全城尋找顧念一喜歡的玩偶的所有聯名款。 朋友控訴,“怎麼哄老婆了,這是上了心?” 陸今安腳步一頓,眸色深沉,“不想她哭。” 後來,一場百年一遇超強降雨襲擊南城。 外出採集信息的顧念一被暴風雨困住,與外界失去聯繫。 推開她面前擋板的是陸今安。 顧念一第一次見到陸今安狼狽的樣子,單薄的襯衫被雨水打溼,手指骨節處帶着斑駁血跡。 一步一步走近她,溫柔地說:“老婆,抱抱。”
28.3萬字8 940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