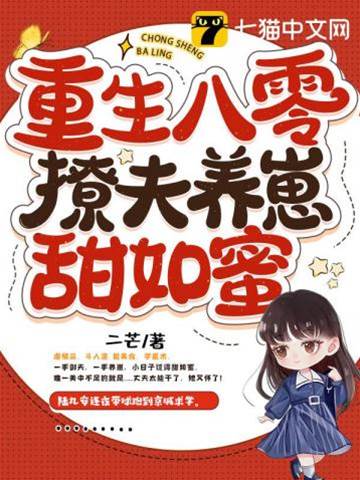《在冷漠的他懷裏撒個嬌》 第22章 不用怕
姚武組的局,他卻不需要親自上陣,而是請了人幫他比賽。
見麵的地點是在回虎山半山腰的斷崖邊,蕭瑟的山風呼嘯著,回在峽穀裏宛若百鬼哭嚎。
謝隨從車裏走出來,遙遙地見姚武幾人不耐煩地倚靠在車邊,已經等候多時了。
“謝隨,遲到了啊。”
謝隨漫不經心道:“又他媽不是上課,還管遲到不遲到?”
姚武吃了一癟,訕訕地:“既然是我約的局,那就由我來定規矩,沒意見吧。”
“隨便。”
姚武和周圍幾個男孩換了眼神,道:“玩速度你是專業的,今我們換個花樣玩玩。”
“你想玩什麽?”
“玩命。”
姚武回頭招招手,車邊,一個穿著白的賽車服,脖頸邊有紋的男人走了出來。
“看到前麵的懸崖了,就往那兒開,速度不能低於80碼,誰他媽先停,算誰輸;相反,到最後誰越靠前,誰贏。”
此言一出,叢喻舟臉變了變,不過他還是沒有怯,衝姚武道:“行啊,我們隨哥陪你玩命,你他媽也該拿出點誠意來,親上陣啊,請人玩算幾個意思。”
姚武道:“咱們之前好了,我約的局,規矩也是我來定,能玩就玩,不能玩就他媽乖乖給老子道歉。”
“你定規矩也不能瞎定吧”叢喻舟還想什麽,謝隨回頭的眼神止住了他。
“行,就按你的規矩來。”
姚武眼角出狡詐的笑意,覺得這次他媽總算能把謝隨囂張的氣焰按下去了,他花了大數目請人來比這個局,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他很有信心能贏謝隨。
謝隨二話沒,上了車。
姚武拿出手機準備錄視頻,同時也沒忘叮囑他雇的紋男:“給我往死了開,越往後,錢越多,拖死他。”
紋男點了點頭,看樣子也是下了決心,要錢不要命。
Advertisement
叢喻舟實在不放心,拉開副駕駛的門準備坐進去。
謝隨卻提前一步鎖了門。
“隨哥,我跟你一起。”
“不用。”
“隨哥!”
謝隨偏頭向他,黑漆漆的眸子裏暗流湧:“你站在邊上看就好,下次帶你,乖。”
“”
謝隨越是認真的時候,就越是喜歡用輕浮這樣的口吻話。
叢喻舟願意跟他,他心裏是的,但這是他的局,也是他的命,更是他無可遁逃的人生,他避無可避,隻能麵對,但毋須拉別人下水。
姚武走到了馬路中間,拿著手機對著兩輛賽車,拍下特寫鏡頭,嚷嚷道:“開始了!走!”
謝隨啟引擎之後,方向盤一歪,朝著姚武撞了過去,姚武嚇得魂飛魄散,張牙舞抓地著:“你幹什麽!”
然而謝隨隻不過和他開個玩笑而已,在他邊繞了個彎,駛了出去,但姚武卻差點嚇尿了。
蔣仲寧叢喻舟等人笑了起來:“就這點膽子,你他媽還跟我們隨哥玩命呢。”
姚武了幾句口,眼角顯出戾氣,心待會兒有你好看的。
公路的盡頭是一道九十度直角的轉彎,且這段路護欄缺損,很多車經過此地都會放慢速度,以確保不會因為巨大慣而跌落山崖,即便是最優秀的賽車手,也不敢在這條路上無所顧忌地開車。
但今,玩的就是心跳。
謝隨將車速控製在八十碼,而紋男也將車保持與他並行,甚至要慢上幾碼。
謝隨過車窗了他,他衝謝隨咧一笑,看樣子是要死拖著他了。
謝隨稍稍踩了一腳油門,將距離拉開,而紋男眼見著便要落後於他了。規則的是最後誰越靠前,誰贏,因此一味地放慢速度也不行,姚武看著有些急了,拿著對講機大喊:“跟上去!追上他!”
Advertisement
紋男沒辦法,隻能跟著一腳油門踩下去,追上了謝隨。
謝隨的速度已經加到了九十碼,極速奔馳在那條筆直險峻的公路之上。
紋男臉上的笑容漸漸消失了,眉心簇,隻能全力追著他,卻又不敢加快速度超過他。
姚武拿著遠鏡,遠遠的看著兩輛並行疾馳的跑車,眼見著懸崖近在咫尺,而謝隨毫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最後一百米、五十米、二十米……
紋男已經有些怯,他本能地點住了剎車,可是對講機裏姚武刺耳的聲音傳來:“今要是輸了,你他媽一分錢都別想拿到,他停下之前,你不準停!”
紋男想著姚武給他開的高價,他狠了狠心,終於還是踩下油門,追上了謝隨。
眼看著公路彎道的懸崖已經近在咫尺,謝隨的目平視正前方,漆黑的眸子波瀾不驚,他依舊沒有減速。
紋男時而看看他,又看看前麵咫尺之距的深淵,心跳加速,全的沸騰洶湧。
二十米、十米、五米……
他終於不了這種刺激的挑戰,猛地大了一聲,一腳踩下了剎車!
胎與公路劃出一道尖銳的“嗞拉”聲,而在他停下來的下一秒,謝隨也踩下剎車。
他前麵的公路已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深不見底的懸崖,繚繞著白霧,車已經有三分之一駛出了斷崖!
叢喻舟和蔣仲寧懸著的一顆心驟然放鬆,大罵著謝隨他媽的不要命了,衝過去將他從車裏拉出來,推搡著他,也擁抱著他,張激的心難以平複。
紋男的車頭與謝隨的車尾差了約莫兩米的距離,他從車裏下來,全的力氣仿佛是被空一般,撐著車,差點他媽的吐了!
姚武跑過來,難以置信看著謝隨駛出懸崖三分之一的車,無話可。
Advertisement
麵前的謝隨,那冷峻的眉弓之下,深邃的眸子裏凝結著死亡的氣息。
亡命之徒。
他回頭罵了紋男幾句,便讓手底下的人開著車離開了。筆趣閣V首發biqugevbiqugev
他和謝隨的賭約很多人都知道,腦門上的傷算是白捱了,不僅如此,他還要申請轉班,並且以後在學校裏看見謝隨,避著走。
經過這次事件,姚武也清楚地認識到,謝隨那樣不要命的家夥,他是真的惹不起他。
從回虎山公路回來的路上,蔣仲寧開車,叢喻舟坐在副駕駛,而謝隨一個人坐在車後座,沉默著,一直沒有話。
叢喻舟過後視鏡向他。
他的手撐著闊的額,臉沉靜,飛速流過的路燈在他的臉上投下斑駁的影。
誰能真的不要命,剛才生死之際走一遭,他心裏應該也不平靜吧。
叢喻舟沒有打擾他。
謝隨終於出手機,撥出了一個號碼。
寂白手機響起來的時候,正在吃飯。
“喂。”
“請問是哪位?”
電話那端沒人吭聲,隻有風在呼嘯。
“喂?”
“我聽不見你話。”
“咦?”
孩的聲音就像溫的棉花糖,黏黏的,穿過他的耳,震著他孤獨的心靈。
他也不知道為什麽會在這個時候,如此聽到的聲音。
方才在生死邊緣走過這一遭,看著漆黑無邊的懸崖深淵,他心頭升起一陣無名的恐懼。
生死相隔,此生永不複見。
這陣劇痛仿佛來自於靈魂深,像刀子一樣剔刮著他的心,他的眼睛驀然便紅了。
“白白,是誰的電話?”
“不知道,媽媽,可能打錯了。”
電話裏傳來一陣冰冷的忙音,謝隨放下手機,了眼角,平複著心裏翻湧的緒。
而第二上午,那段視頻在學校裏傳遍了。
Advertisement
當寂白從班級群裏看到那段亡命飆車的視頻,看到車頭幾乎駛出懸崖之後驟停,謝隨從車裏走出來的畫麵,覺自己的心髒被一雙巨大的手掌扼製住,無法呼吸
沒錯,上一世發生的車禍事故,謝隨的車衝出了懸崖,搜救人員找到他的時候,滿的鮮,雖然最終還是保住了一條命,但他已經形同廢人。
提前了嗎,他避過一劫了嗎,還是隻是巧合!
無數疑問纏繞著寂白,心很,同時也漸漸明白,謝隨所經曆的一切,怨不了任何人,都是他自己一手造的!
想到昨接到的那個無名的電話,聽見裏麵傳來瑟瑟的風聲,的心突然揪了。
放下手機,衝出了教室。
殷夏夏不明所以,見神不對勁,也連忙追了上去:“白白,快上課了,你去哪裏啊?”
寂白沒有回頭,徑直上樓,來到了十九班教室門前,迎麵便撞見謝隨拎著水杯走出教室。
兩個人狹路相逢,麵麵相覷,寂白一張臉因為憤怒,脹紅不已。
謝隨角忽而綻開了一抹微笑,一句“來找我”還沒問出口,寂白加快步伐走到他的邊,揚起手便是一掌
現在一切行為都已經不理智所控製,隻想好好發泄心中的鬱憤,卻在掌距離謝隨臉頰不過分寸之際,停了下來。
從來沒有打過人,也狠不下這個心。
即便是可惡至極如寂緋緋之流,都從來沒有想過傷害的,當然,更多是出於不屑。
周圍不經過的同學瞪大了眼睛,驚愕地著寂白,居然居然敢對謝隨手!
知道,哪裏來的熊心豹子膽。
謝隨的臉冷了下去,側眸了的手,白皙的掌腹裏纏繞著順的紋路。
所有人都以為寂白死定了,哪怕這一掌沒有扇下去,但謝隨是什麽人,他能輕易放過嗎。
令人未想到的是,下一秒,謝隨握住了的手背,輕輕一按,讓中止的那一掌,穩穩地扇在了自己的臉上。
“想打就打。”
年低垂著眉眼,漆黑的眸子凝視著,聲音和——
“不用怕,你是我永遠不會還手的人。”
猜你喜歡
-
完結1722 章

快穿之女配功德無量
從混沌中醒來的蘇離沒有記憶,身上也沒有系統,只是按照冥冥之中的指引,淡然的過好每一次的輪迴的生活 慢慢的她發現,她每一世的身份均是下場不太好的砲灰..... 百世輪迴,積累了無量的功德金光的蘇離才發現,事情遠不是她認為的那樣簡單
292.3萬字8 27087 -
完結719 章
穿書後我成了娛樂圈天花板
一覺醒來,秦暖穿成了虐文小說里最慘的女主角。面對要被惡毒女二和絕情男主欺負的命運,秦暖冷冷一笑,她現在可是手握整個劇本的女主角。什麼?說她戀愛腦、傻白甜、演技差?拜拜男主,虐虐女二,影后獎盃拿到手!當紅小花:「暖姐是我姐妹!」頂流歌神:「暖姐是我爸爸!」秦家父子+八千萬暖陽:「暖姐是我寶貝!」這時,某個小號暗戳戳發了一條:「暖姐是我小祖宗!」娛樂記者嗅到一絲不尋常,當天#秦暖疑似戀愛##秦暖男友#上了圍脖熱搜。秦暖剛拿完新獎,走下舞臺,被記者圍住。「秦小姐,請問你的男朋友是厲氏總裁嗎?」「秦小姐,請問你是不是和歌神在一起了?」面對記者的採訪,秦暖朝著鏡頭嫵媚一笑,一句話解決了所有緋聞。「要男人有什麼用?只會影響我出劍的速度。」當晚,秦暖就被圈內三獎大滿貫的影帝按進了被子里,咬著耳朵命令:「官宣,現在,立刻,馬上。」第二天,秦暖揉著小腰委屈巴巴地發了一條圍脖:「男人只會影響我出劍的速度,所以……我把劍扔了。」
69.3萬字8 47376 -
完結94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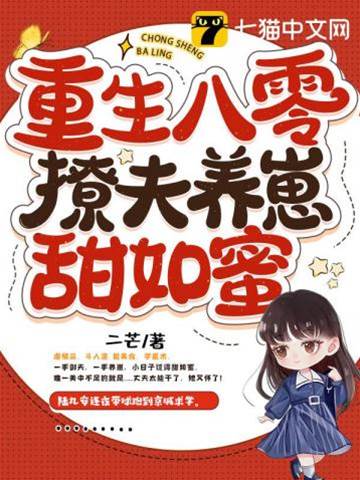
重生八零撩夫養崽甜如蜜
一場綁架,陸九安重回八零年的新婚夜,她果斷選擇收拾包袱跟著新婚丈夫謝蘊寧到林場。虐極品、斗人渣。做美食、學醫術。一手御夫,一手養崽,小日子過得甜如蜜。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丈夫太能干了,她又懷了!怕了怕了!陸九安連夜帶球跑到京城求學。卻發現自己的丈夫站在三尺講臺上,成了她的老師!救命!她真的不想再生崽了!!
174.3萬字8.18 74899 -
完結711 章

高考首富身份曝光,攻略高冷學姐
[都市日常](偏日常+1V1+無系統+學姐+校園戀愛)(女主十章內出現) “兒子,你爸其實是龍國首富!” 老媽的一句話直接給林尋干懵了。 在工地搬磚的老爸
123.7萬字8.33 18213 -
完結242 章

圓橙
直到離開學校許多年後。 在得到那句遲來的抱歉之前。舒沅記憶裏揮之不去的,仍是少年時代那間黑漆漆的器材室倉庫、永遠“不經意”被反鎖的大門、得不到回應的拍打——以及所謂同學們看向她,那些自以為並不傷人的眼神與玩笑話。她記了很多年。 而老天爺對她的眷顧,算起來,卻大概只有一件。 那就是後來,她如願嫁給了那個為她拍案而起、為她打開倉庫大門、為她遮風避雨的人。 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從來屢見不鮮。 連她自己也一直以為,和蔣成的婚姻,不過源於後者的憐憫與成全。 只有蔣成知道。 由始至終真正握住風箏線的人,其實一直都是舒沅。 * 少年時,她是圓滾滾一粒橙,時而微甘時而泛苦。他常把玩著,拿捏著,覺得逗趣,意味盎然。從沒想過,多年後他栽在她手裏,才嘗到真正酸澀滋味。 他愛她到幾近落淚。 庸俗且愚昧。如她當年。
36.8萬字8 103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